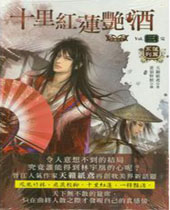十里红妆-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华文渊的党人抓住把柄,落实了我的“叛国通敌之罪”,纵然我贵为天子之姊,亦有性命之虞。
虽然如此,但形势咄咄逼人,我不得不妥协。若不与耶律景私下合作,和谈就很难达成。若战争继续下去,恐怕先遭殃的不是燕国,而是我和文源……
世无恒友,亦无恒敌,唯有恒利。
纸上寥寥数行字迹,十分简略。归纳起来只有三件事:
一,据可靠情报,燕国太子派出了一名神秘的杀手,已在齐国潜伏,意欲破坏和谈。
二,此次来访我国的燕国使者是耶律景的心腹,完全可以信任。
三,为防秘密合作之事泄露,被华文渊或者燕国太子抓住把柄,和谈期间,我与他必须中断一切联系,并且格外小心。
这些情报看似重要,实则可有可无。第三条不用他提醒,我也不会不明白。第一条亦无意义,显然,此事危机重重。无论是燕国太子还是华文渊,都会极尽所能、从中作梗。至于第二条,我连耶律景都无法完全信任,又岂敢真正信任他的心腹?
裴允点燃了案上蜡烛。我将信纸放上去。蜡焰的舔噬下,薄纸迅速化为蝴蝶般的灰烬,消散在风中。
他也看到了纸上内容,双眉微蹙。我轻轻靠在他胸前,他没有抗拒。
我能听到他沉沉的心跳,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他的气息。唯有此时,我才会觉得完全的安稳。仿佛,我不再孤苦,不再无助,不再罪孽深重、无可救赎……
“阿允,你是在担心我么?”
我鼓起勇气,轻声问他。虽是随意淡然的口吻,但只有我知道自己心中的恐惧。我害怕听到否定的答案,害怕他对我的忠诚仅是因为我的身份,害怕上天以他作为对我的惩罚。
等待答案的那一刻,时光仿佛格外漫长。终于,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低低的,却极清晰:“当然,长宁有危险,我自然担心……我,可以一直陪着你,直到我们一同死去么?”与此同时,他第一次主动抱紧了我。
一时间,我不能置信,半晌才回过神来。心中思虑千回百转,却不知如何说起,只能静静埋首在他怀中。
记得幼时,母亲曾对我说,男女之情最不理智。你不知道它产生的缘由,便不能确定它何时会破灭,甚至彻底变质。它可以作为游戏,却不能被相信。能被相信的,只有那些我们可以把握的东西,那些能让我们永远站在最高处的东西。譬如,权力。
母亲说这些话时,眸中有近乎疯狂的炽热光芒。我知道她的痛苦。未及三十岁的她,鬓边已染霜华,只因她无时无刻不在悔恨中煎熬——
她及笄之年,与先皇后沈烟一同入宫侍奉父皇。母亲出身于门第高华的云阳陈氏,父兄皆为朝中高官,一入宫便被封为从二品的婉仪,而出身寒微的沈烟仅是正六品的才人。那时,母亲十分天真。沈烟对她亲近,她便把沈烟当作要好的姐妹。父皇对她宠爱有加,她便把父皇当作温柔的良人。那是她少女时代的一场幸福的美梦,但梦总会破灭——在她怀上文源时,终于遭到了这两个最信任之人的背叛。不仅是背叛,还是她整个家族的灭顶之灾。
父皇早已对陈家暗怀不满,却找不到发作的契机。而沈烟利用她从母亲那里探知的消息,加上她的长期绸缪,提供了那个关键的契机。陈氏满门抄斩,母亲因身怀龙裔才幸免于难,但被降为正七品的更衣,此后从未得任何晋封。而沈烟工于心计,步步为营,最终成为中宫皇后。她唯一的孩子,皇长子华文澜,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东宫太子。
从此,母亲不再相信那些虚无的感情,只剩下刻骨铭心的悔与恨。而如今,我竟愿意相信这种最不理智的感情。她若泉下有知,定然会失望至极地冷笑,等待着我重蹈覆辙吧。
但我不是她,他也不是父皇。
然而,若终有一日,他真的背叛我呢?
我止住自己的胡思乱想,闭上眼,试图摆脱那些阴霾般挥之不去的记忆。
“怎么了?”他轻声问,手轻轻搭在我的额头上,微凉。
我抬头凝视他,他眼眸幽深,却有温和的光芒。
我微微一笑:“没什么,只是太累了。阿允,为我弹一支曲子,好么?”
“想听什么?”
“《凤求凰》。”
他眸光微闪,似乎欲言又止。我正要询问,他却已垂首静默抚琴。
修长的十指,滑过泠泠冰弦。腕下流出的琴声,和他的人一样,沉静如水,无波无澜。纵然是弹奏这样乐律华美的曲子,也是清寂的。是呵,他本是这浮世尘埃之外的人,我不该试图将他禁锢。但我还是忍不住贪恋他带给我的那一丝温暖。从未有过的,温暖。
凤求凰,明知是求不得……但,至少此刻,我是快乐的……
在琴声中阖上眼,恍惚想起过去的艰难。
当初,之所以让他远赴燕国联络耶律景,一来,是因为此事极为重要又极为隐秘,而我最信任的只有他,而且,以他的能力,的确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二来,他主动向我要求让他前往,态度极为坚决。
于是,我便让他去了。但他走后还不到三日,我便后悔了,从未那样痛悔过。
无论是兵荒马乱的边境,还是遥远陌生的燕国,都危机重重。我日日担心,夜夜失眠,服用过御医开的安神药才能勉强睡着。虽然身为女冠,之前我从不信神,但那段时间里,我无数次地向神灵祈祷。也正是那段不堪回首的时光,让我确定了自己的溃败——若爱情是一场战争,他不费一兵一卒便已攻城略地,而我早已溃不成军。
所幸,四个月后,他回来了。如今,他就在我身边,咫尺之遥。我何其幸运。
但,千疮百孔、污秽不堪的我,给不了他幸福。
待和谈结束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让他离开。为他准备足够优渥的条件,任他远走高飞……去四季如春的越州,或去山水秀异的湖州,或去某个宁静的江南水乡……总之,离京都越远越好……而我,我从出生那天起,便注定了要在这座城中禁锢一生……
似乎有温软的风扑着面颊,轻若游丝。睡意止不住地袭上来,意识渐渐模糊……琴声仿佛变了,不再是《凤求凰》,而是某支记忆深处的曲子……
琴声忽然变得遥远,仿佛回到很久以前……四周是熙攘而喧嚣的人群,光影斑驳。无数陌生人从我身旁流水般经过,但我看不清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模样……这时,我察觉到,有人拉着我的手,带我静静地穿过茫茫人海。那只稳定而温暖的手,免我惊惶,免我担忧……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驻足。
“清音坊,到了。”熟悉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
我一惊,匆匆转身,身旁却已无人。虚空中,唯有沉沉的黑暗与遥远的琴声。我想要逃离,却动弹不得。一片刺目的浓红漫上来,似要将我淹没……
我陡然惊醒。
睁开眼时,已汗浥绡衣。
视线由模糊转为清晰,只见裴允正在我身侧,执着一把折扇,静静为我打扇。紫竹扇骨,扇面雪白,无字无画。扇起的微风间,衣上墨香愈发淡远。纱袍的袖角微微拂动,似一片淡碧轻烟。他垂眸静坐,神色静谧,仿佛这世间没有什么能惊扰他。
他在这里,不曾离开。我的心便也渐渐宁定下来。
或许因为近日太过疲劳,方才听着琴声,竟不知不觉,在簟席上睡着了。
我撑身起来,懒懒地靠在他怀中。钗钿松落,三尺青丝尽委于他的衣上,仿佛沉黑的流水。
恍惚记起,在我坠入梦境之前,隐约听到的琴曲,正是《流水》。这也是我初到清音坊时,在琴室之外听到的琴曲。琴音淙淙,若淡烟流水,玉壶冰心。因我由衷地赞了一句,华文澜玩笑道:“不如去看看弹琴之人。或许,还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就这样,我遇见了裴允。
方才,听到久已不闻的《流水》,难怪会有此梦。
但,为何一直在弹《凤求凰》的他,会将曲子换成《流水》?
我微觉疑惑,正要询问,他已轻声道:“可是魇着了?”
我不欲让他担心,便微笑道:“无妨,只是梦罢了。”
无妨。诸如此类的梦魇,早已习惯。三年来,已不记得曾多少次梦到华文澜。
当年,是他带着年方及笄的我,初来清音坊。后来,身处宫禁的我与裴允私下通信,华文澜也帮我隐瞒。从小,他就待我极好。由于母亲背负着罪臣之女的耻辱,我童年的境遇十分不堪,时常遭人欺辱。他总是尽量帮我。即使是我犯了错,也会偏袒维护我。在他眼中,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需要他的爱护与怜悯。他的清朗大度,绝不相类于其母的阴狠歹毒。若无上一代的恩怨仇恨,也许,我和他会是最要好的兄妹。但世事安排,从来由不得人……
剥啄的叩门声打破了寂静,也打断了我的思绪。
“谁?”他淡淡问。
门外传来清欢的声音:“是我,师父。外面有位姓颜的大人来找长公主,说有要事,必须马上通传。”
朝中的颜姓官员并不多,可能来找我的,唯有一人——鸿胪寺右少卿颜慎。他是三年前的新科进士,由我提拔,为人谨慎沉着,是我得力的直系下属。此次我派他前去护送燕国使者,但他竟突然来此……
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我立即起身下楼。
果然,清音坊的大门外,身着湖青夔纹官服的年轻人正负手站在那里,正是颜慎。他素来沉稳,此刻却不复往日的从容,满脸焦虑之色。见了我,连忙迎上来,也顾不得礼节,开门见山:“燕国使者遇害了。”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静了刹那,我还是有些不能相信。
他深吸了口气,脸色苍白:“属下无能,未能护送使者安全抵达京都,有负长公主所托,甘受重责。”
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镇定下来,冷静地问:“使者在何处遇害?”
“方远镇的一家客栈。”
方远镇距离京不到三百里,若快马加鞭,来此不过大半日的行程。而颜慎带领数十名精兵侍卫,从两国边境一路护送到方远镇,已行了近半个月,自然会疲惫,眼见即将到达帝都完成任务,便可能放松警惕。
功亏一篑。
紧要关头,容不得举棋不定。我静声道:“带我去那里,越快越好。”
他有些惊讶:“长公主千金之躯,不宜亲赴……”
我扫了他一眼,他立刻噤声,迅速安排车马。
似乎察觉到身后投来的目光,我转过身,只见裴允独自立于紫檀镂花的门框前,怀抱桐木蜀琴。阳光斜斜照过来,在他身上落了一层淡凉的金。夏日的微风中,衣袂轻扬,可见碧纱袖角勾绣的竹叶暗纹。但他只是静静望着我,目光中有我看不透的幽深。
我忽然疑心他会突然消失。那一瞬,似有千言万语,最终却只能归于轻轻一声“抱歉。”
对他,我不是没有歉意的。我虽时常来此,但实际上,几乎从未有过完整的半日光阴,让我可以一直待在他身旁。尘网萦身,然而一旦离了尘网,又何处栖身?
他微微一笑,垂首轻拨琴弦,溅出几个清亮的碎音:“长公主不需要在下陪同么?”
他是担心我的安危么?心头一暖,但我还是拒绝了。
在我得知噩耗的同时,华文渊也该收到消息了,他很可能会去方远镇。下意识里,我不想让裴允与他见面。毕竟,再无人比他更清楚我的肮脏过往。他是我的同类,在欲望与阴谋中翻云覆雨,永生不得光明。而裴允清净淡泊,与我差若云泥。
自欺欺人的逃避么?
我垂下车帘。车声辘辘,向东城门驶去,一路绝尘。
马车中,颜慎向我简要介绍事情的经过:“昨夜,护送队伍在方远镇内的一家客栈歇息,准备明日一早启程,下午便可抵达京都。为确保安全,属下包下了整座客栈,燕国使者单独住一间上房……”
我略感惊讶地打断他:“怎能让燕使单独住一个房间?”
他一向办事谨慎,这不像他的作风。
“属下本来安排了两名侍卫贴身保护燕国使者,但使者坚持拒绝。他说他带着燕国皇帝托付给他的机密文书,未见到陛下之前,不能泄露给任何人。而他又似乎不太信任我们的人。我只能允了,但还是实施了尽可能严密的保护——客栈被包下,外人不得进出。他周围的房间里都住着我们的人,稍有动静便会警觉。还有不少侍卫把守于走廊上。
属下原本以为,如此已是万无一失,却没想到,刺客化装为客栈的小二,借送茶之名,进入房间。其实,若刺客是后来才伪装的,想必也不会得逞。但他显然早已预料到我们会在这家客栈住宿,我们刚到客栈时,便是他出来殷勤迎接我们的,因此,我们对他放松了警惕。”
说着,颜慎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听出了端倪,挑眉道:“你的意思是……”
他郑重地颔首道:“属下怀疑,有我朝内部之人为刺客提供情报。方远镇是大镇,客栈至少有四五家,而且,京都附近的城镇也不少。我们的行程与路线皆是机密,若无内应,刺客很难预知我们会在方远镇的那家客栈借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