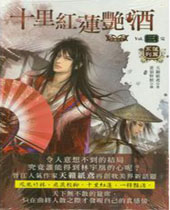十里红妆-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八、浮华远影
傍晚,风中还残留着白日的暑气,带来城郊青山的隐隐气息。马车沿天街驶出城门。宽敞的青石街面铺以洁白细砂,车轮轧过平稳无声。两旁是连绵不绝的绛红罗金缕锦帐,皆作海龙纹,是亲王婚礼才能使用的仪制。
坐于车内的我,依然能听到街边看热闹的百姓的交谈声——
“啧啧,这是谁的马车啊,好大排场?”
“银鞯金络脑,宝辂香车,朱漆嵌螺,绡纱帷……这还用说,除了当今圣上,还有谁的车驾如此奢华?”
“但今日是王爷的婚礼,她来作什么?她不是和王爷势不两立么?难道那些传说是真的,她与王爷真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别瞎扯。王爷是大齐的英雄,岂会与妖女做那苟且之事?依我看,这妖女定是来趁机作乱。”
真是纷纷攘攘,好不热闹。
我的唇角漫出一丝无声笑意,随手理了理衣襟上的银丝碎珠流苏。
目的地到了,马车终于停下。
按照京都风俗,有婚嫁喜事时,新人要到城外近郊的月神庙祈求姻缘美满。或者说,是希望永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之中,永不醒来。
此时,月神庙前,倚仗煊赫,旌节遮天。一众宫女着水红宫锦高腰襦裙,分执宝扇、华盖、香炉、宫灯等礼器,分列两旁。武官持弓佩剑,拱卫如仪。庙前的石阙楼门装饰得金碧辉煌,浮雕的七夕鹊桥栩栩如生,上千只喜鹊只只形态各异,振翅欲飞。《紫云》乐声响遏行云。天边的璀璨霞光也比不过这人间繁华的盛大艳丽。
如此声势浩大,不但引来众多百姓围观,许多主战派的大臣皆亲临恭贺,冠盖如云。华文渊正按照京都的婚俗,在庙前的月神像下,象征性地供奉馨香祭品,以祈求姻缘幸福。而新娘的鸾车停在一旁,紫金鸾铃在风中宛转而鸣。
我的出现,令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微妙。
此刻,有多少人恨不得用目光将我撕成碎片呢?我一边含笑揣测,一边提着裙裾,绣履一步步踏上石阶,向月神像走去。阶上铺着柔软的蜀锦茵褥,上面铺绣着各种泥金印花:牡丹、芍药、蔷薇、菡萏、芙蓉、山茶……仿佛四季花卉一时盛开,灿烂得目眩。拾阶而上,我仿佛走过记忆里漫长的年光岁月,韶华如花。似能听到花朵在曳地的裙裾下纷纷凋零的声音。
华文渊静立于月神庙前,身后是夕阳最后的余光。我逆光而行,影子在身后拖得修长,步履却是闲时踏青般的轻松。
终至他面前,站定,妩媚微笑:“恭喜。”
绯罗麒麟金绣的吉服,每一丝绣纹都精美无比。但他沉默如斯,连这明艳色彩也显得凝重沉郁,在他微微蹙眉的瞬间,竟有肃杀之感。不像即将洞房花烛的新郎,倒像刚从沙场沐血归来的将军。这般模样,怕是要吓坏新妇了。
我掩袖而笑:“我不是来送贺礼的,而是来向王爷讨要一样东西。王爷欠我之物,可还记得?”
他的眸光一动,似有记忆在窅暗中翻腾。但那也不过是刹那之间。他随即轻勾唇角,扬起微笑:“我还以为,你已忘了。”
我的目光扫过周围众人,悠然道:“王爷是言而有信之人,想必不会令我失望而归。”
他静了刹那,低低道:“如你所愿。”
下一刻,他已一把将我横抱起来。我笑着伸臂搂住他的颈,腕上银镯叮当轻响。
今日,我特地穿了一身缟裳素衣,单钗浅黛。在满目如海浓红之中,想必格外醒目。漩纹轻容素纱、云鹤水波绫、染银晕痕吹絮纶、白萍纹连烟妆花缎、纯白折枝牡丹暗纹天华锦……层层衣裾重叠着次第绽放,在风中轻扬着拂过他朱红的吉服。檀乌色的长发流水般垂泻而下,浓郁的降真香弥散在襟带间。
他紧紧拥着这尊华丽而冰冷的偶人,仿佛要把它揉进骨血中。
是恨么?就像我恨他,就像我恨自己。
我闭上眼,听着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想象着他们的惊讶失措之态,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般,不能自已地欣然微笑。
何必大惊小怪呢,这早已不是我与他的第一个拥抱。
第一次,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他多病的母亲在冷宫中去世,他独立在廊上,整整一夜不言不动,静如雕塑,仿佛连呼吸都消失。我静静站在他身后,陪他度过长夜。黎明的晨光浮现时,我终于上前,浅浅拥抱了他,如同怜惜另一种可能的自己,如同安慰被病痛折磨的文源。他终于说了长久以来的第一句话:“这个拥抱,我欠你。”
那一刻他冰凉的体温似乎仍残留在我的指尖,那一夜的风露星辰亦仍如在目前。但当年的承诺,终于在今日被我当成报复的工具。
忽然,有什么轻轻落在额头上,像是一瓣眉间的落花。
我蓦然睁开眼,他却已将我放下。平静如水的神情,让我知道方才不过是恍惚中的错觉。
转身的刹那,并不意外地迎上了新娘的目光。鎏金飞檐、馥彩纱幕的鸾车内,本应静静坐着的她,挑开了缀着细碎珍珠穗的纱幕,凤冠霞帔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如果不是她此刻震惊的目光与神情,精心妆扮过的她,会更美吧。据说,作为阮宰辅嫡长女的阮明月,从小被视为掌珠。外表温柔娴静,性情却娇纵,蛾眉不肯让人。
真是很有趣呢。
人群中再次爆发出潮水般的议论声,关于我,也关于华文渊。
我朝她颔首微笑,而后从容离去。仿佛一个戏伶,在观众的喝彩中,优雅谢幕。
斜阳在我身后敛去了最后一抹霞光。
夜□临。
文源,为你提供的故事话本着墨添色,这是我离开之前,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初次见到耶律景的诧异神色,是在燕国国君派来的第二位使者出现在金銮殿上时。当这位使者朗声念完燕君的请婚旨意时,耶律景冷然一笑,似是自嘲。
他自以为掌握一切,到底仍是太轻敌了,棋差一着。他冀图使文源与华文渊河蚌相争,殊不知,他们也希望维持耶律景与燕国太子势力间的平衡。为了达到这个共同目的,这两个分庭抗礼的敌人,达成了一次令人意外的合作——我赴燕和亲,却不是嫁给国君,而是嫁给太子。
皇贵妃变成太子妃,我是否也该表示惊讶?却只有麻木了。
额角垂下一缕青丝,轻拂着脸庞。看着水晶帘上的瑟瑟光影,哑然失笑。棋子无论放到哪里,都只是棋子罢了,随时可能变成弃子。嫁给年近六旬的国君,与嫁给庸懦无能的太子,又有何区别?终不过是,浮云沧海各自远。
煌煌大殿内,龙涎香的气息太过浓郁。高大的朱漆雕龙的梁柱下,满殿文武衣冠像是一排排面目模糊的泥俑。上百盏宝盖珠络的琉璃宫灯之下,容不得半点阴影。地面上,沉厚的金砖拼贴无缝,光洁如鉴。然而,阴谋、野心、仇恨、欲望……种种人间极致的罪恶,隐藏其间。
华文渊静声道:“从此两国结为秦晋之好,恭喜陛下。”
文源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模糊得失了真,却又明明是真的:“众爱卿以为如何?”
满殿犹在惊诧中的大臣,齐齐跪了满地,山呼万岁,齐声道贺。仿佛真是普天同庆。而我冷眼旁观,格格不入。
同样格格不入的,唯有耶律景。他仍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不辨端倪。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暗暗握紧了,很快又松开。他不会逃避这次失策,毕竟来日方长,他尚有无限可能——如今,无论是齐与燕的局,还是两国各自内部之局,都是和局。微妙而危险的平衡状态,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下朝后,我在殿外的走廊上与他不期而遇。
廊下芳莎如烟,古槐浓荫似水,他的眸子映得隐隐生碧,无声时也似在言语。
他俯身行礼后,含笑轻声道:“令兄和令弟都很为您着想呢。”
我握紧了手中的镂花檀香折扇。
他似乎并不介意我的沉默,在我耳畔以轻快的语气续道:“对了,长公主大概还不知道吧,这可是燕国皇室最大的丑闻,一直被小心遮掩——燕国太子不近女色,却有断袖之癖。”
我微微一怔,侧眸看着他,莞尔笑了:“一个有断袖之癖的丈夫,与一个荒□伦的妻子,真是绝配。白大人难道不觉得么?”
言罢,与他擦肩而过。
廊上,恰有一队宫女捧着几件名窑进贡的瓷器姗姗行来,见了我,皆半跪行礼。看着她们按节令更变的宫装——秋香色海棠纹潞绸襦裙,方才蓦然察觉,不知不觉间,秋已至了。
我离开京都之日,再次见到了十里红妆的盛况。
文源赐下的随嫁妆奁之丰厚,远逾仪制。许多朝臣虽觉不妥,但连华文渊都未表示反对,礼部谏臣的上书被驳回之后,再无人提出异议。
其实这是件再清楚不过的买卖,礼尚往来。既然燕国给出了太子妃这个名位,齐国不能也没有付出。至于我这个人如何,与十万缗的嫁妆相比,倒是无足轻重的。
但连我也始料未及的是,此次远嫁和亲,动用了全副的鸾驾凤仪。这是册后时才用的规格,而公主出降向来只能用其一半。
想起幼时与华文澜的对话,竟像是早已预言了命运一般。只是,送我出嫁的并不是他。
但无论如何,终不过微笑着领旨谢恩。
身着金红九鸾缠枝花卉纹云锦礼服,广袖长垂及地,环佩玎玲。薄如蝉翼的绛色纱罗上,捻金孔雀羽线绣出的凤凰振翅欲飞。高梳的云髻上,十二对宝钿珠钗与点翠纹金耳坠相映,沉沉地压着颈,像是教人不得不谦卑俯首的命运。从内臣手中接过圣旨的刹那,似有清风漫过深远的大殿,隐约微凉。
到底已是秋了。
钟磬齐鸣,重重宫门次第打开。织金石榴纹朱红茵毯从殿内直铺出去,通向逶迤满城的仪仗,通向京都最大的城门,通向我未来的命运。那样漫长,漫长得看不到尽头,漫长得教人绝望。
此时的我,已不再是名义上的女冠。之前的度道出家,被朝廷解释为我替皇室、国脉祈福,如今功德圆满。除下缁衣披嫁衣,民间由此衍生的话题和流言,可想而知,一定十分热闹。
百年之后,野史上声名不堪的长宁公主,是我?非我?
而今时今日,十里红妆,满城繁华,如云蒸霞蔚。上千担剔红彩绘螺钿嫁箱,车水马龙经过天街。锦帐底下坠着细密的精雕玉珠串和碎金流苏,随嫁宫娥与匠役身着红绡金罗如意纹服饰。
鸳鸯锦制成的珠履,以白玉为底,用莲花暗纹的绡纱包了香粉。踏在柔软的茵毯上,印出一朵朵淡色莲花,宛如步步生莲。身后拖裾长曳,四名宫女絜托重重叠叠的滚绣裙幅。另由一名宫女小心翼翼地扶着手,如一件被展览的珍器般,缓缓走过众人的视线。
满目的红,朱红、嫣红、妃红、桃红、朱砂红、珊瑚红、海棠红、石榴红、胭脂红……种种的红,浓得不能再浓,好像随时会化了灰,扑簌簌消失在风中。禁城的连绵朱墙,锁不住急景流年,只锁住了三千红颜、一叠彤帖,与零落满地的,宫花寂寞红。红叶也漂不出九重深宫的御沟。
而我可是被人移植异地的那一株罂粟?纤手为刃,胭脂是毒。
我从不知,红色可以如此荒凉,看久了便觉空茫,微微晕眩。或许,是一夜无眠的缘故?
昨夜,皇帝、皇后的仪驾,先后来了长宁观,真是空前盛况。待得清静时,东方已白。
“我曾说过,若你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文源负手立在窗前,没有看我。他用认真的语气,说着太过稚气的内容,“我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终是顿住了,再无下文。像窗外玉玦般的残月,不得圆满。
月光照在案上的沉香木雕山水对杯上,淡如霜。茶烟渐渐淡了。
我召来侍女:“茶凉了,温一温吧。”
茶可以再温,味却不是初沏时的了。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当然,还可以重泡新茶,或另换一种茶。诸类佳茗,宫中永远不缺。更何况,还有许多事,比品茶更为重要。譬如,江山。盈盈一杯茶,承载不起如斯重量。不若,舍弃。
文源离开后,又迎来阮秋水的凤驾。大齐皇后的华雅雍容,像玉瓶里的软瓣银红牡丹,开在工笔彩绘的古卷上,堪为后世摹本。抑或,每朵于禁苑中宫盛开的牡丹,本就相仿——妍丽的是千瓣的天香与国色,却不见了柔软的初心?
暗中助文源构建势力的,一直是她。她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即使是帮他迎娶顾司马的千金。也许,不是不难过的,但不得不向命运妥协。我亦如此。所以,她为文源而瞒着我,我从不怪她。但她为何双眉不展?我愈笑,那远山似的眉便蹙得愈深。我敛了笑意,接过侍女奉上的茶盏,静静道:“皇后娘娘,请用茶吧。”
她终是没有用茶,离去。我掩上茶盖,轻轻叹息。
而此刻,在声彻云霄的乐声中,任何一声叹息,都足以被淹没。
登上城楼最后一次回望京都时,看着城楼下跪地行礼的官吏民众,我忽然想起了太庙中祭祀用的牲牢。终年不见日光的殿宇内,历代皇族的紫檀牌位高高供奉,袅袅炉烟氤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