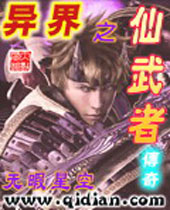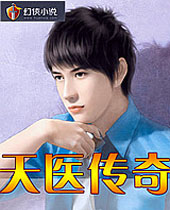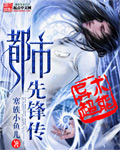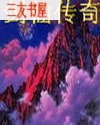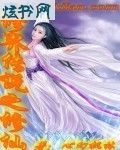高衙内新传-第39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哪个想借机赌一把从中获利的,眼下有枢密院跳出来挑大梁,谁不顺水推舟?反正打赢了大家升官发财,打输了自然有枢密院受责。
对于这中间的细微转折,高强如今已经是明镜一般看得通透,心说本衙内如今至少也弄一个勇于任事的名声了吧?
既然大家都意见一致,皇帝基本上就没有别的意见了,御笔照谁。这一声令下,大宋的军事机器立即运转起来,枢密院新成立的参议司由宗泽暂领,又征调了若干通晓西北形势的干员襄赞其事。
对于此次攻打减底河城之役,参议司按照既定战略,将后勤的重点放在兵器和战具的调集上,将环庆路、漉延路两路州府所储藏的军器和战具并有关工匠,悉数调往保安军,准备支持攻城作战,同时集结起这两路与邻近的泾原路、秦凤路、京兆府等的精兵共计八万余,战马近两万匹,在保安军集结待命。
凡战必当设疑兵,这次宋军的疑兵之计有所不同,不是以出兵来实施,而是将今年交由参议司来分配的边军粮草一大部集结到西边靖夏城附近交割囤积,同时征召民失数万,也都往靖夏城集结。自来宋军出兵,粮草转输都是事先囤积,大军出击之后,民失大队运输粮草随后跟进,而这种种情报,由于西夏与西北各路的蕃民时有联络,亦尽数送往了西夏朝中。
在夏人看来,这当然是最有力的出兵证据,证明宋军的主力所向是西路地靖夏城、萧关一线,甚至可能远从羌地的古骨龙出兵。因此一面与宋朝地使者扯皮,察哥一面便将主力集结到中路和西线,东线的盛底河城一带便撤空了,只有梁多凌所部万余人屯守。
战机凸现,童贯却在这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他紧急上书,称自己认为减底河城难攻,请求朝廷收回成命,改从西路进兵。
这道表章传回东京,高强差点把鼻子给气歪了,心说有意见你早点提,如今箭在弦上了,你倒来耍花样,哪有这等视军事如儿戏的?童贯的说法当然是有一定道理,朝廷现在打的主意是一锤子买卖,全军不携辎重粮草,作战前后最多有十天时间,要是打不下盛底河城,就只能撤兵还朝。而就他所见,这盛底河城实在是形势险要,易守难攻,把宝押到这上头,不大明智。
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种师道得知此事后,半夜跑到高强府上,拍着胸脯担保此战必胜,集八万大军攻打五千人的城池,哪怕每天用三千人换一千人,五天也就攻下来了,就算伤亡较大,但盛底河城如此坚城数日便沧陷,对于西夏的精神冲击巨大,对于实现朝廷稳定西线的既定目标极为有利。
有了种师道的拍胸脯担保,高强的胆气便壮了许多,次日朝堂上便提出,大军已集,不得不发,既然童贯以为难不肯率军,便当另择良将统兵,随即推荐种师道统兵。赵佶对于种师道却有印象,当即命宣上殿来,每询方略。
时种师道已经年过半百,但精神健旺不亚少年,当廷指陈方略时声如洪钟,震的四壁隐隐有回声,尽显武将豪迈,谈及胜败之时,声称愿立下军令状,事败便不还朝。赵佶也不知是被他的豪气打动,还是被其必胜信心所感染,总之是龙颜大悦,说道:“卿家乃朕所亲擢也,此去只望露布捷报!”
即日,皇命枢密院都承旨种师道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衔,进官康州防御使,督责五路大军近九万人,攻打盛底河城,期以十日必克。种师道受命上马,十日飞驰至保安军,一到军中,即刻下令全军进发,直取减底河城,当时的情景,据在场一名书生的描述:“军中建种四厢旗号,诸军睹之皆欢呼,声震山谷,俄尔知进取盛底河城,士皆踊跃,大军四合,甲光耀日,上有气大如二千斛囤,有人善观风角者识之乃必克之相也。”
那些底河城距离保安军边境不过百里,大军出塞,行两日即至。种师道率军一到,分布骑兵巡查四周,又命诸军将此城团团围住,分散队猛攻。当时有将领提出:此城甚为坚固,应当砍伐树木,建造鹅车木驴,并竖起石炮来四面轰击方可,肉搏登城损伤必多。
种师道置之不理,却将皇帝亲笔诏书给拿了出来,说道十日不下此城,则大事皆去,一旦敌兵四合,我军又无粮草,全军覆没只在顷刻间!诸将一看,才知道此战与平常不同,进是死,退也是死,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一连五日,种师道督军猛攻,昼夜不休,开头是肉搏登城,后来赶制了几十辆鹅车和吕公车攻城,城中梁多凌等人情知大势不妙,拼命抵御,仗着城高壕深,得以保守城池。
到了第六日上,种师道亲身督战,见有一员偏将坐在胡床上没精打采的督战,当即大怒,命亲将王进将这偏将一刀砍了脑袋,传首诸军,号令:有战不尽力者,便如此人!
这号令传到种师中营中,激起两位英雄,当日夕阳之下,万众瞩目之中,只见一名白发头陀和一名红袍僧人先登城头,手杀百十人,当者披靡,众宋军士气大振,蚁附而上,底河城遂一举告破。
第十二卷 燕云中篇 第四二章
露布飞捷,沿边各路与京城官民俱都大喜。宋军近年虽然在对西夏的战事中取得主动,然而崇宁大观历次战事多在对羌人的作战中发生,象此番攻克盛底河城战事,动员八万多大军——照例“号称”十万——几天之内就传来捷报,这样的破竹之势,实属仅见。
连日来,朝野上书称贺的文书如雪片般飞来,花样翻新的大拍赵佶的马屁,以至于高强被招到崇政殿时,摆在他面前的景象就是赵佶正在津津有味地翻阅着案头一大堆几有一人高的书奏。
见到高强进来,赵佶满面春风,起座道:“爱卿当日一力主张进兵,称说盛底河城必克,又荐种师道可使,真可谓知兵也!相形之下,童贯虽亦有平羌人之功,今番可教爱卿比下去了。朕得卿家辅政,真乃社稷之福也!”
高强是知道赵佶的脾气的,这皇帝经常想到一处是一处,口不择言,过后便忘,要是以为他就会从此不再绮重童贯,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是以忙拱手作礼,道:“官家圣明宸断,祖宗之福,臣何功之有?童帅极言此城难攻,亦是爱惜士卒性命,持重为计,臣观此战战报,阵亡将士计三千余人,被伤过万人,不可谓不惨烈。况且师出不携辎重,是不顾后路,兵家所忌,今虽统幸得胜,后却不可以为法。”
赵佶见高强说的恳切,又转思童贯的好处起来,愈发觉得高强言行得体。当即夸奖了高强几句,又道:“如今一阵大胜,夏人胆落,种四厢奏请当毁坏此城,大军回转,更晓谕夏人,以固其盟约,卿家以为如何?”
这正是高强在种师道出征前就和他商量好的战略,更有何疑?便将时下情势解说一遍,着重点出塞北已经现出乱象。不数年就是收复燕云的大好机会。区区西夏,就算让他多活几十年,也不会危及大宋根本。何况这一仗已经打得夏人胆落,若是大宋主动息兵修好,他那里正是求之不得,趁机要求减少些岁币也是有的,何乐而不为?
赵佶原是耳朵根子软的,又当信用高强之时,自然无不见听。随即议起当命何人前去晓谕夏人,重修盟约。高强心里打鼓,心说可不要派我去吧?眼下北边随时有可能打起来,我哪里走的开!
好在西夏如辽国一般,也有使节在汴京常驻,况且如今又是宋军得胜。这遣使之事也可免了,只要私下命人向西夏那边吹吹风就好,说罢这件,赵佶却又拿起那捷报来。指着上面道:“高爱卿,这露布上说,此役先登乃是常胜军统领官武松,此人你可识得?”
高强心说我自然认得,还是我弟弟呢!不过这些事自然不好对着皇帝说,便点头称是,将童贯借兵一事说了,又说那光头僧人乃是武松的师父,出家前原是种师道麾下将佐,此番激于大义,重回军前效力,不意有此大功。
赵佶听说还有这等新鲜八卦,如何不爱?催着高强将鲁智深的种种情事说了一遍,听他醉打山门,又吃狗肉,大闹僧堂,不禁击节叫好:“似此真可谓得其性情者,金狄之教,每重名戒,最是不堪,要如此作和尚方好!”
高强这才省起,这皇帝原是个爱道家的,难得他能喜欢鲁智深的作为,也算是异数了。
鲁智深既走出家,什么官衔封赏也落不到他头上,赵佶便命人造一面金牌,御赐一个名号与他。至于武松虽是头陀,却因为梁山军系招安之故,离不得军中,故而有军职在身,临战有功,自然以军法封赏。高强又趁机称说借兵之事不可长久,既然立功,便许回戍京东,赵佶正在兴头上,也便允了。
说了一会,赵佶忽然想起一事,便道:“卿家时时以收复燕云为务,自然是好,但不知这收复燕云,须用多少兵马,多少粮饷,朝廷可支吾得?如其仓促难集,可从今日便着手调遣为上。”
高强闻言,便想起历史上的平燕钱来,就用这个名义,王甫为首的宰执大臣搜舌了整整六千二百万贯钱!若是再算上以此为契机,各方官吏层层加码所征收的钱财来,大宋百姓等于是额外多花了几亿贯钱,换来的却是一个残破的燕云,以及短短几年的虚假繁荣!事实上,这加派饷钱和东南方腊起事有着直接关系,经过了全国加赋和东南残破两件事一折腾,原本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朝廷财政立刻陷于崩溃,这才是北宋灭亡背后的真实原因。
当然,一个国家的灭亡,绝不能归罪于外征和内敛,如果国家没有集结国民力量,对抗外侮的能力,那么这样的国家也就活该灭亡了。正是基于这一点见识,高强在后世每每看到有人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女真,说如果没有女真就没有辽饷,没有辽饷就没有流民时,便觉得极端之幼稚可笑,国家是为了保护国民而生的,如果他不能完成这个义务,不亡何待?
“官家虑的身当,惟臣于梁山招安十万之众,冥冥中岂有天意,欲借此佐陛下成此功业子?”高强当然不会说他就是有意招安梁山军,为了收复燕云之用的,将此事归于皇帝,那是顺手一记马屁,不拍白不拍:“至于常胜军之战力,则于此盛底河城一役亦可窥见矣。此役集西军之精华所在,而武松、鲁智深能为先登,功盖诸军,此亦可谓善战矣!“
果然赵佶闻言大悦,欣然道:“是乃天顾朕命,故降下佐命之臣也!卿亦如是。”
这对于皇帝来说是极大的奖励了,高强当然要惶恐谢恩,却被赵佶止住,笑道:“皇天佐命,厥功必成。卿但放胆作去,万事有朕。倘须兵马钱粮,只须拟上札子来,朕必照谁。纵然宰执外廷有大臣不服,朕亦可以手诏降之,惟卿勉力为之。”
这等于是非正式地的燕云大事都委任给高强了,尽管不断地提醒自己,赵佶这皇帝经常头脑发热,比如他在崇宁四年就曾经说过蔡京是“盗臣”,并痛陈“宁有聚敛之臣,莫用盗臣”。可是后来还不是三用蔡京为相?饶是这般,高强还是忍不住的欣喜,忙活了这么久,不就是为了这件大事么?
说及平燕所需的钱粮。高强自是胸有成竹。如果按照历史上收复燕云的使费来看。即便是赵佶及其大臣们那么败家,临了这六千二百万贯好象也没用完,就拿这个数字来计算。如今的高衙内,掏尽身家大约也拿的出来了,到时候就算朝廷没钱,大不了再贷款给朝廷好了。什么,你说衙内自己用度怎么办?以宋朝的官员俸禄来说,到时候就算高强在家吃闲饭,只要不一顿吃掉若干人的一年收入之类,大约也够过活了,况且他也不是好享受的人——从现代回转古代的人,对于生活上还能有什么要求?再高也不能电气化吧?凑合着过呗!
话是这么说,当然也只是个最低限度的计划,高强对赵佶的说法则是:“自来官吏刻录百姓,惟患无名目,是上征一钱于民。而官吏得趁机博九钱入私门矣!是以臣虽受命勾当大事,亦当以不加民赋为己任。然臣理财各事,便须得官家天聪明断了。”那意思,我以后要是有什么理财的新花样,你可得保证支持我。
对于这样的要求,赵佶非但不觉得过分,反而有些期待,莫非这位以理财圣手闻名的年轻大臣,居然还有什么理财的新方法不成?这却是他无从预料到棉花和白糖这两样事物的利润率的,照着许贯忠等人的估算,以目前的推广速度进行下去,不过五年,这两样东西给应奉局带来的净利润便可以达到每年三百万贯以上,这还没有计算民间商业发达和百姓财产性收入增加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好处。一个每年的净收入一千万贯,并且速度每年递增的应奉局,五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