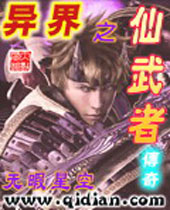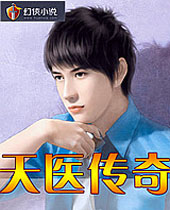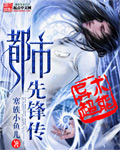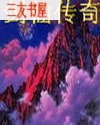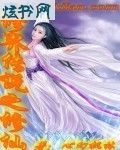高衙内新传-第3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无论如何,总不会比历史上金兵打破汴梁来得差吧?”这么一想,高强便心安理得起来,在博览会三楼的办公室里哼起小曲来。
只是忙里偷闲终究是难得的,他才清闲了一会,便被许贯忠带来的一个消息惊地跳了起来:“衙内,杭州报喜!小乙已经制成了马车车厢和车头。并从杭州城到运河码头铺了一条铁轨。初试成功云!“这所谓的马车可不同于四轮马车,乃是马拉火车之意,只是这时代又没有人见过火车。这概念自然也就简化成了马车。
高强闻讯,抢过许贯忠手中的书信来看时,只见燕青写的明白,这马拉火车用十二匹马为一纲首——宋人没有什么一列火车的概念,便沿用纲运的概念,将车头称作纲首——一纲四节车厢连缀,车厢以木为箱,用铁为底,用钢作轮,青铜为轴。每节车厢可载重五千斤,四节便是两万,正合宋朝一纲运粮之数目。这也是燕青巧思,便于这马车的运输制度得以与现今的纲运制度相契合。
见信上说,此车快如飞电,一程百里,不过费时两个时辰,惟需调训马速,不可过快。否则车重马轻,一旦动起来之后,轻易难得停止,倒好挫伤了马匹。
高强见了,连连扼腕,叫道当初少说了一句,这刹车得安在车厢上,用一个联动装置,由车头控制着便好,若是用车头刹车,那马腿如何经受的住偌大惯性?好在这也只是一个小问题。再往下看,心却冷了一截,原来燕青附上铺设铁轨的费用,每一里铁轨,竟需要费钱两千五百贯,从杭州铺到京城,曲折四千里路,再加上沿途车站地设置,铺这么一条铁轨起码要花上两千万贯!
高强愁眉苦脸,心说这么大笔数目,倘若再迁延时日的话,又得翻着跟头向上涨,这铁路到猴年马月才能通车?还是许贯忠在一旁见高强变色,问了情由,不由失笑道:“从杭州铺到汴京,衙内好大手笔!只不悟此路一成,沿路漕挽士卒当如何生计?能不生乱乎?”
高强一凛,这才省觉。历史上中国近代黑社会的形成,很大原因就是洋人介入了内河和内地的运输之后,失业的漕运工人无处去,才结成了黑社会。大宋南北漕运地发达,比晚清也不差到哪里去,赖之营生之人少说上百万,他这么一搞,那些人怎么办?难道逼人家造反么?
“如此说来,此物竟是无用?”高强大为懊丧,心说单单研究经费就不晓得花了多少,弄出来却没用,没得叫人丧气。
许贯忠笑道:“若说无用,却又不然,小乙这信中,其实已经说明了其用途所在,只是衙内不曾深思而已。”
高强大讶,复又将那信拿起来看了一遍,若有所悟,道:“贯忠所说的,莫非是小乙以杭州城到码头这一段,营建铁路作为试行?”
许贯忠颔首道:“正是。自来漕运以河,陆运以辇,沿途上下集散煞是不便。若是于汴京、南京、建康府、杭州等地,量建铁路,以通码头与州城,即是便利非常。至于这几处亦有不少漕挽士卒,往昔以来往州城与码头之间运脚为业,这铁路通后,亦为无业,幸而人数不为多,大抵不下数万人,可使转而为军,庶几不生事为上。此辈人又多为石三郎部下,亦好支吾,不致为有心者煽惑生事。”
高强见他计算周详,心下甚喜。石秀费数年之功,所作的无非就是将这些在各地担负力役地厢兵士兵联结起来,再延伸到市井中去,因此他这所谓的黑社会,其人力资源比后世的黑社会雄厚不知多少倍,也较为有组织。若是用上这些力量,料来亦可免于动乱。
于是次日上朝,高强便奏陈其事,启请于运河沿路大集散处,铺设铁路,用马车运输,铁路车站纵然也用人力上下货物,到底省却许多,更兼速度飞快,诚为美事。赵佶与众大臣细细计之,又说了无数注意事项,比之高强和许贯忠所想的又复杂许多,好在大体上都肯定了这马车的运输效能,张克公且以不能将铁路行于全国为憾。
于是中书拟下诏书,命汴京、大名府、应天府、真州、建康府、杭州这几处量建铁路,由应奉局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赴各处指导铁路铺设,以及车头车厢打造工作。至于一应费用,高强也提出由应奉局代垫,铁路建成后由应奉局派人管理,从来往货物的运费中收取费用,逐年偿还。赵佶与众大臣见不必朝廷掏钱,自无不可。
第十二卷 燕云中篇 第四一章
正当汴京朝廷升平度日之时,西北前线却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和高强也有一点点关系。西北环庆路治所环州辖下定远城,有个党项人头领,唤作李阿雅卜。此人久居西北,也是个大商贩,一则来往西夏和大宋之间走私为生,一则以向宋军供给粮草获利。但自从高强包揽西北大军粮草供给之后,将原先各处军吏与商人直接交易的模式,改成了由他大通钱庄负责从各地商人手中收敛粮草,然后供应给大军,所需钱款从边市贸易所得中扣除的模式。如此一来,杜绝了地方官吏、军吏和大商人相互串通,囤积粮食从中牟利的途经,而百姓也得以经由大通钱庄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和各处分支机构,顺利地出售粮食,不必受官吏和大商人的压价盘录。
这一项改革使得朝廷和百姓都获利非浅,但却损伤了当地大商人和地方军吏的利益,为此自然也起了一些纠纷,不过仗着军中童贯的支持,石秀处置安当,铁腕镇压了几处捣乱之后,也就渐渐安堵,大多数人也可以接受这种比以前赚的钱少一些,但却更为稳当的方式。但是表面上没有了骚乱,不等于背地里没有人暗怀怨恨。这李阿雅卜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复杂处在于他是个党项人,和西夏那边有相当多的联系。事实上,在西北各路,汉族与各异族混居的情形习以为常。宋廷以汉法羁縻蕃部,又建立蕃学以收拢蕃部首领子弟之心,使得其汉化进程加速,这种统治方式相当有效,许多蕃人都乐为宋用。例如已经牺牲的西北大将高永年,便是羌人一部。这名字还是归化以后哲宗所赐的,蕃兵弓箭手更成为西北军的劲旅。
有这样的环境,李大首领的西夏背景也就不象现代改革初的所谓“海外关系”那样引人注目了。然而在这个事例上,却证明了“海外关系”确实很有可能成为叛逃的契机。李大首领在失去了沿边入中军狼的资格以后,恨怨身深,便写信给西夏国统军梁多凌,请他派兵来攻打环州定远城,自己愿为内应。
梁多凌原本是不大愿意来的。须知自从童贯率领宋军进取横山之后,宋军占据了形势之地,城都相连,烽火可望,防守身为严密。而西夏若要侵入宋境,则必须在漠北集结大军,筹备粮草,进而才可以择路入侵,比起以往要打便打的便利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再加上近年来西夏皇弟晋王察哥主持军政,惩于宋军连年进逼,西夏累战不利,正在准备改革西夏兵制和装备,期间严格约束部下犯境生事,因此梁多凌得了这封书信后,身是犹豫。但李大首领所提供的两点信息却促使他下了决心。李大首领提出,他自来多作粮草买卖,于各处掘地藏粮,储量甚丰,大军若来,只须携带路上所需的粮草就可以。到了这定远城,自有粮草可供大军食用,无需筹粮;二则定远城是附近百里的形势所在,一旦定远城攻下之后。周围十余座城寨皆可不战而下,真可谓是有之以利。
于是梁统军终于下定决心来迎,由于仓促不得集结重兵,又怕因为违反了察哥的军令而受到责罚,因此只有万余兵。哪知走到一半,就得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李大首领行事不密,这桩图谋被环庆路转运使任掠给知道了,李阿雅卜知机走得快,任凉没有抓着人,便招集军兵,吩咐他们把李大首领的窖藏粮米统统挖出来,来了个打土豪分田地。
梁统军和李大首领忙活了半天,临了只接了李阿雅卜所部一万多人回来,怜似捧了一个烫手山子,若是丢掉不管的话,好歹他也是党项人,恐怕失了众心。欲待接纳,却又怕宋军报复,最终还是察哥下了决心,择要地建筑盛底河城,就命这梁多凌和李阿雅卜守之。
童贯此时已经回到西北,正在为了从何处下手攻伐西夏而与诸将连日计议,得了这消息不怒反喜,当即上表,说西夏首开边衅,枭厉凶顽,若不以天兵讨伐,恐失天朝体面。表章既上,又连书催促高强,要他加快参议司建设的步伐,不妨将这次对夏作战当作一个契机。
这表章到了京城,朝野一片哗然,近年来西北捷报频传,宋军对河谨羌人用兵顺利,已经成功对西夏形成了三面包抄之势,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没想到夏人居然主动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上至宰执大臣,下到看门小吏,乃至那些“白衣卿相”太学生们,无不一片开战之声。
这一日,高强请来种师道,向他问计,想他是将门世家,又文武兼资,西北山川形势尽在胸中,又在枢密院有一段时间了,当可从大略上提出方略。
种师道得到高强召唤,自知其重,便道:“兵法云:恕不兴兵,今夏人虽云挑衅,却是疥藓之患,倘若就此大举兴兵去讨,无非攻被减底河城而已。此地乃是旧城重建,形势身险,周围有溪水多条环绕,牧草丰盛,倘若我军深入围攻,夏人无须赍粮,只须人携干粮,便可凭其铁骑纵横驰骋其间,我兵若久顿坚城之下,其危可知。是以此战上策,不如不战,陈兵边境,以书责夏人,使归我朝逃人李阿雅卜等,若是不从,则奇兵出夏右厢或其左厢,大掠士马而还,亦足张我朝军威。”
高强一听他又来这一套,常看古书上说什么上中下三策,只要一看到这种词汇出来,上下两策基本上就可以略去不看了,因为咨询者十有八九是选择中策。便道:“然则中策为何?”心说本衙内这捧呕作得不错吧?
种师道显然也是这么想,欣然捋须道:“中策者。调集大兵,攻城器具并集,一面遣使往还,以懈怠其心;而后出其不意,突出保安军和定远军。直至减底河城下,昼夜强攻。倘能于十日内攻取此城。则夏人仓促间亦难集结重兵来援,我师克捷。惟此策须集结重兵,粮草军器转输须时,更须得重将压阵方可。”
至于下策,基本上就是要吃败仗了。照种师道的估计,西夏如今是晋王察哥主持军政,此人深通兵法,慨然有超迈元昊之志。如今西夏筑减底河城以纳逃人,明显是一个陷阱,就等着宋军按部就班地出塞攻城。他那里集结大兵,正好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迎头痛击。若是宋军大败,则十几年来宋军一直掌握主动的战略态势便有望扭转了。
高强见说,沉吟片刻,却道:“似承旨所言,倒是上策为佳。然则此役之后。两国之间又当如何?”
种师道一怔。看了看高强,忽然明白过来:“相公所虑者。莫非是我朝与夏之间从此大战连年,恐怕误了北收燕云的大计?倘若有见及此,这上策却又不是上策了,只因如此一来,便是大战不休。不战至两方疲敝无力,势难罢休。至于要一战而亡,则又是我军所不能。”
高强击掌道:“知我者,种承旨也!方今北地大乱方起,我大宋岂可被区区西夏捆住手脚,不得任意施为?自当设法稳定西北局面。不使动荡。朝廷不劳西顾。自然全心伺候北地。等到燕云收复,辽国纵然不亡,也无力声援西夏矣,那时咱们再回头来对付西夏,恐怕无需动兵,一纸诏书便足以平定矣!”这么说倒也不是全然夸张,若只是要西夏奉表称藩,将原本对辽的礼节拿来对宋,基本上也就是一纸诏书的事,那三十万岁币尽可省下了;倘若要夏弃国投降,大概又是十几年好杀,那时自可慢慢计议。
如此则方略既定,无非走出于中策。高强随后与枢密使侯蒙通了讯息,大家意见相同,便即向赵佶进言,称如今以北事为先,西北战局当使稳定之,但如今夏人首开边衅,不可不予以惩戒,当命使者谴责之,一面潜集重兵,往攻盛底河城,务期一战而克,而后再申前盟,凉那西夏惩于失利,亦不敢如何。
枢密院是“本兵之地”,掌握着军事决定权,如今两大枢密使都是这意见,赵佶自然要掂量掂量。待他向宰府诸臣咨议时,却见前几日还在那里争执不休的众大臣,此时口经出奇一致,都说枢府此议深谋远虑,知所进退,官家应当采纳。表面上看来,这是大家给高强的面子,实际上兵家胜败,谁都说不好,这些人又都是新近得宠之人,权位大多稳固,没有哪个想借机赌一把从中获利的,眼下有枢密院跳出来挑大梁,谁不顺水推舟?反正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