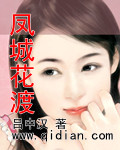凤城花渡-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凤城一带,草狗是指土生土长的普普通通的母狗,一般情况下不会把人叫着草狗的。一种是贬义词骂人的话,另一种就是对关系亲近女人的称呼,要么是丈夫对妻子的昵称,要么是闺蜜之间的戏称。窦兰珍和孙阿珍算得上是闺蜜,小时候一起上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起辍学回家打猪草、带弟弟。
“说说,不要这样神经兮兮。”孙阿珍拍打着身上的鸭毛。
“前几天,我看到你家陈家辉和李秋燕在一起了。”
“去,他们在一起啊?一个村子里的同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孙阿珍装着若无其事。
“不一样,这次不一样。他们两个那个亲密劲儿,那个样子啊恐怕已经做过大人的事情了。”窦兰珍面部表情极其丰富,神秘而又兴奋。有些中年农村妇人,一遇到男男女女的花边新闻就好像猫见到老鼠一般的兴奋,狂追猛打,夸大其辞也是常的事情,不过也不是“无影造机枪”。
“你不要见了风就是雨的。不会吧,我家儿子那个笨样,不会的。”孙阿珍已经知道儿子和李秋燕的事情,乡下人这种新闻比报纸传播的还要快。孙阿珍觉得既然反对没有用,倒不如成全了儿子。
“我不是来混吃混喝的,你不相信,我走!”窦兰珍转身就要走。
孙阿珍拉着她坐下:“坐下来说。”孙阿珍到了一杯水给窦兰珍。
“没有三分三,也不上花果山。李秋燕人长得漂亮,陈家辉能吃苦,对人客气。两家经济上也差不多,也算得上门当户对。”窦兰珍喝一口水,呸了一下全吐了:“全是鸭毛味道。”
孙阿珍哈哈大笑接过茶碗一口喝光:“我习惯了,闻不出鸭毛鹅毛味道的。我说啊,李秋燕头脑是不是那个——”
“头脑怎么了?不是头脑有点那个,人家就是名牌大学生了,会和你家陈家辉谈情说爱?你省省吧。再说,你家陈家辉去年当不了兵,为什么啊?”
这句话触到了孙阿珍的痛处,在农村只要进看守所的就会当着进监狱一般,在婚嫁问题上大受影响,一般人家不放心将女孩子一生交给一个坐过牢的人。
“你这条草狗,你找点好话说说行不行?”孙阿珍话中的“草狗”就是骂人的话了。
“好好,我不说,你说吧。二个孩子半斤八两,坏锅碗配旧锅盖。看样子两个孩子是没有问题的,还不知道人家李秋燕大伯、叔叔、舅舅能不能看中你家宝贝儿子呢。”
“不要废话连篇的,我对李秋燕知根知底的,没有狐臭什么的就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就做个现成的媒人。”风城一代男女谈到婚事总免不了涉及“狐臭”,由来已久。
“你就等好消息吧。到时候成了,不要‘新娘进了房,媒人丢一旁’啊!”
“放心,该你的囍糖啊什么的一样不得少,你去忙吧!”
孙阿珍送走窦兰珍又忙着翻晒鸭毛,太阳快落山了,她又抽空到菜园子里看看,把遮阳的稻草掀掉,丝瓜、辣椒、茄子秧子有一尺来高了,浇浇水。
第十章 修建婚房
1
题字:大凡在艺术品中,茅草屋是美的。无论是国画还是油画,无论是刺绣还是诗歌散文中,茅屋总是令人产生美好遐想的所在,是美极了的风景,是值得讴歌的世外桃源。而身在茅屋中的人,他们绝不会唱赞歌,他们生活在令人心寒的贫困中,他们在无聊闲谈中诅咒与生俱来的财富的不公平和迫切希望有朝一日坐上干净、不怕风雨的瓦房,农民的这种希望在此前延续了几千年。
1
窦兰珍一直没有闲着,东奔西走之后哼着小曲到孙阿珍家回话,孙阿珍炒鸡蛋、红烧鱼招待窦闲珍,陈保良、陈绍奇陪她喝酒。
陈家辉回到家,孙阿珍就将提亲的事情说了说。陈家辉两眼放光,心情激动:“老妈,你太伟大了!”
窦闲珍说:“你慢点激动,他家外婆、舅舅、伯伯、叔叔都没有意见,就是舅妈、婶婶说要有楼房才可以谈婚事。李秋燕听他们大人的,同意订婚,有楼房就行。”
陈保良哑口无言地懵了:一座楼房至少需要花费5万元,家底子多厚多拨他心理清楚。
孙阿珍显然受刺激了:“拼命也要把楼房建起来,不管娶哪家姑娘回来做媳妇都要楼房的。”
陈保良说:“你见了风就是雨,急急忙忙的哪有这么多钱?”
孙阿珍说:“借!赚钱砌屋不如攒钱还债!”
陈保良说:“屋子砌起来就住在债窝里。”
孙阿珍说:“没有出息,三个人赚钱,怕什么,一、二年就能还债!”
陈保良皱着眉头:“屋子砌好了,还要订婚,又是一大笔开销,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孙阿珍板着脸说:“照你这样说。小辉这辈子也娶不到老婆了——窝囊,打一棒,走一步!”
陈保良家的房屋虽然没有在龙卷风中倒塌,屋面的瓦破了、椽子损坏了很多,墙体几处裂缝可以塞进个拳头,显然不能长期住人了。就是没有破损,孩子大了要娶老婆,没有楼房人家媒婆也懒得往你家跑。窦闲珍不是看到两个孩子亲昵的样子,她会来陈保良家说亲?
房子,农村人心头永远的结。
桃花渡人几十年前住在草棚里又叫“茅草屋”,低矮小五架、三架梁的草棚子“进门总把腰来弯,不然撞得你眼睛翻”,狭小的空间,“坐在铺边盛到饭,屁股一鞠到东山”,常常将猪圈和厨房合在一间小屋里,猪养在铺底、鸡鸭关在堂屋里也是有的。老鼠、虫子常常把主人家的床被子当着自己的窝,掀开被子看到蛇,或者蛇、老鼠在你熟睡的时候爬上床的事情常有发生。茅草屋怕水,土坯做的墙用稻草编成的帘子护着,不然雨水一泡就倒。麦秸稻草盖的屋顶一二年就会烂掉,就要请手艺好的瓦匠换掉。茅草屋怕风,大风吹开一个口子,半间屋顶顷刻间掀走了,很多农民就找几块城砖,半片磨盘压在“山头风口”。茅草屋怕火,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燃整个房子,“救火啊!”的喊声并少现,那时候条件好一点的村里都有“水龙”的。一旦遇到火灾,左邻右居齐刷刷地动手,肩挑手提全力抢救,一边救火一边等待“水龙”的到来,水龙一到,人们把取来的水倒在“龙桶”里,四个精壮的男人分开,一头二人压着杠杆,一个救火经验丰富的男人拿着“龙嘴”向快要烧没的茅草屋喷水。
大凡在艺术品中,茅草屋是美的。无论是国画还是油画,无论是刺绣还是诗歌散文中,茅屋总是令人产生美好遐想的所在,是美极了的风景,是值得讴歌的世外桃源。而身在茅屋中的人,他们绝不会唱赞歌,他们生活在令人心寒的贫困中,他们在无聊闲谈中诅咒与生俱来的财富的不公平和迫切希望有朝一日坐上干净、不怕风雨的瓦房,农民的这种希望在此前延续了几千年。
十多年前,桃花渡人种田打工做小生意积攒了一点小钱,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翻了茅草棚,建起了砖瓦结构的房子,比以前的结实些大些。农民的房子从草棚子到瓦房是无法讲究的,鸽子窼大洋瓦,是瓦房就行。没有瓦房是让人瞧不起的,即使暂时建不起瓦房的人家,倘若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装模作样地买几千块砖头,大大方方地堆在屋前屋后,告诉媒婆准备造瓦房,先把媳妇娶回家再说,这就有骗婚的嫌疑。
在农村,房子和老婆是密不可分的,有一个温暖的窝就不怕没有鸟儿来生蛋!
刘正洵祖上是清末一代举人,属于剥削阶级,在一个特殊年代,“坏人”的后代刘正洵一定是“坏人”。刘正洵老房子被生产队没收了做了仓库,一家几口人挤在茅草棚里,他娶不到老婆,等到三十多岁了,生产队才将老房子归还给他,林秀红也不嫌弃他比自己大十多岁,**,等生米做成熟饭的时候就结婚了,惹得一群有意刘正洵的大姑娘把她说得一文不值。
前几年,先富裕起来的人家开始修建楼房,同样不是很讲究的,是楼房就行。二层小楼一旦建起来,鹤立鸡群的风光就是一个广告,媒婆会把门槛踏矮,楼房少主就成了抢手货,哪怕是天生有点小残疾也不会打光棍。没有修建楼房的人家就“买”边远地区的、老少穷地区的女子做老婆,有些人家遇到“放鸽子”的,难免人财两空。也有的“鸽子”在桃花渡生活一些时日,发觉这里是个好地方,男人对她又好,干脆弃暗投明,回家拿了“户口”跑回来成为正式老婆的。很多外地女子嫁给这里的穷小子,一开始有点失望,听说江苏是个富裕的地方,没有想到哪里都存在贫富差距的,本想少受点苦嫁个如意郎,没想到情况不尽人意,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生孩子了,穷小子挣到钱了,自己还能到附近的小厂上班,就死心塌地呆下来过日子。
有时候桃花渡的外地媳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多国部队”——YN的、SX的、SC的、AH的、HUBEI的……
农民造房子不是不会讲究,是没有足够的钱讲究。
2
陈绍奇将荒货处理干净,从夹袄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子,展开一张报纸,一叠百元大钞呈现在孙阿珍面前,陈绍奇把钱推到孙阿珍面前:“阿珍,这钱本来是准备给小辉上大学的,现在给他砌房子用!”孙阿珍眼睛睁得像个铜铃,看着满脸的喜悦公公,再看看钱:“这,我们收下了,你以后要用钱的时候我们来用!”陈绍奇笑笑:“我一把年纪,用什么钱啊,到了那一天,只要你们把我送到高烟囱里就行。还有,你们不要声张,让保善家的知道不好!”宝善是陈家辉的大伯,生的的是个女孩子。
孙阿珍赶紧把钱收起来藏在衣袋里:“不说,我知道。”
孙阿珍东挪西借,陈保良七凑八凑的,这许多年没有开口向人家借过钱,还好,没有费太大的周折,钱基本筹备得差不多了,接着就开工建房子。
“建房三担稻,拆屋一斗米。”拆房容易建房难。
家里造房子需要人手,陈家辉忙起来,一边要收鸭毛鹅毛,一边要照应砌房子。不过,李秋燕哪里还是要天天跑的,一旦遇到李秋燕晚班,陈家辉就等在厂门口,一直接到李秋燕,送她到家关了门,他才回家。
陈保良喊上几个邻居一天工夫就把三间主屋、二间小厨房拆掉了。陈保良父子又在东边的菜园里搭建一间临时帐篷,把一些家具放在里面,临时厨房、卧室、客厅都安排在里面。陈绍奇也一样住在里面,一家四口挤在一起。
农村这样楼房建设起来很快的,无需设计,主人只要跟工头说一声:“和他家一模一样就行”。木匠、瓦匠一齐进场,木匠开始整理桁条、椽子,然后开始做门窗。
首先,陈保良带着陈家辉开始丈量、打桩定点,每根木桩大约一米高,顶头用红纸包着。面积显然比审批的大得多,村干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家不多几个平方?管不了这许多,麻烦越少越好。接着,陈保良在房基堂屋中间放上一把椅子,将香炉端端正正地放到上面,敬上三柱香,朝南方供奉着喜神的牌位,一张红纸上写着:“敕封掌管阴阳刘李周三位喜神之神位”。
炮竹一响,陈保良和陈家辉家就在原来的房基宅地上挖夯槽,父子两人在夯槽里填上碎砖破瓦,请来张渔翁、张宇勤作为打夯手,这是不需要开工资的,农村人相互帮工的事情常见。
开始打夯了,张渔翁先自一声吼:“主家发财砌华堂啊!”
陈家辉、陈保良、张宇勤便和张渔翁一齐拉绳并随声附和:“吆嗨!”
张渔翁:“打夯劲要匀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用力别太大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抬要抬得高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放手轻轻落哟!”
众人附和:“吆嗨!”
张渔翁的声音抑扬顿挫,众人的附和粗犷且深沉。四个男人浑身湿透,全身的肌肉随着打夯歌兴奋着。
这也许是桃花渡听到的最后一次《打夯歌》,此后,电动打夯机取代了人工打夯,打夯的情景成了桃花渡人的记忆。
打夯之后是砌四层砖头作为房基,二层四九墙、二层三七墙,正负零以上就是二四墙,三合土、砖头做砌墙材料。“一米三,放开关”,村里的电工就来放线管,一个房间里设计了二盏电灯开关盒子,堂屋里放吊扇开关、几个插座盒子,黑色的老式线管不费什么事就放好了。
墙体达到三米左右就要上楼板了,这时,孙阿珍早就请好几个身强力壮的人来上楼板。上楼板是一件很费力很可怕的事情,无论是标榜自己专业的还是临时组成的业余队伍,他们都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包工头找来了上楼板的小工头曹杨鸿,他一眼认出了陈家辉。
曹杨鸿西装革履的,扬着脸:“怎么这就是你家!巧啊。”
陈家辉也认出了他:“你——你怎么成了小工头?”
曹杨鸿吹一声哨子:“喂,先把楼板抬进来,一会,沙三,杨二站到东山墙上,顾林生、乔大站到西山墙上,沙风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