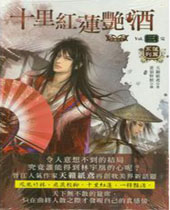十里红妆-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心中一惊,来不及出声阻拦,他已引剑自刎。
只能闭上眼。鲜血喷薄而出的声音,如风呼啸而过。仿佛一声悠长叹息,终于落定了。
“拖下去吧。”我的声音淡漠得连自己都觉陌生。
两名侍卫连忙上前拖走了易铭的尸体。
华文渊仍负手立而立,一动不动。自始自终,他都没有转身。仿佛一切与他全无关联。
在外人看来,这是大义灭亲的觉悟,还是舍车保帅的决绝?但我知道,亲手把曾并肩作战、同生共死的部下送上绝路,他不是不痛苦的。
多年前,他母亲去世那日,他也是这样,在廊上立了一夜。不言,不动,不哭,不笑,静如雕塑,仿佛连呼吸都消失了。那时,我曾在他身后,静静陪他度过长夜。而如今……
时光如河,逝而不返。
命运如弈,落子无悔。
世事逼人,容不得谁多作流连,他不再是那个任性的少年,可以用整夜光阴来治疗伤痛。
终于,冷月斜光转照窗内时,他转身离开。神色平静如常,仿佛之前一切皆未发生。但我注意到,他方才站立过的地方,木地板向下凹陷了近一寸深。
方才,我询问侍卫时了解到,燕国使者的遗物中,并无本该有的议和国书。一旦和谈不成,国书就成了一张废纸。若使者已遇害,和谈自然破灭,刺客无需将它销毁。据目前情况,更有可能是使者本人带走了它。若使者急于赶回燕国保命,也没有必要带走它,而留下路上必需的值钱的物事。如此看来,和谈尚有希望。但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使者在何处?
华文渊紧急抽调的军中人马已经赶到,开始分头寻找使者的下落。
剩下的,便是等待了。此时此刻,再焦虑也无济于事。
我与华文渊来到楼下。庭中芳莎满地,踏上去轻软无声。几枝夹竹桃逸出墙来,花色清明,夜露微泫。花影投落在斑驳的照壁上,淡如水墨。
我故意重提方才之事,问他如何得知刺客与易铭有关。
他淡淡道:“死者手上的胼胝,说明他是用剑高手。而死者鬓角的印痕,说明他很可能是长期头戴银盔的军士。综合这两点,很容易联想到飞鹰卫。另外,燕国使者来到京都的行程安排属于机密。有机会看到那份密报的人,屈指可数。恰巧,前日易铭到我的书房翻看过一些文书。所以,我怀疑到他。”
我注意着他的神色,却再也无法寻得一丝软弱的情绪。对弈时,最危险的情况不是处于下风,而是完全猜不透对方的棋路。而他,就是那样一个危险的对手。
夜深,清辉如水。仿佛此夜与之前的无数个夏夜,并无不同。风乍起,纱袖拂在腕上,轻软如梦。
多年前的夏夜,月光清好时,我会把小文源抱到殿外乘凉。竹帘半卷,玉簟生凉,文源卧在我怀中,不时咿呀学语。殿后有一泊清池,白莲盛开,夜雾浮动。清风度水而来,花香细细,随风漾开。有时,当母亲情绪难得地稳定,会轻轻哼起她家乡的曲调:“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如今,母亲去世已经多年。
庭院寂寂,月光下的青瓦如覆微霜。
檐上挂着一盏竹骨素纸灯笼,于风中飘转,仿佛随时可能熄灭。
五更时,颜慎匆匆赶来,有些艰难地向我启口:“属下办事不力,尚未找到使者的下落线索。”
“继续搜。”
他松了口气,领命退下。
我虽看似镇定,但随着光阴流逝,心中担忧愈来愈浓。由于不能排除华文渊意欲破坏和谈的可能,为了确保使者的安全,颜慎必须在华文渊的人之前找到使者。
大约又过了一刻,华文渊的一名手下前来禀报搜索情况,同样毫无线索。
我不知自己该是喜是忧。
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天亮了。出动数百人搜寻,竟还毫无头绪,未免有些蹊跷。我侧首看向华文渊,只见他静静凭栏而立,目光淡然。仿佛即使云垂海立,也作等闲。
我只能按捺心中焦虑。
这时,他的手下再次到来,但还未走近,华文渊便沉声问:“还未找到?”
谁都能听出那声音里的不悦。这让我极为诧异,因他从不喜怒形于色。
那人答是,似欲辩解。却不料,华文渊目光冷冷,扫过在场众人,叱道:“跪下!”
他一向不怒自威,如此雷霆之怒,实在令人震惊。庭中诸人俱是一愣,随即纷纷跪下,莫敢辩解。满地匍匐的人群中,却有一名侍卫静立于庭下,身影挺拔,萧肃清举,若孤松之独立。
华文渊看着他,微微笑了。
那侍卫施施然扬手摘掉竹笠,月光下,露出年轻俊朗的面容。他不惊不讶,迎着华文渊的目光,莞尔一笑。随即,他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笑意加深。
电光火石间,我终于明白了他的身份。
他当然不会向华文渊下跪。代表燕帝的意志前来和谈的他,只跪我国天子。
他抚掌赞道:“不愧是天下闻名的明德王。”
华文渊淡然道:“之前不知使者大人在此,失礼之处还望见谅。”
“王爷太客气了。在下初到贵国,还未来得及拜谒王爷与长公主,也是有所失礼。”他扬眉一笑,神采夺人,“虽然贵国的治安状况不甚理想,在下不巧遇到入室行窃的小贼,但王爷已及时惩处那贼。如此果决善断,在下叹服不已。”淡淡一语,将遇刺之事一带而过,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方才,他明知所有人都在找他,却藏而不出,是在试探我与华文渊的深浅吧。燕国竟有如此人才,不愧是耶律景的心腹,我却还未查出他的姓名来历。
而华文渊竟能猜到,使者就在此处。若他真的有心加害,而使者又非如此奇人,恐怕,我早已一败涂地……
我暗暗攥紧了衣袂,片刻后松开,若无其事地微笑道:“使者不计前嫌,实是我朝之幸。和谈之事关乎两国社稷,宜早不宜迟。眼看即将天亮,不如启程赶往京都,以早日促成和谈。使者大人一宿未眠,可在车上略作小憩。事出权宜,招待不周,实在抱歉。”
使者朗然一笑,眸光清亮,似有隐隐戏谑:“哪里哪里。贵国的山川风景秀美无匹,又有长公主这样的南国佳丽,令在下见之忘俗,思之忘归。难怪我国前贤,曾称贵国为‘风物繁华地,红粉温柔乡’。”
我微微一愣。曾听说燕国民风开放,男女之情少有忌讳,言语也颇为直率。但他作为国使,我国的官话也说得如此流利,理应知道,这样的话,在我国是极为大胆无礼的冒犯。更何况,我的冷酷无情、骄奢荒淫之名早已远播,人人视我若蛇蝎,怎会有人与我如此调笑?
难道,他是在向我暗示什么?
但他的笑意那样清朗明亮,容不下任何暗影。毫无掩饰地直视着我,宛若欣赏一道有趣的风景。如此气定神闲,仿佛世间一切于他只是倾身俯瞰。我与他相比,竟仿佛只是一本正经地儿戏。
我微微蹙眉,侧首避开他的目光。
“马车已经备好,不知使者大人是否还有要求?”华文渊的声音静静响起。
他终于收回目光,轻笑道:“不敢再劳烦了。”
我暗暗松了口气。夜风徐徐吹来,背上已一片沁凉。
走出客栈,上了马车,正要放下车帘,却见燕国使者径直走来,在众人的目光中,微笑着向我递来一物。我微觉惊讶,还是伸手接过,见是一条上好的琥珀香珠手串,晶莹沉郁,似曾相识。静了刹那,蓦然忆起,这是昨夜洗漱更衣时,我随手套在腕上的……
心念电转之际,回想起那个在上楼时扶了我一把的侍卫,顿时醒悟。
倏然抬头。
石街之上,清凉月光宛如河流。两侧屋檐高低错落,连绵起伏着没入夜色。街边树影之下,月光斑驳如霰。他迎风而立,衣袂飘然,身影颀秀挺拔,如一把麟胶乌漆的宝弓,弦开明月、箭激流星,柔弛之时也蕴含着巨大的力量。一缕笑意于他唇畔隐现,话音清朗,语意悠然:“在下姓白,单名一个京字。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
闻言,我重重一震。
不待我回应,他欠身一礼,洒然登车而去。举止间如此从容,仿佛只是闲看风月。
望着马车消失在长街尽头,我静默半晌。直到察觉了华文渊的目光,才回过神来:“起程吧。”
车帘垂下,隔断了视线。靠着车厢内的鹅羽软垫,我倦怠地阖上眼。
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
“十二城主”,正是耶律景与我联系时所用的代号。白京,合为景字。
不错,是他,也只能是他。
燕国九皇子耶律景,竟亲自来了。
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串,忽然觉出细微的异样——原本光润的琥珀香珠,似乎有些粗糙。凝神细看,只见其中几粒串珠上有隐约刻字。
逐一辨认,终于连字成句:七日酉时,水月轩见。
四、穆如清风
回到京都,已是翌日午后。和谈之事不宜拖延,我顾不上休息,正欲让鸿胪寺立刻启动准备已久的国礼仪典。这时,一名御前伺候的内侍匆匆赶来,说文源昨夜又犯病了,情绪很不稳定,把自己关在清凉殿内,不准任何人进去,一直没有用膳也没有喝药。
文源虽然年少,却善识大体,懂得进退分寸,鲜少如此任性。可见情况不同寻常。我以使者一路奔波、需要休整为由,将国宴推迟到明日,将使者的接待食宿交给颜慎安排,立刻动身入宫。
清凉殿是避暑之地,临着太液池,水风徐来。错落楼台间,遍植青桐、湘竹、垂槐与桫椤,袅袅濯濯,绿蜡生烟。外头日色如金、暑气逼人,殿内草木成荫,清香氤氲,自生幽凉。头顶空影叠翠,叶片宛如冰纹琉璃,绿意清透。入目便是一幅丹青闲笔,淋漓湿衣。
见到我,殿内的宫女内侍齐齐跪地,唯一名少女独立阶前,神色宁静。烟碧轻罗宫装,外笼两层薄绡淡青裙幅,重叠出深深浅浅的烟霭,浮绣着蓬莱灵云的清淡纹样。臂上挽着水青软罗披帛,长曳及地,迤逦如水。整个人似一枝新叶柔柳,只合身在轻风明月之中、白露泠泠之时。若非她鬓边那支鎏金凤钗,很难让人联想到她的身份——大齐皇后,阮氏秋水。
信陵阮氏,世代簪缨,门第高华。当朝三位宰辅中,一位姓阮,一位与阮氏联姻,足见其势力之大。阮氏一直是我最为重要的支持力量。册阮秋水为皇后,固然是我为了巩固与阮家的联盟,但她是阮家庶女,又比文源大两岁,没人想到我会独独选中她。
记得当初文源刚登基时,我将阮家三位待字闺中的小姐一起召入宫中。另两位都环佩珊珊、行止款款,过分的矜持谨慎。唯她一袭素衣,神情宁和,举止从容,颇见林下之风,却又恰到好处,不曾逾礼。我让宫女取来三把笤帚,请她们分别打扫殿堂。另两位阮氏小姐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而阮秋水默默执帚扫地,仿佛这与在闺中闲坐绣花一般自然。
而今,已然母仪天下的她,全无骄奢跋扈之气,沉静娴雅,似其闺名一般,秋水澄泓。她是极少的几个我能信任托付的人之一,因为她的地位完全维系在文源的身上,与我们利害攸关。
她自然知道我为何前来,无需多言。
想来她也是一宿未眠,神色略显疲惫,但声音依然温雅清晰:“陛下在殿内,我劝不住他。”
文源一向尊重她,这次竟连她的话都不管用。
我定了定神,觉出她话中的自责之意,轻言道:“你已尽力。我去劝劝吧,你命人将药膳备好便是。”
她颔首:“一直备着的。”又有些紧张犹疑,蹙眉道:“陛下他……”
甚少见她有如此忧虑神情,关心则乱。她对文源的情意与关切我一直看得分明,这不是可以伪装的。这是我信任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她不会做出伤害文源的事情。
此刻,什么话语都是多余。我拍拍她的手,让她放心。
宫女内侍皆静候于殿外,我独自走上殿前石阶,用力推开了厚重的镂花填金红檀殿门。轻微的吱嘎声中,心情莫名地沉寂下去。殿内,重重湘帘深垂,光线有些暗。门外照入的日光,落在乌黑如镜的平金砖上,静泊如水。
我挽着曳地的留仙裙,跨过朱漆柏木门槛,丝履踏入那泓水光中的刹那,有濡湿鞋袜的错觉。向前走了两步,若褰裳涉水。还未出声,忽有一物向我飞掷而来,险险擦着我脸边掠过。伴随着坠地碎裂的巨大声响,是文源冷厉的声音:“阮秋水,朕不准你进来,你没听到么!”余音在空荡的殿内悠悠回响,良久不绝。
文源从小柔顺温和,我从未听过他这样的声音。按下心中惊诧,我扫了一眼地上之物,原来是个古玉纸镇,已摔得粉碎。随后,是压抑的咳嗽声,我听得隐隐心惊。
寻声望去,双目终于渐渐适应了晦暗的光线,隐约可见文源身着素白寝衣的身影。他并未戴冠,长发披散着,抱膝坐在案边,地上散落着书册纸笔。幽深的殿堂中,他的背影单薄寂寥,像是随时会融化的春雪。
我知道他的艰难。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