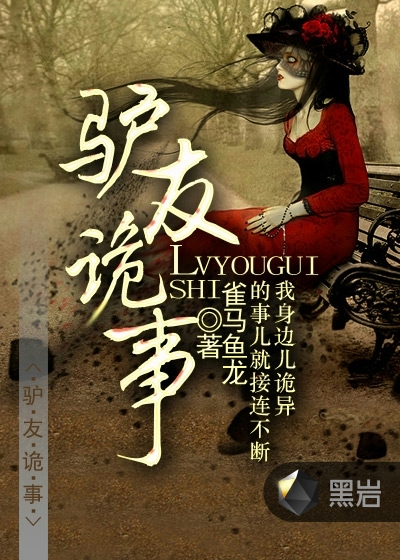五声岛遗事-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国老师,我不想像一个杀手一样活着!”
从获忽然转过身来,她对国满说:“但是,在这之前我必须杀了丁放。只有杀了他,我才会觉得混乱的局面已经结束,生活又可以重新开始。”
她用热切的目光看着国满,内心充满了痛苦。她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她已经不考虑未来,她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杀掉丁放,这几乎成了她活下去的信念。这个信念当然可以支持一段时间,但是,丁放真的死了以后可怎么办?人生需要一个目标,完成了这个目标而没有下一个目标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国满静静地看着从获,她的目光像妈妈一样温和亲切,又带着老师的那种威严慈爱。她就那么看着从获,像神明一样看着等待被拯救的凡人,并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却又像是已经说了一千句一万句,似已穷尽所有的真理。
从获在原地慢慢蹲了下去,她双手抱着头,轻轻啜泣起来。
国满缓缓走到从获身边,她蹲下身子,伸出双手轻轻将从获拥在怀中,轻轻地说:“哭吧,哭出来吧,女孩子的眼泪就是用来对付悲伤痛苦的。把所有的眼泪变成情绪流出来,就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现实。”
从获没有放声大哭,其实她现在根本哭不出来,她只是觉得难受、压抑,她不知道要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情绪。哭应当是人类保护自我的一种本能吧。她没有拒绝国满的拥抱,她几乎没有被人抱过。她在国满的怀抱里只感觉到了不适,然后,她借抬头的机会离开这个怀抱,慢慢地装作自然而然地站了起来。
国满随着从获的动作缓缓站起,她给从获递了纸巾。
“谢谢。”
说这话的时候,从获已经平静了许多。也许,她并不需要别人的安慰,她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所谓“悲伤”。
“你的承受能力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不知为何,国满突然这么说。
“也许是我天性凉薄。”
这是从获突然想到的词,她在看小说的时候见过,现在用它来形容自己的个性,她觉得说不出的贴切。
“不要随便给自己下定义。”
国满说,“有些词不能乱用,它会扰乱你的心绪,让你误以为事实就是那样。人太复杂,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定义。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是一种刻板印象。”
“这些话只有从国老师口中说出来才不会让人觉得别扭。”
从获已经擦拭过泪痕,现在的她轻松了许多。她与国满探讨过不少问题,接触过不少属于国满的新观点,倒不会觉得国满说的有多么奇怪。
“如果人人都持有这样的评价——”
国满顿住,微笑着看了从获一眼,才接着说:“这个世界就没法儿待了。”
☆、宠物
五声岛纪年572年的元旦,从获不在战场上。
持续的暴风雪终于停了,地面上积了厚厚一层雪,铲雪工人正在工作着。从获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病房楼下堆雪人,国满在一旁看着,守卫远远地站着。
雪人已经有了大致的模样,用那戴着厚厚手套的双手在雪人身上摆弄时,从获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
住在父亲私邸的时候,堆雪人、打雪仗这些游戏会被枯燥无味扫雪行动取代,兄弟姐妹们一起埋怨爸妈,却不敢让爸妈听到,这是多么奇特的场景。好在年幼的从获就已经有将无聊变成一个人的有趣的天赋,自娱自乐般扫雪能打发很多时间。
学生时代与雪有关的事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与许甬的初次见面。具体的情节只记得大概,许甬最初的模样还是模糊不清,也许永远都不会再有关于那时的清晰记忆。
蓦然地,从获脑海里快速闪过一个红色的身影,小小的,红衣红帽红彤彤的脸蛋,在夜色下堆着雪人,然后是漫天的血色飞舞、一地猩红。她头一痛,不敢再想下去。
大湾江畔那一夜,是永远的噩梦。
国满走到从获身边,轻轻拍了拍从获袖子上沾到的雪,笑着说:“这羽绒服的手感,怎么那么像我养的那几只鹅?”
从获立刻想起在国满家里见到的那四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白鹅,然后她想到第一次在国满家里吃烧鹅的情形,继而想到国满上次送来的烧鹅,不由打了个寒颤。
“国老师养鹅是为了满足食欲?”
国满笑笑,摇摇头,回答说:“我养的是宠物。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我得赶紧把它们杀掉,在生出感情之前。”
她说的很自然,最后一句明显有所强调,听来让人不寒而栗。
从获眼神微冷,不动声色地低下头给雪人戴上一顶帽子,“国老师对人也是这样吗?”
许是意识到自己一时失言,国满没有立即回答,她静静地看着从获的动作,敛起了笑容。
这时候,一个守卫跑过来说,河源出事了,丁放卷土重来,发动政变,杀了现任领主,重新控制河源。
这个消息立刻吸引了从获的注意力,她一把将已经完成大半的雪人推倒,好像那不是一个雪人,而是丁放的脑袋。
国满似笑非笑地看着,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她一点儿也不好奇不慌乱,就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她看着从获的背影,给人的感觉是:她对从获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河源发生的那些事。
曾经威风凛凛带兵进入河源的郑氏第三子明榕又带着妻儿亲信仓皇出逃,郑氏领地上的主要城市迅速落入丁放魔掌中,这样的变化太快,像梦一般不真实。
从获通过守卫联系上母亲丁尚思,就算之前有过不愉快,这时候还是要确定一下对方是否平安。
“我和你爸都好,不要担心。”
丁尚思的声音一如既往平静,一点也不像刚刚遭逢大难仓皇出逃的人,她叮嘱从获:“你就好好待在医院里,许城方面的人会保护你的安全。”
这一次从获没有主动请战,她已经明白,如果需要她上战场,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碍父母做这个决定。反之,没有任何有效的理由可以支撑她说服父母。她现在还是被父母捏在手心里。
“事实证明,丁放不死,郑氏不宁。”
国满回顾着从获说过的话,微微感慨了一番。
“接下来,你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
从获说,她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她现在寄人篱下,又能做什么?
“也许,你的父兄会像之前讨伐丁放那样,再次组建讨逆军,依靠许氏和韦氏的支持打回河源去。这个时候,你应该可以做点什么。”
从获冷笑一声,得而复失与失而复得是什么样的感觉,估计这次五声岛上的人都可以有深切体会。她现在想的是丁放为什么能够在消失了几个月后卷土重来,那些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的讨逆军士兵就那么不堪一击吗?还是郑氏子弟太无能,竟然连一股残余势力都对付不了?
国满说:“按常理,许氏和韦氏都得支持你父亲的义举。然而,五声岛上的人已经受够了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未必能容许逃难的日子重现。所以,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要有心理准备。”
过了一会儿,从获突然说:“如果丁放死了,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已经发生的事情,来不及阻止了。杀掉丁放,不过解决暂时的危机。你要去做的话,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只是,你想过要承担的后果吗?”
国满突然提到“承担杀死丁放的后果”,从获感到奇怪。
“杀了丁放,在你看来是一个看似无比正义的行为,但未必是所有人都持这种看法。”
从获看着国满,等她说下去。
“这几年里,想要丁放死的人不少,付诸行动的也不少,可没一个真正要了他小命的人。就像这几年的战争,拖拖拉拉,打打停停,好多人都说要尽快结束这种局面,该拖的却还是拖了几年。”
国满的话里有强烈的暗示,然而她只是暗示,却什么都不肯明说。今天的国满很奇怪,从“宠物”话题开始就很奇怪。
一直以来,从获心中的国满老师是个值得尊敬而又琢磨不透的形象。从陌生到亲近,并没有花掉多少时间,但那令人看不透、搞不懂的温和笑容一直没有太多改变。说句实话,从获在依赖国满的同时,并没有搞清楚国满的动机。没有人会毫无理由地对另一个人好,从获想到那几只大白鹅,头皮发麻,心里发寒。
“你在害怕?”
国满注意到了从获的反应,就像看透了从获的心思,她说:“是因为我说养宠物的事?”
从获不语,国满接着说:“人是奇怪而别扭的生物。”
然后,她轻轻笑了起来,一如既往,却饱含了别的意思。
从获的心像是被人用器物狠狠敲打了一下,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情商是不是统统没有得到基因遗传,她开始怀疑这几年发生的事。她本来就是个不够自信而多疑的人,军旅生涯给她改变了以往对自己印象的错觉,现在看来,一切如旧。
“或许,我是应该保持‘国满老师’这个身份的原始状态。”
国满似乎轻轻叹了口气,在她随手关上门离开前,她回头对从获说:“我们确实很投缘,只要你有需要,我们还是可以聊聊。”
从获没有回应,关门的声音传来,很轻很小,像蚊子叮咬人的声音一般。病房里现在只剩下从获一个人,她本来呆呆地望着墙壁,现在猛地窜到房门后面,国满确实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获猛地灌了一杯水,冷水,透心凉的感觉让人在一瞬间清醒过来。她一屁股坐到铺了软垫的凳子上,心想自己这次是惹恼了国满老师。她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来之不易,要想维护长久的友谊更是要花费大量的心思。女性之间的友谊更是脆弱得可怜可恨,一言一行的不慎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也许是源起于自己都不在意的小事。
她忽然感到害怕。从获还是个缺少友谊的人,所以格外珍惜友谊。甚至可以说,她认为自己在意友谊甚于亲情。因为从前的失误和不肯低头,她曾经被迫抛弃过两段友谊,那是多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啊!也许太在意太珍惜,到头来就会变成不可补救的伤害。
从获开始觉得愧疚,她以为是自己的不信任的言论导致国满老师失望而离开,她由此开始深深地反省自己的言行。因为出现了这些想法,最初对于国满老师的怀疑情绪被替换掉了,河源发生的事也被放在脑后,一堆乱七八糟的思绪开始占据心头。
医院里安排的守卫并不严密,所以从获有办法跑出去,但迄今为止,从获没有产生这个念头。她不是被人限制了自由,而是自己限制了自己的自由。现在,她的眼睛开始盯着外面的世界。
从获终究没有办法鼓起勇气打个电话给国满,因为她不知道要说什么。国满老师那种带有预测性质的言论已经留在她的脑海中,她可以想象国满老师是一个多么精明能干的人,所以今天的事像一个疙瘩,刻在了从获心里。
直到若干年以后,从获才知道自己当时的感觉并没有错,但为时已晚。因为在那时,一切已经成为定局,除了做最后的挣扎,悲壮地迎接未来,她没有任何办法。
☆、办法
一个雨后的下午,空气清新,从获在许城南湖公园的湖心亭上见了许甬。托丁放的福,从获现在已经是自由身。
因为刚下过一场大雨,又是周一,公园里人影稀疏。欢快地叫唤着的各色小鸟落到草地上觅食,鱼儿在水里游着,一派欢乐景象。
“钉子没有拔/出/来,血倒是先流了一地。”
许甬神色黯然,他看着不远处轻轻扑打翅膀的黑色小鸟,目光落在一片竹林里。在湖心亭可以观察四周的情况,同时也处在别人的观察之下。
从获知道这话意味着最近一次刺杀丁放的行动又一失败告终,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太多次,不知道是丁放太狡猾还是“拔钉子小组”太弱,每一次看似天/衣无缝的行动最后都会被戳出一个窟窿来,流一地的血不说,还引来了外界对这种模式的批评。
“这几年,为了杀掉丁放,你的人损失很大吧?”
“连你也说他们是我的人,难怪——”
许甬背对着从获,双手支撑着亭子的护栏。从获看不见他的表情,只听他接着说:“我们最初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行动小组,没有所谓的负责人,为了行动方便,他们推我为联络员。就是这样,我们内部分工还是很明确的。但是外界对此产生了许多误解,有些人甚至质疑我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天哪,我得有多冤枉啊!”
也许许甬的话里透露出了一丝委屈与无奈,从获并不是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