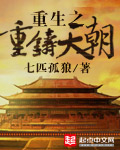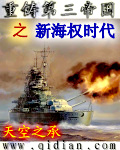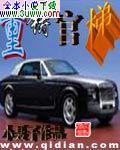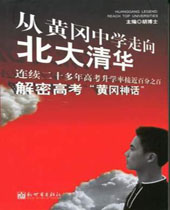重铸清华-第1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会受到礼遇和赏赐;不磕头。就会受到慢待甚至被驱逐。渤泥国王(今天的文莱一带)来华朝见明成祖朱棣时就首先按照中国的礼仪制度规矩的行跪拜之礼,而后才能致辞。其后明成祖对这位渤泥国王有如下观感:“朕观其谈吐文雅。体貌恭顺,举止合乎礼教,可见他已摆脱了蛮夷习俗……渤泥国王这样率领妻儿、兄弟、亲戚和陪臣。一起跪拜于陛阶之下,却还不曾有过。这位国王精诚所致,可谓之于神明。”于是乎永乐大帝也赐予渤泥国王以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而就是这种跪拜之礼,发展到了清代更是有所加强。清代把觐见皇帝规定的礼仪叩头次数增加了三倍,即三跪九叩之礼。只有行这种大礼,也只有这一种礼仪,才能够尽到藩属臣邦对中国天子表示敬意的本分,1793年马戈尔尼率团访华,要求觐见乾隆皇帝,但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帝在得知他这一态度后,谕令办理接待事务的大臣用下述理由来开道对方:“凡是四方藩封之国,前来天朝进贡和观光者,不但陪臣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即使是该国的国王亲自来朝,也必须躬行此礼……如尔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礼,那就不能表示尔国王谴派尔等航海远来输诚归顺的诚意。不仅各藩属国使臣讥笑尔等不懂天朝礼仪,恐怕我朝官员也不会允许。”最终因马戈尔尼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双方不欢而散。乾隆帝降旨令其早日出境。当然马戈尔尼的此行目的也没有达到,更不用说是受到像渤泥国王那样的公侯规格的礼遇和丰厚的赏赐了。忒杯缄
咸丰帝饱读史书和儒家经典,当然知道这些,更明白三跪九叩之礼是 清朝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唯一礼仪。在他眼中,礼代表着上下等级秩序,是自己统治的标志,如果没有了礼,就连自己皇帝这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都无法解释。礼在咸丰帝心中的地位是我们今人所无法想像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中的这句话实际上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而天下是“九州分野”以内的华夏人和这一分野之外的夷狄共同构成的。华夏人处于天下的中心,相对于四周的蛮夷来说,他们便是“中国”,中国的皇帝们也便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说文解字》称“夏者,中国之人也。”正是华夏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的明确阐释。而四周那些不曾开化的部族,依其与中国的方位关系,则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这样就形成了华夷国际秩序。而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严格按照三纲五常所要求的君臣关系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千百年来,中国的皇帝们,甚至是庶民百姓都把这种等级性的华夷国际秩序视为天经地义的。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是古代中国人所不曾梦想到过的。宋人石介在《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传统中国人对华夷秩序的信念是何等的明确和坚定。因而,中国与外邦诸国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以尊临卑”的关系,而没有其他第二中选择。
ps:
蒋用庵刺史是常州人。一天,他和四个朋友在徐兆潢家里喝酒。徐家精通烹调技术。尤
其烧烹河豚更是拿手。这次酒宴上也摆出了河豚。六个人贪河豚肉味鲜美,各各举筷大吃,
可又担心中毒。
忽然,一位张姓客人陡然倒地,口吐白沫,发不出声音。大家都以为他中了河豚毒,急
忙寻了粪汁来灌他,可他没有苏醒过来,其他五人害怕地说:“宁可在毒性发作之前吃药。”
于是各自捏着鼻孔喝下一杯粪汁。
过了很久,张客人居然苏醒过来,知粪汁解毒之事,失笑道:“我素来有羊癫疯,常常
发作,并不是河豚中毒呀!”
☆、三十三、天津条约(八)
这种华夷国际秩序到了清朝又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邦”。对于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清朝在官方文书中称为“夷”,如英法美各国分别被称为“英夷”、“佛夷”、“米夷”。根据传统的这种华夷国际秩序,在对外关系上,清朝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当然不会承认像英法美这样的国家和自己有平等的地位。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就是管理像蒙古、西藏等事务的理藩院。因为在清朝皇帝眼里,这些国家只不过是藩部的延伸。鸦片战争失败后,原来的中外格局已经破坏,但道光帝只做了一些修补:以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总之是依然在坚信和维护着这种不平等的华夷国际秩序。
现今这些夷酋提出公使驻京这一要求,定是“意存叵测”因为在咸丰帝所读的史书、经典中,根本没有像西方这样的常驻使节。如果硬要说有的话,那常住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咸丰帝心中明白, 第 256 章 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后者身份,这样推理下来,他们只能是敌国派来的钦差。“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又受挟制。”咸丰帝甚是担心。但事与愿违,咸丰帝越是不准公使驻京,英法就越要求驻京,这更加剧了咸丰帝的疑心。最后被逼无奈。在臣子奏折上朱批到:“若必欲公使驻京,则俄国成例惧在。但能派学生留驻,不能有钦差名目……听中国约束,专令学习技艺,不得与闻公事。”一切理由全在其中,因为按照咸丰帝的理解。这些西方的常驻使节是敌国派来专门监视自己的钦差,是可以在京城里任意收税、干涉政令、拆迁民居、建立高楼、部署各类武器的。总之是如同太上皇,可以为所欲为。而中国也将沦为外夷监守,自己也将变成历史上的 第 256 章 壮着胆子问了一句:“皇上?天津那边来的军情是?”
皇帝摇了摇头,闭着眼睛,殿内的蜡烛燃地室内恍如白昼,过了许久,方才开口,只是突然之间,皇帝都没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然哑了,苦涩嘶哑的声音在勤政殿里头响起。
“军机处拟旨:着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礼部侍郎庆海、并耆英赴天津与各国谈判,钦此。”
肃顺不敢置信,望着咸丰皇帝膝行了几步,大声道:“皇上!?!?!?!”本来被自己已经说通了,怎么会突然变卦!
皇帝睁开了眼睛,眼中全是无力感,他觉得自己的力气已经在坏消息哪里用完了,“英国舰队在渤海上攻击了上海运来的漕运船,并号称,若是再不和谈,将会一直封锁到大清愿意和谈为止,”咸丰皇帝闭上了眼睛,“就这样办吧,朕乏了,你们跪安吧。”
“外托恭顺之名,内挟要求之术。。。。。。天津郡城,无一日之水,无隔宿之粮,城外廛肆毗连,河路错杂,战守两难,不得已仍行议抚,但使津郡能羁縻一日,京师则筹备一日。。。。。。臣与津存亡自誓已久,非敢以言抚为退缩求生。”
圆明园勤政殿,一个小太监悄无声息地疾步走进勤政殿内,手里还捧着一叠新到的折子,等到掀帘的太监掀开帘子,东暖阁里面传出来皇后朗朗地读折子声音,小太监放慢了脚步,走到里间,里面伺候的双喜接过折子,放在了炕上的小几子上,咸丰闭着眼睛,眉头紧皱,听着坐在对面的皇后的声音。
皇后读完了折子,放下,静声看着皇帝,“皇上,谭廷襄的折子,您的意思是?”
“要停止贸易,关闭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四个通商口岸,这法子不行,”咸丰皇帝摇了摇头,否决了谭廷襄的提议,“如今不论说关税如何,单单宁波府买进来的西洋火炮就是少不了,如何能停止贸易,”如今发逆已经被压制在江南一带,若是停止贸易,恐怕又要猖獗起来了。
“宣战么。。。。。。目前还不到时候,”皇帝继续摇了摇头。
杏贞连忙说道,“两广的黄宗汉上折子说,提议速速克复广州,使英法等国震慑再出面开导。。。。。。”对于前世公知精英产生最多的法律生来说,自己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例外,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利益至上者,杏贞清楚的明白如今和英法两国开战确实是不明智之举,国内的太平军和捻军都是冷兵器时代的反叛,朝廷军队到现在举全国之力还没有把金陵的洪秀全剿灭,怎么能把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蒸汽强国,打到家门口的英法两强打到?
“皇上,臣妾以为宣战不是要真和洋人动刀动枪,”杏贞说了自己的意思,“宣战只是表明咱们大清的一个态度,要强硬到底,天朝仁义之极,就算是不通教化的洋人,咱们也应该是先礼后兵,”杏贞说话圆了皇帝的面子,总不能说皇帝怕吃败仗才迟迟不肯宣战吧。
ps:
甲和乙素不相识,甲问乙姓什么,乙答道:“孙。”
乙问甲姓什么,甲说:“不敢。”
乙说:“问君姓,君为啥如此谦虚?”
甲还是说:“不敢。”
乙再三询问,甲便说:“祖。”
乙恍然大悟:原来他是用姓来讨便宜,便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祖我孙,我孙你祖
罢了。”
☆、三十三、天津条约(九)
皇后到了勤政殿的时候,军机大臣们已经全都散了,五月的春夜已经不会凉,斜月朦胧地罩在勤政殿高耸的飞檐上,地上出现了古怪而沉重的阴影,殿前的御前侍卫挎着腰刀肃然挺立,杏贞看不到殿内的烛光,杨庆喜沉重地出来打千行礼,“皇后娘娘,”杨庆喜的声音隐隐带着哭腔,“快去瞧瞧万岁爷吧。”
“皇上在哪里?”杏贞平静地开口,边上素来最为跳脱的帆儿也不说话,只是拿着点亮的宫灯。
“在东暖阁里头,什么人都赶出来了。”杨庆喜委委屈屈地说道,脸上的红印子在月光之下清晰可见,“万岁爷刚才还发作了奴才一顿。”
“你快去用冰敷一下,别叫人瞧见了,这里有本宫,叫如意和双喜伺候着,”杏贞抬头瞧了瞧天上的月亮,不远处几朵漆黑的乌云慢慢地弥漫过来,吞没了月光,“帆儿,我们进去。”
“是。”
杏贞缓步走进东暖阁,只见咸丰皇帝枯坐在炕上,阁内只是点了一盏豆大的油灯,其余地方漆黑如墨,只有皇帝身上的明黄衣裳和他惨白的脸色在摇曳的灯火中微微发光,咸丰听到动静,缓缓睁开眼,见到是杏贞,毫无动作,只是开口说了一句,“皇后来了。”
“是,臣妾来了,”杏贞行了一礼,皇帝没有发话,自己也自顾自地站了起来,挥手让帆儿点灯,接连的几个含着龙涎香的蜡烛点了起来,东暖阁里头变得明亮了起来。皇帝没有动怒,只是微微皱眉。复又闭上了眼睛。
“皇上,”杏贞示意让帆儿出去,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她也不坐下,就站在地上对着皇帝开口了。
“皇上。您就这样对着洋人低头了?”杏贞问地毫不客气,丝毫没有以往的婉转和蔼。
“还能如何?”皇帝不以为忤,语气萧然,可见是已经对着局面失去信心了,“大沽口虽然败了,毕竟天津未失,大约还能一战,可是。”皇帝依旧闭着眼睛,只是眉宇间剧烈地抖动了起来,“朕偏偏是忘了漕运!如今金陵在发逆之手,只能海运至京,如今英国人已经示威,若是再不和谈,就要封锁漕运,如此一来。北京必然大乱,朕想到如此之结果,不由得阵阵后怕。如此一来又变成先帝时候的故事了,”皇帝缓缓地平静了下来,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还能如何?只能是听他们的了,怎么,皇后你还有法子?”
杏贞没有回答皇帝略微不满的问题。不卑不亢,站在地上说起了别的事情,“当年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越国几乎全灭,勾践忍辱负重,带着夫人和大臣范蠡去吴国服苦役。越王给阖闾看坟,给夫差喂马,还给夫差脱鞋,服侍夫差上厕所。勾践三人受尽嘲笑和羞辱。为图复国大计,勾践顽强地忍耐着吴国对他的精神和**折磨,对夫差更加恭敬驯服。勾践回国后,时刻不忘吴国受辱的情景。他睡觉时,躺在乱柴草之上,夜夜不得安眠,睁眼便是励精图志,早日报仇!勾践在自己的屋里挂了一只苦胆,每顿饭都要尝尝苦味,提醒自己:不能忘了在吴国的苦难和耻辱经历!失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皇上,如今京畿未失,天津依然在僧王手里,天下大事,仍有可为之机,若论局势艰难,如何能比刘邦被项羽追赶,不得不丢下汉惠帝和公主?若论无计可施,皇上比得过当年的越王勾践吗!”杏贞说话声音越来越高声,话中的深意惊得咸丰皇帝瞪大了眼睛盯着杏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