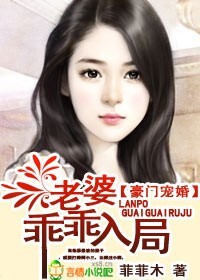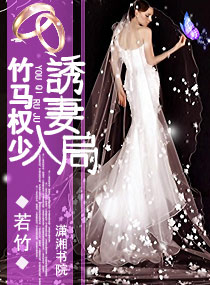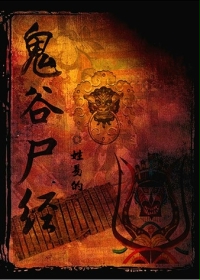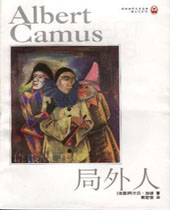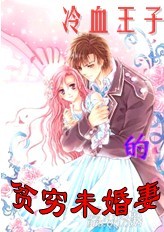鬼谷子的局-第1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鬼谷子侃侃而谈:“观天下就如观这远山,视这深谷,不能单靠眼睛,要用直觉,要用心。观远山,不必上远山,看深谷,也不必下深谷。反过来说,若是真的上了远山,下了深谷,你只会观不见远山,看不到深谷。就好比钻进林中,但见树木,不见林莽。要想看到林莽,唯有站在此处绝顶,用眼望下去,用直觉望下去,再用心望下去。”
鬼谷子一席话如醍醐灌顶,苏秦、张仪心中皆是一亮。
苏秦应道:“弟子明白了,审时度势,须用心眼,不能用肉眼。”
“是的,”鬼谷子微微点头,“心眼也叫慧眼。口舌之学,在服天下;要服天下,须观天下;要观天下,须洞悉天、圣、人三道,须熟谙捭阖之术。你们四年所学,仅是嘴皮功夫,说人说家尚可,说国则显不足,若以之说天下,必贻笑大方。”
苏秦、张仪面面相觑。
有顷,苏秦问道:“请问先生,何为天、圣、人三道?”
“天道为自然之道,也即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之理;圣道为人世之道,也即安邦定国、天下大同之理;人道为人生之道,也即安居乐业、为人立世之理。此三道相辅相成,失此离彼。远天道,圣道困;远圣道,人道难。”
诸人各陷深思。
过有一时,张仪复问:“请问先生,何为捭阖之术?”
“捭即开,即言;阖即闭,即不言。捭阖之术,就是张口闭口之术,习口舌之学,知捭知阖,最是难得。”
张仪急道:“张口、闭口有何难哉?”
鬼谷子连连摇头:“难!难!难!”
苏秦问道:“请问先生,难于何处?”
“难于你必须知道何时应该张口,何时应该闭口;你必须知道应该张口时如何张口,应该闭口时如何闭口。宫廷之上,一句话入心,大功唾手可成;一句话说错,脑袋顷刻搬家。常言道,福从口入,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理儿。”
苏秦怔了下,接着问道:“这……捭阖之术可有诀窍?”
“若要明白捭阖之术,先须明白捭阖之道。”
“何为捭阖之道?”
“捭阖之道,也即天、圣、人三道,就是宇宙万物的阴阳变化之理。任何事物,都离不开捭阖,也都可以用捭阖之道进行解析。阳为捭,阴为阖;白昼为捭,黑夜为阖;开始为捭,终结为阖;善为捭,恶为阖;春夏为捭,秋冬为阖;月圆为捭,月缺为阖;向上为捭,向下为阖;长生、富贵、荣耀、安乐、利益、希望为捭,死亡、贫穷、毁弃、痛苦、损失、失望为阖……”
“先生,”玉蝉儿抬起头来,望着鬼谷子若有所思,“可否这么说,凡与生相关,均为捭,凡与死相关,均为阖?”
鬼谷子微微点头:“有这么个意思,但捭阖之道远不止此,你们唯有慢慢体悟,方能明白其中妙理。”
张仪再问:“捭阖之道,具体到口舌之中,可有因循法则?”
“当然有,”鬼谷子徐徐言道,“捭阖之道,其因循可依阴阳变化法则。万物或捭或阖,或捭中有阖,或阖中有捭。具体到口舌之学,其法则是,凡朝成功方向的谋划,均叫捭,凡朝挫败方向的谋划,均叫阖。”
张仪恍然悟道:“先生之言,如开茅塞!”
“习口舌之学,捭阖之道就如一扇大门,你们唯从此门进入,方能领悟其中玄妙,方能掌握捭阖契机,方能做到何时张口,何时闭口,方能做到开口时如何开口,闭口时如何闭口。”
苏秦、张仪双双叹服:“弟子受教了!”
自于猴望尖得传捭阖大道之后,苏秦、张仪再也不提下山之事,于谷中日夜感悟。每有所得,二人就在一起研讨,精进神速。数月之后,二人观物察事一如玉蝉儿,学会了如何使用直觉。又过数月,他们竟也赶上童子,能以心眼观物。
流光如梭,转眼又值深秋。朔风吹来阵阵寒意,催红漫山秋叶。秋叶一片片落下,鬼谷林中,部分树木已近光秃。
这日午后,玉蝉儿正在草堂中看书,一股冷风呼啸着吹开房门,袭入草堂。玉蝉儿陡然受凉,情不自禁地打个喷嚏,起身关住房门,拿木棍顶上,返回洞中闺房,打开衣箱,取出一套秋衣加在身上。
玉蝉儿复至草堂,正欲坐下,忽听天上传来大雁的“呱呱”叫声。
玉蝉儿猛然想起什么,心儿就如被人揪住似的,只几步跨到门口,打开房门,冲到外面的草坪上。
玉蝉儿放眼望去,但见万里晴空点缀朵朵白云,一行大雁正从头顶掠过,排成人字队形飞过鬼谷。姬雪的声音亦随着一声声的雁叫响在耳边:“雨儿,燕地遥远,阿姐这一去,此生怕是再难回来了。阿姐想念你时,就会把心里的话儿说予大雁,大雁最是守信,定会把阿姐的话儿一丝不差,全捎予你。雨儿,秋天到来时,只要你看到南飞的大雁,可要用心去听……”
玉蝉儿正在回想,雁阵已是掠过头顶,飞向南面山顶。玉蝉儿紧追几步,眼睁睁地看着雁阵没入山后,那串“呱呱”的叫声也渐响渐弱,再也听不到了。
山谷重归静寂。
玉蝉儿的泪水攸然而出,正自伤怀,又有两行雁阵由北飞来,呱呱叫着,掠过她的头顶。玉蝉儿精神一振,两眼直直地凝视它们,目送它们再次消失在南山之巅。
又候一时,看到再无雁阵,玉蝉儿轻叹一声,走回草堂,取出琴匣,拿出姬雪临别赠她的七弦琴,轻轻抚摸。
玉蝉儿手抚琴弦,泪下如雨,喃喃哽咽道:“阿姐,雨儿看到大雁了,它们告诉我,它们看到你了,它们看到你站在它们面前。可你望着它们,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说……阿姐,你心里有话,为何不对雨儿说呢?阿姐……雨儿想你啊!”
玉蝉儿悲泣有顷,缓缓起身,抱琴走到户外,在草坪上并膝坐下,面朝北国方向,轻轻弹奏起来。
一阵风儿吹过,一片秋叶飘零,落于琴上,复被风儿拂走。
琴声初时低沉,如呜如咽,而后如急风骤雨,再后如雁语声声,又如流水淙淙,声声呢喃,最后如浮云掠过,陷入一片死寂。
两百步开外的小溪旁,苏秦、张仪并肩呆坐于一块巨石上,各闭眼睛,全神贯注地倾听玉蝉儿的琴声。
鬼谷子与童子散步归来,看到二人,亦走过来。苏秦感觉有人,睁眼一看,见是先生,翻身欲拜,被鬼谷子伸手制住。张仪则完全沉浸于玉蝉儿的琴声里,两行泪水悄无声息地滴下,滑落在石头上。
鬼谷子跨上石头,并膝坐下。张仪猛然发觉,打个惊愣,忙拿衣袖抹去泪水,坐拢过来。
鬼谷子眼望张仪:“张仪,在听什么呢?”
张仪应道:“回先生的话,弟子在听师姐弹琴。”
“琴声如何?”
“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弟子听琴无数,唯有今日琴声令弟子心颤。”
“是的,”鬼谷子点头道,“老朽看到了。”转问苏秦,“苏秦,你也在听蝉儿弹琴么?”
苏秦应道:“是的,先生。”
“琴声如何?”
“如泣如诉。”
“哦?”鬼谷子抬头,“可曾听出她在泣什么?诉什么?”
苏秦摇头:“弟子听不真切。”
“嗯,”鬼谷子赞道,“你能听出,已经不错了!”
张仪心里一动,急切问道:“敢问先生,师姐在诉说什么?”
鬼谷子转向童子:“小子,你来说说,你的蝉儿姐在诉说什么。”
童子正在闭目倾听,听到鬼谷子发问,头也未扭:“回先生的话,蝉儿姐在跟大雁说话。”
“大雁?”张仪略怔一下,恍然有悟,不无叹服地点头道,“嗯,大师兄说得极是,刚才师姐看到大雁南飞,这才出来弹琴。”
鬼谷子没有睬他,继续问童子:“你的蝉儿姐在对大雁说些什么呢?”
童子又听一阵,摇头。
张仪急问:“先生能听出她在诉说什么吗?”
“是的,”鬼谷子缓缓说道,“她在诘问大雁为何不守信用,为何不把该捎之物捎来。”
“该捎之物?”张仪打个惊愣,“请问先生,大雁能捎何物?”
鬼谷子瞥他一眼:“你要关心这个,最好去问蝉儿。”
张仪知先生已经揣出他的心意,脸上一热,急急垂下头去。
“先生,”苏秦解围道,“如此细微之境,弟子能否听懂?”
鬼谷子应道:“只要用心,自然能够听懂。”
“如何用心?”
“将心比心,心心相印。”
“如何做到心心相印?”
“人心直通情、意。欲知他人之心,就要揣摩他人情意。听其琴,揣其情,摩其意,自通其心。”
苏秦喃喃重复:“揣其情,摩其意,自通其心。”
“正是,”鬼谷子重申一句,“此为揣、摩之术。捭阖之术五花八门,首推揣、摩。”
张仪已经听出先生是在借机传授,精神陡来,大睁两眼:“请问先生,何为揣情?”
鬼谷子缓缓说道:“揣情就是度量他人之心。诗曰,‘他人有心,于忖度之,’讲的就是揣情。若是揣人,则要察其言,观其色,闻其声,视其行,然后推知其心之所趋。若是揣天下,则要透视国情,观其货财之有无,人民之多少,地形之险易,军力之强弱,君臣之贤愚,天时之福祸,民心之向背,然后推知其国运是盛是衰,是兴是亡。”
鬼谷子由此及彼,推而揣摩天下。苏秦、张仪如闻天书,似痴似迷。沉思有顷,苏秦问道:“请问先生,如何揣情?”
“欲揣其情,首摩其意。摩为揣之术,揣、摩不可分离。”
张仪急问:“何为摩意?”
“所谓摩意,就是投其所好,诱其心情。譬如说,对方廉洁,若说以刚正,此人必喜,喜,必泄其情;对方贪婪,若结以财物,此人必喜,喜,必泄其情;对方好色,若诱以美色,此人必喜,喜,必泄其情。是以善摩之人,如临渊钓鱼,只要用饵得当,鱼必上钩。”
苏秦、张仪再入深思。
鬼谷子见二人已入状态,缓缓起身:“习口舌之学,不知揣情摩意,就如聋子瞎子,若想成功,难矣。”
苏秦、张仪起身拜道:“弟子谨记先生所言,细加体悟。”
望着鬼谷子与童子的背影渐去渐远,张仪回过头来,转对苏秦,一本正经地说道:“苏兄,你说先生这人,肚里有多少宝货,尽可悉数倒出就是,偏是星儿点儿,让你我整天价日里瞎琢磨。”
苏秦扑哧笑道:“贤弟,就你我这点肚量,先生若是全倒出来,能不撑死?”
“苏兄说的是!”张仪亦笑一声,“先生这……今日一点儿,明日一星儿,就是让你我慢慢悟呢。”略顿一下,“哎,我说苏兄,今儿这点揣和摩,可有感悟?”
“还没细想呢,谈何感悟?”
“在下想到一事,你我何不就此习练一下,或有所悟。”
苏秦笑道:“贤弟想到何事?”
“师姐。”张仪稍作迟疑,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方才先生说,师姐在诘问大雁为何不把该捎之物捎来,想必是师姐在思念什么人。苏兄你来揣摩一下,师姐她能思念何人?”
苏秦连连摆手:“若是揣摩别人,在下或可。揣摩师姐,在下断然不及贤弟。”
“苏兄不必谦逊。”张仪话中有话,“在此谷里,除先生之外,真正晓得师姐的,还不是你苏兄?譬如方才,师姐弹琴,在下听到的不过是琴,苏兄听到的却是心。仅此一点,在下已是服了。”
“贤弟过誉了。”苏秦笑道,“其实,师姐之心,贤弟早已揣出,不过是知作不知而已。”
“苏兄说笑了,”张仪亦笑一声,“在下若是知晓,何苦去问先生,授人笑柄?”
“贤弟听琴心颤,泪流满面,若不将心比心,心心相印,何至此境?”
张仪见苏秦说出此话,拱手笑道:“在下心事,真还瞒不过苏兄啊!”
这日夜间,张仪躺在榻上,辗转反侧,久久未能入眠。联想到《诗经》开篇里的“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句,似是突然体会到了古人的感受。两相比照,张仪觉得,古人吟出的就是现在的他。
张仪轻叹一声,披衣起床,“吱呀”一声推开房门。
是夜正值仲秋,一轮圆月明朗如镜,高悬天上。张仪走到外面的草坪上,仰面躺下,两眼眨也不眨地凝视着这轮明月,观望一团又一团的淡淡白云缓缓地移近它的身边,从它身上攸然掠过,渐去渐远。
望着,望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