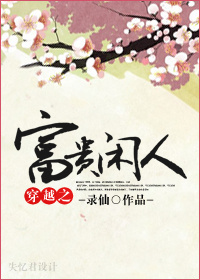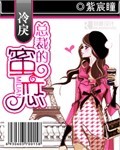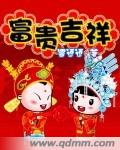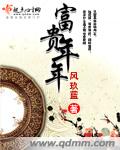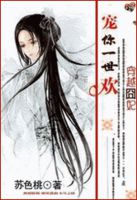一世富贵-第9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宋朝的税赋科捐,一个根本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从制度上对乡村上等户特别是形势户从严,对下等户从宽。制度上如此规定,哪怕制度执行不彻底,也不会让国家的税赋负担全压到最贫穷的人家身上,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
夏税从五月十五开始征收,七月三十是最后期限。现在已经六月,巩县的形势户钱粮已经催收完毕,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了,想让县里夏税难收,不好操作了。是以谭节级觉得让县里收不上来夏税,把知县逼走,现在已经晚了,多半行不通。
张押司冷笑:“只要钱粮还没有解到县里,就有办法可想。里正和乡书手,只要得我们一纸文字,库里的钱粮,要散回去还不容易!”
听到这里,宋押司猛然一惊:“二哥,你这意思,是让我们全都不做了?”
“不错!”张押司猛地一拍桌子,“一不做,二不休,知县相公让我们活不下去,那就干脆把事情搞大!把收上来的钱粮散回去,我们去太室山躲些日子,说落草为寇,那就落草为寇好了!只要逼走了知县相公,我们回来依然过自己的好日子!”
………………………………
第65章 要将功赎罪
政事堂里,徐平看着京西路关于巩县的奏章两眼发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长官,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起了,从景祐年间之后特别多。但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往往是官员完不成任务,或者被劾,或者调任,路监司为官员求情。巩县不同,吏人集体逃亡,王安石没有比毫完不成任务的担忧,而是主动上章,要求对逃亡吏人重惩。
放下奏章,徐平对一边的晏殊道:“巩县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说他们落草为寇,要发海捕文书。此种事情不少见,如此做的倒还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锋芒太露。吏人逃亡,长吏躲不过逼下太严的罪过。京西路虽然上奏是吏人贪渎,害怕事情败露而潜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动辄一两千贯的弊案,令簿难逃失察之过。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员太过,当从容商议。”
杜衍也道:“不错,出现此等事,必然是官与吏均有过错。巩县欲发海捕文书,说那些吏人为寇,只怕有些言过其实。可着京西路监司,从附近选谨慎强干的知通,去巩县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听县官一面之辞。”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纵然我们觉得此事别有委屈,也不可此时去查。官与吏,吏与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边,此天下大义。不然,官吏一有冲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养成不好习气,从此吏人有恃无恐,仗势以临官长,地方难治。”
吏是与民接触最密切的政权基层,朝廷大部分的制度和政策,都由他们执行。面对老百姓,他们代表的就是朝廷,往往耀武扬威。一旦再让他们对官员占了上风,那就成了上下通吃之势,再也难治。是以对吏人,朝廷可以站在百姓一边,可以站在官员一边,惟独不能站在小吏一边。朝廷用吏人,最主要的就是啖之以利。不管是用重禄,还是让他们在百姓身上占便宜,总之就是有好处才有人来做这差使。
不可否认,吏人中也有重情重义的人,也有深明大义的人,那是个人。从总体上吏是无义的,所以官不可以从吏人中选,吏除了钱,是没有政治前途的。吏要想做官,必须先辞去吏职,才能够受举荐,参加科举。要是不这样做,把持住基层的吏人,就把持住了社会的上升通道,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后果。历史上官吏不分,以吏为官的,有两个朝代,一个是秦朝,一个是元朝,都没有留下好的统治经验。
这个人群的定位如此,是政权为了稳定基层,同时又不被基层挟持,而有意做出的官吏之分。这个分别对大一统政权非常重要,封建制下则可有可无。
想了想,徐平道:“要不这样,夏税未完之前,一切依巩县上奏为准。如果县衙不能完成夏税,则论如律,此不必多言。税能完足,再从临州抽调得力人员,前去彻查。”
程琳道:“如此自然也可。只是现在逃亡的吏人该如何处置?巩县说他们上太室山落草为寇,此无异于反叛,要发海捕文书。秋后再派人去查,这些吏人罪名可就定了。”
徐平道:“既已逃亡,罪名自然就定了。不管事出何因,这些吏人都不能再用,不然以后谁能够治他们?官不能制,他们不就成了地方之主。为朝廷计,为百姓计,逃亡的吏人决不可于用。不只是巩县,其他地方一样如此办理。”
跟县官闹矛盾,逃亡之后再请回去,这些吏人以后就没人管得了。所以这次不管是不是他们的错,巩县都容不下他们,最少也要发配他州。所谓强吏猾吏,都是靠着在地方上错综复杂的根基。出现这种苗头就不行,必须要及时铲除。朝廷不能贪有这些能人,便于治理地方,就容忍他们,这样做是掘统治根基,稳固的政权不需要基层的能人。
几人又商议了一会,由章得象执笔拟定熟状。
巩县暂时依王安石上奏处理,只是不允许发海捕文书。既然说吏人已经落草为寇,那便着京西路巡检司,派得力将领前去围剿。由巩县尉带弓手协助,其他人不与。
原由知许州兼任的京西路安抚使司已经撤销,新设几个都巡检司,负责地方治安。前些日子刚刚平定了作乱几年的张海之乱,初显锋芒,刚好再到巩县去再立威。
敕令到巩县,颇有些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河南府是京府,比不得一般军州,上边管事的婆婆就有好几个。吏人逃亡之后,王安石知道河南府和西京御史台,对自己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满,想派人来查自己。转运使杜杞因张海初平,不欲治下生乱,也有些怪王安石生事。没想到敕令下来,竟然一切依自己所奏。
随着敕令而来的还有徐平一道手札,告诉王安石,吏乱官不能脱罪,只是不能现在治他的罪,而让吏人怀侥幸之心。让他尽快安抚地方,特别是夏税不能出任何乱子。再一个前些日子卖出去的官营产业,有如此大的情弊,王安石失察。接下来的日子,对所有的产业重新梳理一遍,不縻费朝廷之财,也不要让百姓吃亏。
徐平一再强调,官员在地方最重要的是让朝廷取信于民,政绩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考核。大规模发卖官营产业,众官都没有经验,出问题再所难免。最重要的,是在出问题之后进行补救。王安石如果能在重新彻查中,弥补先前的缺失,才可将功赎罪。若是为天下做个榜样出来,那就是大功一件。
原先王安石对工商业改革不上心,为政讲究崇本抑末,农业是本,工商是末。码头附近一处邸店就能出现两千多贯的弊案,让他吃了一惊。两千多贯,顶得上多少良田,让他重新考虑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对于此次的工商改革,有了新的认识。
王安石自己知道,此次乱子,自己被问罪是逃不掉的。吏人舞弊,自己失察在先,发现弊端之后,手段粗暴把矛盾激化在后。不管哪一条,都可以进行惩处。不过王安石是个拗人,越是这样他越不低头。别人觉得把吏人逼跑了,巩县必然收不上来夏税,王安石偏偏就不信邪。都认为此次工商改革搞砸了,王安石不认,一定要做得比别的地方好。
这是王安石的自负,他天资过人,有资格有这种自负。
………………………………
第66章 以民为师
小雨淅淅沥沥,天地间茫茫一片,宛如成了一个水世界。
还是那一间小店,王安石进了门,随手把油伞放在门后,到一副座头坐下。
小厮急急地跑过来,行礼道:“客官,要用些什酒肉?”
“若有煮好的羊肉,切一盘来,再来几样时鲜菜蔬。此时大酒,筛一壶来。”小厮应一声,转身就走,被王安石叫住。“这里的主人家,还烦请来,我问几句话。”
看旁边站的伴当,小厮就知道这客人非富即贵,答应一声,向后边去了。
不大一会,孙二郎从后面出来,见到王安石急忙行礼:“小民见过知县相公?”
“不须多礼。”王安石指了指身边的座头,“且坐下来说话。”
孙二郎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当初举家逃亡,便是遇到了徐平,现如今的昭文相公,改变了自己一家的命运。这些年来,上至宰相,下到知州知县,更不要说小官小吏,孙二郎实在见得多了。当下也产推辞,在座头上虚坐了。
让了两杯酒,王安石道:“我听人说,几年前你家里颇穷,曾经举家逃亡。现在却是县里数一数二的财主,由穷到富,有许多故事。可否说来佐酒?”
孙二郎道:“不瞒相公,小的命蹇。前几年在洛阳城里曾遇到一位神相,说小的命里无横财。这一生若想吃喝不愁,只要苦做。”
王安石笑道:“你命里无横财,现如今却是个大财主,才让人佩服。若是那等由横财暴富的人家,故事听来何用?你吃苦实做,由此发家,才可劝民。”
巩县是这一带的商业中心,一头担着河南府,一头担着郑州,非是其他小县可比。这里临洛河,当官道,水陆交通便给,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孙二郎的家离此不远,有意把这里作为自己商业的基地。洛阳那种大城,还不是现在的孙二朗能去闯的。
有意要在巩县发展,面对王安石这位父母官,孙二郎也不矫情,直言说道:“不瞒相公,小的幼年时,家里实在过不下去,父母带着欲要逃到开封府去。因是公人阻拦,得一位贵人相助,得以重返家园,收拾产业,终于有了今日。”
王安石问道:“不知是哪一位贵人助你。”
“便是如今的昭文相公。当日昭文相公正查探引洛入汴的河道,恰巧遇上公人抓小的一家,便为小民作主。后来相公挖通河道,在周围各县劝民立社,小的便是那时与同乡人建了个买卖社。如此苦做了几年,乡人都得了便利,小的也积攒下了些钱财。”
孙二郎发家的过程没有大风大浪,也没有过天降横财,就是靠着持之以恒,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家财。从最早的买卖社,到后来几家信得过他的人家立社,向洛阳城卖当地的土产,从洛阳贩货物回乡卖。他的生意利润都不高,但一直稳定,慢慢走到了今天。
王安石要听的就是这个慢慢发家的过程,商业怎么互通有无,怎么联络城乡。孙二郎生意做大的过程,一直都跟三司铺子有关。他收的土产是卖给三司铺子,货物也多是从三司铺子贩来。从开始的偶有赊欠,到后面的现钱现货,规模越做越大。等到接唐大姐铺子碎布头衣服生意的时候,已经有资本积累了,发现市场很快就做大。
跟洛阳城里的那些商家不同,孙二郎发家的过程,基本跟银行无关。他们的余财存入银行,是贪图有利息,而且安全,但却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钱。
小生意风险大,生意人怕背上债务,一有意外难以翻身。银行也嫌贷钱给他们的风险太大,不愿意做他们的生意。银行的放贷业务,还是以公司为主。
王安石留意的,是孙二郎这些年到底做了哪些生意。买卖社的时候,是以从城市向乡间贩运生活物资为主。后来做得稍大,开始从城里向乡间贩运农具。
说起贩农具的时候,孙二郎来了兴致,对王安石道:“不瞒官人,那几年,小的靠着向乡里卖各种农具,着实是赚了不少钱。最开始农具贩回来,是卖给几个大户人家,他们有本钱,家里的地也多,用得着这些。但不过一二年,这些大户人家的生意便就不好做下去了。一是农具结实耐用,爱惜的人家,一副犁铧用一辈子也不稀奇。再一个大户人家知道了路子,官府又让三司铺子方便乡下人买,我们的就卖不出去了。后来无法,小的想起当初昭文相公在周围县里立各种社,其中就有牛社之类。便就又托人到京西路南面的几州贩牛,与我们的农具一起,帮着乡里人立社。如此,又红火了几年。那几年,着实是靠着各种农具赚了不少钱。乡里人有了农具,地也种得好了,产粮多了,着实两得其利。”
王安石对此事甚感兴趣,问道:“既然做得好,后来为何不做了?”
“做的人多了,官府又劝立社,没大利息,便只好改做别的了。”
当年做农具生意,后来兼且贩牛,孙二郎那几年,不但是自己赚了钱,还带动了周围不少地方的农业发展。因为这事,他在本乡的名声极好,有乡间有德行的人之一。后来各种生意做得顺利,与此不无关系,人人都信他孙二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