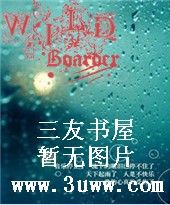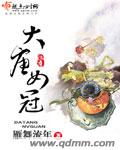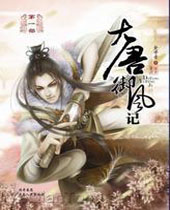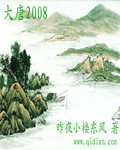大唐-第15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家天下的传承,自然不受它姓人喜欢,外姓人永远不得真正正法,不得真正神法,因此,东晋后期又产生了上清派和灵宝派等派,当时大圣大贤,如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寇谦之等人将重新将经典、科仪、神话整理。而所谓的三清,其实就是上清派和灵宝派的祖神,相互妥协的情况下,确定了三清,成为了道教的至高神,以后传播扩大,影响扩大,慢慢变成了正宗,这正是在唐时才开始正式形成的事情。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硬是要组织起一个统一地道教,不但是不可能的事情,更是不应该的事情。
与其建道观,乱封神,不如先统一土地信仰,各派先入土地神殿,以获得修行之资,慢慢再形成体系。
正本清源,以道为宗,如何处置各派各宗不同祖(师)神地关系,如何编写宗教,如何处置显派和隐派的区别,这不是一时一日地事情。
因此李播才如此说。
“至于道宗,陛下有意在天下已定后,召集天下道贤,共同商定道敕。”
所谓道敕。并不是统一道教,只是确定道之宪法,也就是确定创世论、无上道论。天地人体系,这统一口径。作为基石。
而各教各宗,只要不违背这三点,都可各有祖(师)神,各有道统,各有正法。万法归道,万流归渊,百家齐放,如此足矣。
既然李播如此说,大局已定,正法就行。
“圣上这次离洛阳去成都,更有深意,圣上居洛阳,数十万兵。不但李阀难以安眠,就是窦建德、刘武周也感到芒刺在背,谁也不敢动弹。但是如此,只怕三家结盟。共同对付本朝。圣上这去洛阳,专于对付李阀。全局就活,而窦建德必会北上解决罗家,刘武周,趁此机会,不但会巩固统治,更会趁关而入,攻打李阀,而李阀受此压力,必会引突厥而围攻薛仁杲。”
“圣上曾问话,如我是李渊,又会如何,我那时回答,此时,唯有引突厥,不顾一切解决薛仁杲,因此李阀虽受三重牵制,但是讨伐薛仁杲势在必行,因此必圣上亲去,才可让此战拖地更长一些。”
“而三军要扩编,如今七十万还不足,要对付日后突厥,一举平天下,必百万才可,非如前朝隋炀帝之大举征讨,而是预备,要知道,无论本朝攻向何方,再无喘息之机,攻下地点,必须有厢兵驻扎,来不及消化整编,圣上判断,现在局面牵一发而动雷霆,可能连场战役,因此我方,必须作出准备。”
“圣上说,十分可取天下,二十分时才出手,因此我方,无论兵员,粮草,军资,都要预备,训练完毕,屯兵以侯,各粮道,运输道,也要提前准备。兵部,如何?”
“首辅,兵部计算在册,已有镇军三十五万,训练完毕之厢军四十万,新征三十万兵,还要半年训练,才可安守各地。”石之轩报告的说着:“军械,现还有三十万军地军衣和武器,还没有到位。”“工部如何说?”
“纸甲,半年内必到位,现有一百二十万套,已可用事,而标制武器,由于铁器不足,难以到位。”鲁妙子说着。
“这倒无事,圣上已有旨意,不日进行禁法刀献令,民间有刀剑者,虽不禁,但是这时战时,必须全数交出,如有违抗,必受其法,因此足可弥补其铁器,等日后讨伐各地,也有铁器而得,当不要紧。”
魏征,参政平章事,刑部尚书,嘴角现出一丝冷酷的笑容,说着。
“具体细节,还要仔细记录分析,一一计划,这次事关本朝大业,不可大意。”
“我等明白。”
“马场呢?”
“一是收购民间马匹,但是战马很少,国内有二千匹已经是大善,其它的马匹,可充军运,二是各地马场,虽已建立,但是时日才浅,如今扣除了留种用马,就算加上买卖运输陇西军马,半年后,可用不过三万。”
如果不是有着飞马牧场,再加上一直重视牧场,宁可短时间占地放牧,那整个南方,别说三万匹了,说不定连五千匹也没有。
“三万足了,本朝目前无法深入突厥草原,无需一人三马,因此可训练二万五千铁骑,这是日后对付突厥入侵兵马所用,万万不可大意,在这时,可加粗粮喂食,以壮其力。”
这也是因为新得了兴洛等仓,这是隋朝大半地积粮所在,所以才可以如此用之,不但养百万军足够了,甚至可用粮食喂养马匹,以壮实。
要知道,真实历史上,兴洛仓等仓库,日后唐朝用了二十年,也没有用光,可见其粮食之多。
“水师呢?”
“水师已有六万军,船上千,无需扩军,当训练之,一旦有令,可沿海其上,攻入河北,配合陆路大军,一举消灭窦建德。”
“如此,诸位用事,积蓄雷霆之势,一旦蓄满,就可扫平天下,千秋基业,就在这时。”李播断然说着。
♂第二卷 一刀转战三千里♀
―第一百十九章 … 无衣妃暄―
月光如水,幽林小谷
在群山环汇形成的宁静幽谷内,溪水于林木中蜿蜒穿流,溪旁婆婆树木间隐见几间小石屋,若他推断不错,溪水该绕过屋前,流至谷口形成清澈的池潭,再流往谷外去。
谷内枫树参天,密集成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山崖峻峭,石秀泉清,能避世隐居于此,人生尚有何求?
池中大石从水底冒起,或如磨盆,或似方桌,清泉石上过,小鱼结伴游,充满自由写意,不染尘俗的意味。
一道箫音,在风中缓缓起伏,空灵通透的清音,似是娓娓描述某一心灵深处无尽的美丽空间,无悲无喜,偏又能触动听者的感情。
杨宣凝默然而听,整个人的精气神平静如海,又与万化而合。
只有站在人道人皇的颠峰,才能领略除人道之外,天地的无限广阔与奥妙所在。
坐拥亿万众生,天下命运翻掌之间,美人如玉,尽取尽享,权力无边,荣耀无限,真正是会当领绝顶,一览众生小。
今日,那属人的,我都尽有。
自身圆满而足,再站在这个高度,睁开眼睛,望向世界,刹那之间,天地玄黄,人道化生,尽在眸中,帝道奥妙,徐徐展开,这也是天人合
就一瞬间,他明白,自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宗师之前,自己受制于肉体和力量,不能超越,宗师之后,人力已尽。破除限制,自己潜在心中花朵徐徐开放,那是连石之轩也难以理解的力量。那是无限永恒的花园。
流水淙淙,沿溪而行。绕过清池,踏着满枫叶的碎石小径,心神安宁沉静,每跨前一步,似乎都更染上这里地风情。
林路弯弯曲曲。突地豁然开出,一个无比优美的身形映入眼帘。
箫音突地而停。
就在屋前,溪水旁一方盘石上,一个女子双足浸在水内,取下长箫。
“师妃暄,你来迟了。”杨宣凝毫不惊疑的说着。
这个女子,缓缓抬起俏脸,朝他瞧来。
杨宣凝心中顿时惊叹,俏脸所转。沐浴在温柔地月色里。
见惯美人,亦不由狂涌起惊艳的感觉。
虽在书上,看见洛阳小桥地描写。但是此时,才真正感觉到洛神现身水畔的意境。
长发被玉簪简单束住。只有一小绰青丝轻掠风中。一袭衣裙,不加任何点缀。纤细可折的腰身上,束着简单的腰带,纤细美妙的曲线浑然一体,风吹过,微微而露。
但是,她地眸中,流淌着对生命的热恋,和对永恒的追求。
周围,一种神秘不可测的安宁,使一切都如此纯粹,就好比来到了永恒的净土。
杨宣凝至此方体会到师妃暄,或者说,慈航静斋的惊人的造诣和研究。
极于美,极于情,极于禅。
女体极于美,感情极于真,意境至于寂。
三位一体,如此,才能接近完美。
就在杨宣凝心弦震动时,师妃暄以她不含一丝杂质的甜美声线柔声道:“妃暄实在不愿于这种情况下和陛下相见,只是时世奈何?”
此时,只有流水流过她的双足,沿上而看,似乎可以看见裙衣下掩映地大腿,小腹与腰部惹人遐思。
杨宣凝却淡然的说着:“朕岂是喜操干戈的人,只因天下一统地契机已现,万民苦难将过,故才诚惶诚恐,不敢粗心大意,怕有负群臣万民,与上天之命。”
又笑的说:“听闻妃暄化名秦川,不知现在八百里秦川,又有何用?”
这句话,本是她说地,但是现在,完全可以回给她,这句反问,更是直破人心,直接说明了,你当年选皇帝时,化名秦川,就已经有所定数,这明显是属意得关中地李阀,其心如此,还谈得上其它吗?
师妃暄默然,美眸异采涟涟,却还是以平静的语调淡淡道:“陛下现已登基,不知为君之道如何?”
杨宣凝同样淡然说着:“为君之道,天地人。”
“何为天地人?”
“天者,天命,应运,时势,地者,地理,城池,龙脉,人者,得人心者得天下。”
“何以得人
“如得天地,得人心者,下者小恩而法道,中者小恩而安道,上者大恩而权道。至于选贤任能,已在其次。”
“何为法道,安道,权道?”
“人心如铁,官法如铁,小恩大法,治民之要。”
“世所安宁,在于中者,小恩而安,治士之要。”
“上者寡恩,在于自有,唯治于权,治上之要。”
也就是说,小民施于小恩足够了,要以法律罗网处置,这是受法地主要阶级,士子阶级,小恩也足够了,但是要给他一个安定的产业基础和言论基础,而上位者,本来自有产业,自有根基,皇帝施恩,根本就是锦上添花,治理他们,唯权道。
师妃暄沉声道:“大乱之后,如何实现大治?”
杨宣凝微微一笑:“杨广之基,已可大治,且乱后易教,唯在许之自化就可,朕取道德清静二字,以得修养,又取大禹治水,也取疏导二字,以引国运。”
师妃暄听得默然不语,又沉声说着:“昔日文帝杨坚登基,不也是推行德政,谁料两世而亡,天意难测,陛下对此又有何看法?”
杨宣凝默想片刻,说着:“因为隋帝得国不正。没有能力大举杀戮。”
师妃暄平静的说着:“还请陛下仔细说来。”
“隋帝如嫁接,苗虽新苗,骨干树根仍是老旧。如此,皇帝虽新。国家还旧,无法拥有新血,旧病还在,所以二世而亡,古往今来成大事者。能延国运者,无不是新苗新枝,凡挡着帝座的障碍物,一律均被清除,妃暄你也不例外。”杨宣凝淡然说着。
师妃暄现出一丝充满苦涩意味的神情,美目凝视:“陛下,李渊从强势转为弱势,塞外联军将乘机入侵,纵使不能荡平中土。造成的损害会是严刻深远地,百姓的苦难更不知何年何日结束?中土或永不能回复元气,这又何解?”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朕本天下独夫。妃暄这个问题问错人了。朕只为自己,只为杨唐。其它的事情,与我何关,唯民如大海,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所以朕立下法度,必安抚百姓,施于小仁大法,朕不会让腐朽地木头,充当朕的座船,更不允许随时可以抽开地底板存在。”
“天下是由北统南,天下可望有一段长治久安的兴盛繁荣。若是由南统北,不但外族入侵,天下必四分五裂,这话实有道理,但是此时,朕已掌握天下大半,孟子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此也是朕意,时至今日,妃暄如为天下苍生福祉,何不牺牲自己?”
师妃暄迎上他的目光,平静的说:“陛下有何建言?”
“论私,你就脱下衣服,赤裸与我说话,以示再无女性廉耻。”
“论公,为天下百姓,你就联合三大圣僧,刺杀李阀要人,朕也可一举统一关中,如此,就算突厥进军,也奈何不了朕,就如你所说,为了天下安定,有什么恩怨是抛不开的?有什么私人牺牲不可许出?”杨宣凝微笑地说着:“当然,刺杀不了,只要证明三大圣僧已死,也证明了佛教对朕诚意,莫非到了现在,妃暄还认为,不付出牺牲,就可取信于朕?”
“朕本独夫,向来希望有人为天下人牺牲,这牺牲,请自从妃喧和三大圣僧开始,妃暄向来抱着不计成败得失争取天下和平契机,此时,正是妃喧显示诚意之时,你区区一女身,怎能和天下黎民相比?不是吗?”
就在此刻,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际,说着:“想不到,今日一见,再不复当年,陛下不觉得所说,太过无耻了吗?”
杨宣凝负手而立,也不回头,俯首凝望水流,远一点是水潭,潭底布满彩石,在阳光下荡漾的水波里斑烂绚丽,微笑的说着:“大公大私,谁能够掌控大局,就可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