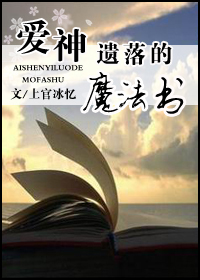神遗-第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欢抬头看了一眼天边的晚霞,零零碎碎的洒了半边天,灰黄的土壤和绚丽的彩霞相印成趣,越发让凄凉更凄凉,悲怆更悲怆。
半晌他低声说:“这些妖兵剩下的也不多了吧。”
齐远嘶哑地笑了两声:“我们手边的火药要是再多个两倍,就能把他们炸上天。”
时欢说:“要是用毒呢?”
齐远抬手往外指了指:“这……得什么程度的毒才能把他们送走?开玩笑呢。”
时欢冷静地帮他包扎,说:“把毒混在火药里,肯定能炸个不同凡响。”
齐远摆摆手,笑了笑:“说什么傻话,现在哪还有毒。”他叹了一口长气,神色里的狂乱逐渐染上了哀意,“想想可能保不住你了,心里就不舒服,你们跟着我,真是倒大霉了。”
时欢把东西收了,说:“齐师兄哪里的话,人各有命,死的值当就行。”
齐远撑着墙面站起身:“能好好活着才最值当,你年纪小,不应该老想着死得其所,你应该想着怎么才能活下去。”
时欢也不动声色地笑:“要是能活着谁想死呢——齐师兄,我去给你拿晚饭。”
齐远拉了他一下:“哪还有吃的?别给我拿了,我听见底下哪家小孩哭的撕心裂肺的,他们把铁锅都敲了给我们打弓打箭,我们也亏欠人家不少。”
时欢说:“已经让人去派了一次粥,你不吃怎么打,别操心了。”
齐远叹了口气,没再应声。
第84章 雾霭
秦府里的两人面前是蚂蝗一般的老少妇孺,要是下手吧,实在过不去自己良心那一关,不下手吧,那些人可不管他对你下的是不是死手。
一把两把菜刀看着不吓人,但各种农用的锄头、砍柴刀都握在这些人手里,就算不怎么发怵,也够让这两位名门正派的传人好一番头疼。
萧盛看了看萧繁:“师兄,这到底是人是鬼?”
萧繁手上的长剑出鞘,闪过一簇寒光,说:“试试吧。”
他说完身形速动,抬指晃了晃剑气,身侧的一个老人被削掉了半截白发,萧繁的剑气使的小心,看着来势汹汹,其实连对方的皮都没蹭破。
他耍了个假把式又迅速撤回到了萧盛边上,神色僵凝地说道:“不好办,是人。”
萧盛的眸光也冷了下来,一边左躲右闪,一边说:“这也是被控制了吗?”
萧繁拉着他转身绕道屋檐后,说:“开始追杀我们的那个,脖子上有道暗红色的什么疤痕,我看着奇怪,你知不知道?”
萧盛想了想,抬手扔出半块碎瓦,把冲他们飞过来的菜刀击落,说:“暗红色的伤疤?刚刚那些人身上有吗?”
萧繁探头看了一眼:“没注意,我再去看一眼。”
萧盛一把拉住他:“师兄等会儿,等他们分散一点再出去,现在打没法打的,只有吃亏的份。”
萧繁拍了他一下:“没事,他们一时半会不会分开的,不能空等着。”
他说着又轻飘飘地落在了那群人的后方,秉承着“挑软柿子捏”的原则,抬手用剑尖挑了一个小孩的后领,那小孩瞬时被扯的往后倒了倒,转头望过来,眼睛灰败空洞,就像被掏走了灵魂,只剩下一个躯壳。
萧繁迅速用剑鞘拨了一下那孩子的肩膀,果然看见同样的地方也有一道红色疤痕。
就这一小会儿的功夫,人群已经注意到了他,开始缓缓转身,像是被下了咒的走尸。
萧繁故意在周围绕来绕去,等把他们溜的差不多了才又闪回了萧盛身边,低声说:“可能就是那个疤痕有古怪,刚刚查看了一下,那小孩也有。”
萧盛手指在配剑上蹭了蹭,说:“让我想想,有什么样的咒法能把人支配道这个份上。”
萧繁探头看了一眼:“他们发现我们了,先换个地方。”说着两人纵身跃上了临近的屋顶上——底下的庭院里已经没有下脚的地方了,就像发了一场水,还是血水,还不知道这是谁的血,说不准沾上就要烂肉。
他们刚刚站稳脚,萧盛突然拉了萧繁一下,说:“师兄,你觉不觉得,这个不太像我们关内的东西?”
萧繁皱了皱眉:“妖兵?”
萧盛摇头:“南疆。”
萧繁露出一份惊诧,又说:“也不是没可能,但你从哪看出来的?”
萧盛说:“夏天的时候长安不是闹了走尸嘛,当时闹的沸沸扬扬,不就是因为山君亲自来要人了,想来如果是那种手法,怎么都应该从他手底下出来的,一是不大可能,二是那都是死人,而这操控活人的法子我总不由自主地想到南疆的那些蛊术了。”
萧繁往身后看了一眼,说:“说来听听。”
萧繁想了想:“我前些日子看了一本写南疆的异闻录,里面大多是常见的养蛊故事,但也有驱使活人的,迷惑心智的都属于比较高阶的招数了。”
萧繁嗯了一声:“所以呢?”
萧盛挠挠头:“不是特别能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南疆是有关系的。”
萧繁点点头,又说:“如果那个秦晨就是赢勾手底下四魔之一,他又怎么和南疆有关系了?南疆和谁都势不两立的,会出手帮他们吗?”
萧盛说:“这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是偷学来的,或者逼迫来的。”
萧繁点头:“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我们眼下怎么对付那些人才是关键,他就把人放出来,难不成杀完才行?”
萧盛四下看了看:“不知道啊,他到底想干嘛啊,追又迟缓的跟锈住了似的,我们就是不还手而已,想耗死我们不成?”
萧繁抬眼看他:“说不准。”
萧盛的表情疑惑起来:“啊?耗死是什么死法?”
萧繁若有所思:“杀也不能杀的,不然敲晕了试试?”
萧盛眼睛里乍然放光:“那现在就试试?”
萧繁笑了一声:“听着不怎么靠谱。”
萧盛还没来得及接话,一把斧头破风劈来,萧繁骤然警觉起来,拉着萧盛躲避后抬眼望过去,扔斧头的那人看着年过花甲,站着却不摇不晃,刚刚扔的那一下也绝不是蛮力,是有内功底子的。
萧繁低声说:“敲晕看来不可行了,这里面混入了练家子。”
*
江离舟查封了万宁楼,那鸨娘除了刚开始不满被他呛了回去,也没再吵吵嚷嚷的要说法了。
他回去后心里挂念着林清和,正想着要不要传个信问问,一只匣鸽就悠悠地落在了他的窗前,打开看来就几句简短的安抚。
江离舟看见他说要走一趟南疆就莫名不安,南疆的地界在他还是黎崇的时候就没踏足过,因为南疆向来不与任何人交好,他们认为自己家的秘术举世无双,旁人来了都是带着不轨的目的。
至于时欢,也是机缘巧合,十几年前被颜钟从南疆与关内的交界地捡回来的,不知道他的亲人是谁,身上只有一个紫檀木的手串,南疆人浑身是毒,颜钟就将那手串保管了起来,时欢那几年也是被颜钟亲自带在身边,明烛山没什么避讳,也没有那么多心眼,除了时欢会注意着自己身上的特殊之处旁人都没有当过一回事。
早些年颜钟并不是不管事,只是分什么事,徒弟能解决的他绝不会插手,实在解决不了的才会帮扶一把,但他对每一个弟子都绝无敷衍之意,只是闲散惯了,实在不想搅和进一些琐事之中。
江离舟想起来许久没有与湟中通过信,也不知道他们近况怎样,也不知今天是想什么来什么的气数旺还是怎的,他这念头还没完全成型,另一只匣鸽又落下了。
江离舟一遍纳罕一边打开了信,同样很简短,却让他手足都僵**。
时欢写信时反反复复改了数次,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噩耗说的更委婉些,后来想想,师兄不是外人,没有必要做些无用的表面功夫,隐晦的词句不过徒增那些纸张之外的猜想和悲痛罢了。
他写的简单,江离舟最后看到的也很简单:“师兄亲启,二月初三湟中大火,烧毁了大半库房,那日我在城门,不知事情原委,猜测是阿连为撤走火药留在了库房里,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逃出,阿连以身为盾让火药爆炸的伤害降到了最低,为我们保住了不少东西。
阿连比我们想象的要勇敢的多,湟中或将失守,还请师兄节哀,大战在即,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保全大局,如若此处便是终点,我也不惧不退,还请师兄不要自责,不要忧心,在城破之前我都不会放弃求生的机会。”
江离舟一字一句地读完信,不敢相信似的又回头读了一遍,后知后觉的有点愣神,他的心神都是恍惚的,好像和他的师弟们分开不过月余,怎么就翻天覆地了,他们好像突然长大了,字字句句透漏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意味。
时连在他心里一直都是那种,翻过石墙就为了摘一串还没熟透的葡萄,想方设法逃避日常的功课,耍赖撒娇让师兄弟们帮他写那些罚抄,怎么突然变成这么一个无惧无畏的大人了。
江离舟觉得脚底都有些漂浮,他想,应该不是长大了,是他们本就足够勇敢,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平静里看不大出来。
明烛山长大的孩子也许不会个个都名扬四海,如果是太平盛世,可能一辈子也只是个二流修士,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更别提什么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但他们永远明是非,辩善恶,知何为可为、何为不可为,遵自然道行正义事,他们都有无数小毛病,却不会犯大错,也许会有几个例外的,跌进了歪门邪道爬不出来,但很少是因为野心和图谋。
修了自然道,行了仁义事。
江离舟心口堵的厉害,神思恍惚的不行,心里反反复复的还是觉得怎么可能,上次去了一趟湟中阿连还高高兴兴地扑过来迎他,现在在心里千回百转的全酿成了苦酒,涩的五脏六腑都疼。
他学的那些尽人事听天命现在全变成了狗屁,根本不能起到任何安慰的作用,时欢的遣词造句出奇的冷静,也够冷血,在生死面前什么婉转的语句都是伤口边上镀金的花纹,除了好看一无是处,毕竟世上大多的伤痛都是靠自己慢慢吞咽的,旁人除了摇旗呐喊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江离舟把纸张捏的有些发皱,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转述给许陵他们听,干脆撂了信纸,叫他们自己来看。
窗外白梅在日光下轻摆,一阵狂风吹散了徘徊不去的雾霭,而那些雾气却又在下一瞬重新聚集,端了个不死不休的架势。
第85章 南疆
层层的黑云压在湟中城的头顶上,似乎在酝酿一场风暴。
城楼边上的青色大旗在风中裹的猎猎作响,所有人都浸没在血腥味的凝重中默不作声。
齐远这时候不在城楼,在萧夏的屋里,萧夏的伤太重,生生地吊了几天的命,半刻钟前突然睁了眼,估计是回光返照,人要不好了。
他们先前并无交集,而此次同在湟中月余,竟也真是过命的交情了,只是萧夏没能扛过去,他硬吃了妖兵的一记响雷,那是浓缩式的火药,胳膊当场炸飞了,五脏六腑都被震伤了,能撑这么几天都已经是奇迹。
齐远右臂还吊着,坐在他床边和他说话:“我知道,修行的大多没有什么身后事要照料,也不知道我们明天还能不能站在这儿,要是扛过去了,我一定带你回琪琳,要是扛不过去,我们很快能再见,这些天你辛苦了,不必挂念,我们自然尽力。”
萧夏眼神灰暗,只听他说,并没有想表达的征兆,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好挂念的,剑宗的师兄弟们可能到他死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寡言的同门,反正人死就是一捧土,萧夏也不会在意到底谁记得自己谁又不记得,横竖是人都要走一遭黄泉,早晚的事,也没什么好不平的。
反正其他的问题都是活人要考虑的。
齐远从他房里出来,神色晦暗,时欢肩上的伤口似乎还没好转,仍然包的严实,他迎上去问:“萧师兄……”
齐远笑了笑:“别往那破庙里送了,就让他待在这儿吧。”
时欢点头,也没再多嘴,至于尸体腐烂的问题,他们能不能撑到尸身腐烂才是问题。
夜间月色昏沉,冷风折断了残枝,夜枭藏在黑暗里发出嘶哑的鸣叫,妖兵突然开始撞击城门,一时之间仿佛天轰地摇,夜间巡视的弟子敲响了铜钟,钟声撕破寒夜,阵阵逼催。
齐远折回城楼,见时欢把什么东西塞进了火药筒里,又和值守的弟子交谈了几句,齐远走上前来:“你放了什么东西进去?”
不知是不是月色昏暗的缘故,时欢的脸色格外难看,他说:“我在附近找到了几味药草,回去翻到我带来的药粉,我稍微把它们处理了一下,就是我上次说的毒了,可以试试,这些东西我暂时都不缺。”
齐远看见他手上也缠了纱布:“手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