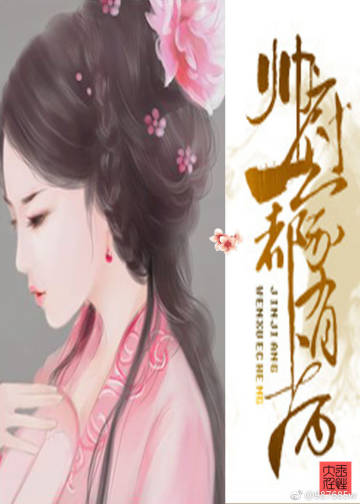我全家都是穿来的-第2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宋茯苓:这就对了。想不开就出去溜达溜达,玩玩。
心宽一寸,路宽一丈。
再说现在是着急挣钱的时候吗?事情要有轻重缓急。
眼下最重要的应该是,甭管一年、两年,还是乱起来三年五载,在外面人恨不得要饭时,我们关上门还有吃有喝就行了。
宋茯苓甚至觉得,点心店关门挺好,倒松了口气。
并不是担心接着开店能不能挣到钱。
是担心往后经济越收越紧,老百姓过的穷苦起来,人没吃没喝,逃荒路上没少见人性的恶,奶奶们天天往返路上总是不安全的。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要是她出面劝,别开了,咱主动关门,奶奶们指定会觉得她有病。
即便给分析会危险也没用。
这些老太太们有时对挣钱的执着超过了性命,不真出大事,她们不见兔子不撒鹰。可话说回来,要是真等到出些什么危险事时,后悔也晚了。
大烤炉房里。
马老太糕糕兴兴店所有员工聚齐。
送糕师傅们站一排,做点心的老师傅们站一排,后进烤炉房的师傅们站一排。
宋茯苓和马老太一人扯着一头,一脸郑重用最大号的草帘子,盖上曾让她们发家的“家当”。
擦拭锃亮的打蛋器;靠墙立着的一块块牌匾;一摞摞空蒸笼;一叠叠油纸;一双双白手套;一条条粉头巾……
别人家都是开业剪彩,奠基。
她们是关业,来了一个完美的收官仪式。
全体成员在帘子盖上那一刻,脸上纷纷露出沉痛的表情。
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就已经足够。
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追忆里留下过并肩作战的快乐。
外面,宋阿爷带着几个老头贴在门前听里面的动静。
马老太将门打开时,几个老头差些摔屋里。
“咳,”马老太掖了掖耳边碎发:“那什么,老爷子,给俺们再编进去吧,挣工分,跟你们干了。”
豁出脸来,也得将下岗员工们的工分制讲明白喽。
宋阿爷摸腰间烟袋,心想:
谢谢你哈,还整句跟俺们干了。
你们不跟俺们干,还想和谁干?
至于挣工分,眼下真的有必要具体谈吗?我就是现在说你挣十工分,也没钱给。公家穷的叮当乱响。
马老太冲老爷子背影:“您老别跑啊,那我们还干以前的活?”
老爷子无所谓的摆摆手,随便干。
八个老太太来到公共大食堂。
郭婆子冲她大儿媳一伸手:“交钥匙。”
她大儿媳立即将管粮的活上交。
田婆子瞪眼瞅烧火的小媳妇,那位小媳妇主动让开。
宋二婆子瞪她儿媳妇:“勺子给我。”
只眨眼间,给大伙做饭的轻巧活记就被八位老太太抢了,被抢的人还啥也不敢说。
任族长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的。
美其名曰,找宋阿爷唠嗑。
宋阿爷一脸懵:你个老秀才,确定和我有共同话题吗?
聊着聊着,宋阿爷就品出不对劲,怎么打听的全是逃荒路上的事,还问的很细致。
到了晚上丧钟响完后,才破迷。
“大伙别走,讲几句话。”任族长今日是有政治任务的。
上头规定,作为里正,必须要做好思想动员工作。
《关于靖难时期我村村民自力更生支持平叛的几点意见》
任族长说:“不平叛,那些人打过来,咱们能有好?那就得逃荒。逃荒有多惨,你看看他们就晓得了。”指向宋福生他们。
任家村村民们齐刷刷地望向宋福生他们。
又齐刷刷露出呆头鹅一样的表情,在心里嘀咕:
这也不惨哪。那如果要是都能逃成他们那样,逃逃试试也中。
第四百四十四章 可要了血命了(二更)
你们那都是什么表情。
任族长急了:“他们惨。”
任公信两手插在袖子里,心里一哼:我不信。
任族长:“远了先不提,就提他们才来到村里时,还要靠救济粮糊口。救济粮啊,乡亲们。那都是潮了捂了的低价米粮,不定是几年前存的粮,他们就靠吃那个维持。”
任公信忽然抬头,怒视前方的任族长:
任尤金你个糟老头子,哪壶不开你提哪壶。
不是他们惨,是我,我惨。
不是他们在吃潮了捂了的低价米粮,是我在吃。
他们吃的都是我给的精米细面。
我最惨的是,用精米细面换糙粮还断了顿,上面不给发救济粮了。
想起这茬就想哭,你说这事上哪讲理去哪。
宋阿爷他们也很尴尬,被任家村村民们的一双双眼睛望着:那我们到底该不该惨啊?
任族长心里也气。
上面让拿村里的逃荒户举例说事,起到教育意义。
可是他们村里的逃荒户根本就起不到教育意义。
多亏提前取材,深吸一口气,任族长正要大声背诵宋阿爷他们一路上遇到的坎坷,连耗子都没放过都吃过。
下面的村民们又给打了茬:
“都要冻透了,族长爷你到底要说啥。”
“就是,你可别乱举例了,”举例失败。河对岸这伙人不惨,连他们的小伙伴,年前给他们送礼鸭子大鹅的那伙逃荒同乡也不惨。要是向他们看齐,该哭的是我们。
“有惨的,我告你族长叔,在五福村。那家伙哭的,救济粮一停,坐家拍大腿哭。可要我说,那是他家没能耐。”
“您是不是想说让俺们省些吃,别乱造化,现在皇朝不易?晓得啦,早就寻思好了。”
“是,我都寻思好几宿了,愁坏了都。”
任族长泄气,行了,散会吧,一个个都是大明白。
过桥后,宋福生有些疑惑,任族长怎么忽然开起动员大会。
原来古代也爱搞这一套吗?
可咱现代搞这一套会直接说出目的,任族长磨磨唧唧的却没有说出个一二三。
问那老头子,那老头子还反问他:“后生,你是怎么看这事的,我不知道啊。”
怎么看的啊。
宋福生认为:
是不是想先做通思想工作,让百姓们有劲一处使,下一步好开展工作方便于征粮?
要知道,之前,他猜的那些全中。
近几日,那几个王爷真进入“骂街”车轮战。
下一步,搞不好真是征粮。
问谁的参考意见都不如问闺女:
“闺女,你怎么看?”
宋茯苓说:“爹,咱一个吃救济粮的,能怎么看?只要不搜家,就杵在村口看他们被征粮呗。至于管咱们要?可我们是吃低保的啊,低保户,哪有。”
回头宋福生就带着大伙忙于四处藏粮食。
只上山就上了四回。
天寒地冻,挖坑挖地道眼下是挖不动的,只能去寻一寻有没有野兽祸害不到的隐秘山洞。
必须是隐秘的,别再让人捡走。
自从耿副尉打完狼了,村里也有好些人上山。
结果只逮到了三只野鸡,搂回家六只野兔。
又在家里的地窖和地窝子里下手,那里暖和,能挖动,挖,瞎挖,还怕挖塌。东藏些西藏些,家家户户也分一些。
免得粮食凑到一起,给人造成存粮很多的印象。
万一真被搜家,得让人知道知道咱这些粮,分摊各户头上没多少。
四天后,真正的答案揭晓了。
衙役忽然带着张贴告示进村。
一副皇命不可违的架势。
宋福生和宋茯苓猜中了整个王朝接下来会发生的种种事情,却没猜对顺序。
会征粮的,但不是眼下。
眼下是,征兵。
犹如惊雷在每个人头顶炸响。
啥玩应?
让俺们去送人头?
小兵能有啥好命运。
被征徭役,累大劲了都丢命,都有回不来家的,一去就去几年。再听到信就是一把枯骨。
更何况是兵役。
就这种被征走的小兵,啥也不会,不是正规兵,征上去的命运,就是在打仗时,前排用身体堵炸药和箭头的。
无法接受。
现在的新皇,曾经的燕王,百姓们一直在他手下活的挺自给自足。
也从不剥削百姓。
有灾年出现,以前的燕王甚至还会让少交赋税。
这可真是要么不出手,出手就来最大最狠的。
汉子们听完告示,直踉跄的后退,强征,谁不遵守就杀头。
“呜呜呜,我不活啦,没好日子过啦。”当即就有好些妇女,腿一软,跪在告示前嚎哭。
翟婆子哭的,在衙役没走前就胆大发疯道:
“我家老头子让狼咬死了,儿子也被撕稀碎,就剩俩儿几个孙,你还要再征去俩。你干脆刨了我家得了,一把火烧了我们,一个根也别留下,俺们通通进祖坟。”
几名衙役唰唰的就抽出剑,一副要当场砍了大逆不道婆子的架势。
是任族长急忙带人捂住翟婆子的嘴,又是作揖又是赔礼说她得了癔症,给拽走,才算没出现血溅当场的惨剧。
是的,一户要征俩,这很突然。
之前,任族长虽然做动员工作,大伙要众志成城之类的,但是他确实一点儿消息也不知。
只在心里合计,估摸是要征粮。
当时心里还寻思:征吧,早晚躲不过。眼下又没种地,咋征也得等秋收后,以为是赋税会增多呢。
哪想到让他们这些里正先劝劝大家,是为征兵做铺垫。
十五岁至三十五岁,每户两名被征名额。
如若有个别家里,只有一位符合被征条件,少的那个名额就要交粮抵,现在就要交二石粮。(五百斤左右)或以银钱抵。
任族长安排人手扯走好些情绪不稳的婆子,转回身要找衙役,发现几名衙役已经到了村口,正被河对岸那伙人围住。
马老太啥也顾不上了,急了眼。
她几个儿子加上大郎还能留住了吗?
她们当初为何要分成十五户,九族就该合为一户。好悔。
“能不能用银钱抵名额,我有钱,用粮也中,没问题。”
不成。
有一名衙役提醒道:前提条件是你家没有人了,没有十五至三十五岁的,才能用粮用银钱抵。不被征的情况只存在一种:那就是家里只剩老人妇孺。
第四百四十五章 上面有人(一更)
得到了确定的答案,宋九族一众人的心理只剩下:
这可真是从尿窝又挪到了屎窝。
“嗳?”任族长凑上前刚要问问,就见河对岸那伙人,很是冷静地互相呼唤着同伴、搀扶着同伴:“走走走,先回家开会。奶?你小心脚下,别摔了,不至于,不至于气昏,啊?”
任族长又回身看了眼任家村的众人,以及扑上前拽住官差没完没了打听的任公信一家。
平时不对比,感觉不出来差在哪。
这一对比就看出来了。
村里人此时咒骂老天又哭又嚎的,好些家汉子还有问自家爹娘咋办的。
再加上小一辈的娃子们,纷纷拽着自个爹哭喊着:“让大伯去,爹不准去。”有那爹愚孝窝囊的,就原地蹲下抱住头,只会沉沉地叹一声:“唉。”
“爹,你不能再听爷奶的了。”
然后就有好些家在祠堂门口,内讧起来内斗了。
当即就有打孩子的,骂着你爹不去谁去?
“我爹凭啥去,平日里爷奶就偏心你们大房,好事落不到我们三房头上,征兵征徭役倒想起我们这房。”
“你个小丫头片子,家里的事还由不得你个赔钱货说的算。等你爹你哥被征走,提脚就给你先卖了换粮。”
“大嫂,你说啥!”窝囊汉子眼通红,又看向爹娘带着哭声道:“我要是走,就要给我家丫卖啦?”
总之,祠堂门口什么样的人间悲剧都有。
出了问题不先想办法,先内讧爹娘偏心的问题。
任族长紧皱两眉,心堵的没条缝隙。
“爹?”
任族长摆了摆手,让儿子们别说了,也不用说。
他打算向河对岸那伙人学习,“老三套车,咱这就出村问问。我当里正,我还是秀才出身,能不能免了咱家的名额,用粮食抵也成,走走人情,想想办法。”
他三儿子立即痛快地应了声。
哭喊咒骂有用吗?
宋九族的一众成员最有发言权:没用,骂出花来都没用。
要不他们能逃荒嘛。
他们的心里早就被生活磨出一层厚厚的茧子,早就被锻炼出来,遇到大事先冷静,想办法,实在没能力解决了,那就再躺平任由命运磋磨呗。
所以过桥这一路,河对岸这伙人,心里琢磨的全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会议室里,大伙才聚齐。
宋富贵就举手发言,“阿爷,福生兄弟,我想到一招,不知当说不当说。”
“你讲。”
“求人吧,咱上面有人。”
求谁呀。
高铁头抢过话,“三叔,求小将军,擒贼先擒王。”
大郎他们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