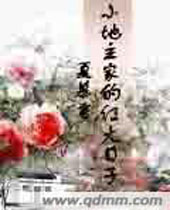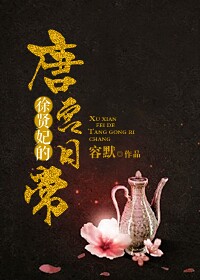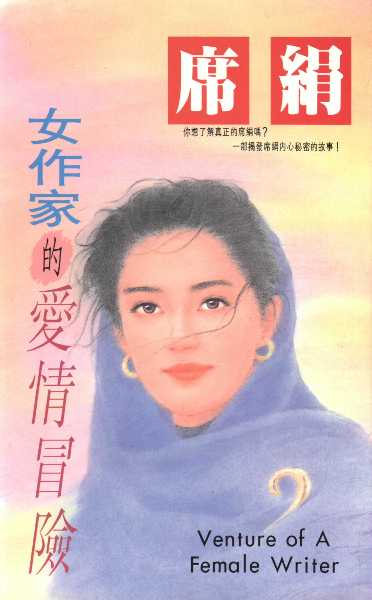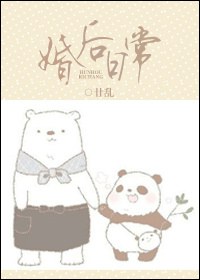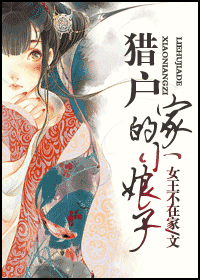慈善家的日常生活-第1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土炕中间是一个小方桌,赵启明也不客气,拖鞋直接爬上去做好。
这种坚实又暖和的土炕赵启明却是有些年头没见了,他笑着对老人说:“外出久了口音上有点变化,实际上我和小余都是咱东北的,就老阮不是。”
“别介,虽说我不是东北的,但我来东北好多次了,土炕什么的还真没少坐,不过南方天气和北方差异还真是挺明显的,就冬天这个气节而言,北方过得还真比南方舒服。”阮正业这时候也不谈工作,笑呵呵地回了一句。
咧嘴笑着,村支书脸上的周围仿佛也明亮许多,说:“那感情好,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拿点花生瓜子。”
第199章。199 收入(求订阅)
花生瓜子红双喜,面前一个烟灰缸,除了余山彤靠得远远的之外,其余四个老爷们都围坐着开始闲聊。
聊了几句后,话题不免又引向各家各户孩子的教育情况了,用指甲抠开瓜子壳,赵启明随口问道:“支书,你家孩子目前怎么样?”
“俺家的那个啊,镇上念初中呢。”吧嗒抽了口烟,然后咳嗽了两声,支书继续说:“那臭小子学得不咋的,不过能咋办啊,只能继续供他读书,我和我老伴都商量好了,孩子中考的时候考差不多点,俺们就花钱让他进市里高中继续读书,最后到底是考大学还是考大专就看他自己了,反正俺们这些大人是做到自己该做的了。”
话虽这么说,但村支书看上去气性不小,虎着一张脸。
‘估摸着你孙子九成九是班级倒数的,不过这想法肯定是没毛病。’
赵启明并未问对方孩子的父母哪去了,也没问是否又二胎一类的事情。
习惯成自然,话题一聊到这,阮正业立马不嗑瓜子了,歪头看了看放在柜子上的小包,最后他还是没下地去拿。
“读书还是很重要的,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让孩子多读读书,别管以后是上大学还是上大专,多学点知识肯定是没问题的。”
听到阮正业的话,村支书脸色缓和许多,很是认同地点头感慨道:“可不是么,俺们家这几个大人也都是这想法,大人吃差点、穿差点都不打紧,孩子的学习时间就这么几年,这是真不耽误不起,就好像种庄稼,你晚个三五天,秋收的时候就减产老多了!”
“说到秋收,我想问问咱们村里营生是什么?来之前我们有打听,说咱们镇上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0块,咱们上午第一个说的那个孩子,好像一个月也都有一两千的月薪吧。”赵启明适时地提出自己的疑问。
一个月按照1000块来算,一年就是1。2万,这和3000块的差距太明显了。
“啊?不到3000?不能吧……去年俺们村儿人均年收入好像也有个一万多吧。”楞了一下,村支书有些糊涂地看向吴科员,不确定赵启明这消息是哪里听到的。
“呃……可能是我当时说差了吧,2800的那个是纯收入,镇上去年的人均纯收入。”吴科员也有点懵逼,磕巴了一下,有些慌乱地解释。
钱这方面不能说谎,万一人家觉得自己是在忽悠对方就很不好了。
“哦,那可能是我记错了。”赵启明也不深究,这些天见闻多了去了,他光记着一个数据了,而且赵启明觉得他记错的概率要大于吴科员说错的概率。
“全镇人均纯收入2800,那咱们村上是什么情况?”赵启明继续问道。
“这个啊,怎么讲呢,纯收入和每年攒下多少钱是不一样的,俺们村儿这的纯收入一般说种地花了多少钱,然后粮食卖了多少钱,在种地上剩下的那块叫纯收入,但俺们老人多、孩子多,就青壮年人不多,所以种地这一块也谈不上收入不收入的。”
“你问的应该是一年能攒多少钱,正经说这一年到头能攒多少钱的话,这块不好讲,情况差一点的,一年到头也就能看着三五百,情况好点的呢,一年到头也就一两千,这还是你家不能出大事,这要是赶上老人生病啥的,那别说攒钱了,家底掏空了都未必够,保不齐外面还得欠钱。”
村支书先是简单解释了一下‘纯收入’,然后才说村里的情况。
脑补了一下上午得来的信息,瘫痪在床的、药罐子的、腿脚不好的,可以说留守在村里的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
但外出打工的好像有五六百人,首先可以明确打工肯定会去相对繁华的城市里,诚然在那些城市里生活成本会大大提升,但收入应该也是同步上升的,如果每年存不下来钱,那何必远赴他乡去打工。
这村子是贫困村,但不是残疾村,这人在外地打工把钱邮到家里,结果最多的就能攒下一两千,感觉不合理啊。
赵启明虽然不想从阴暗的角度来考虑今次的所见所闻,但他不得不为自己基金会的钱财而担心。
基金会可以花钱,可以花大钱,但前提是要真真正正地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希望这钱能做到‘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更不能这边捐钱了,受捐人一边心安理得地大手大脚花善款,一边骂赵启明是傻叉。
不过当着村支书的面,赵启明肯定不会说这些内容,他决定今晚嘱咐一下阮正业。
看到赵启明在沉思,大家不方便继续往下聊,正巧这时候村支书的老婆,也就是先前进屋看着的那老太太说饭做好了,大家也赶忙收拾小桌准备吃饭。
午饭很简单,红豆米饭作为主食,菜只有四道,分别是猪肉炖粉条、猪皮冻、炒鸡蛋和白菜炒肉。
猪皮冻是一道凉菜,用筷子加起来颤颤巍巍地,粘上点酱油蒜末,吃起来味道非常好,口感Q弹得很。
“今天呢,欢迎赵总带队来俺们村儿来考察,无论最后结果如何,俺代表全村儿人,先感谢赵总几位了!”先前言明不喝酒,村支书以茶代酒做开餐前最后一道工序。
“支书客气了。”端起茶杯矮一截碰杯,随后喝了一口廉价又苦涩的褐色浓茶。
在对方没有大过的情况下,赵启明首先要尊重对方的年龄和职务。
放下茶杯,支书拿起自己面前那双都掉漆的木质筷子,示意大家趁热吃的同时,开口道:“临时通知说今天赵总过来,家里也没什么准备,幸好上次去镇上的时候割了一刀后鞧没吃光搁外面冻上了,要不然今天都不知道拿啥招待几位。”
赵启明不知道一刀是多重,但却知道后鞧是屁股肉,泛指猪的屁股肉,心下却想着吃完饭一定要留钱才行,对方不是富裕人家,不能白吃人家米和肉。
“支书客气了。”再次重复这句话,赵启明暂时不打算说饭钱的事,他准备临走的时候偷偷放这屋里,免得这老头倔强不肯收。
第200章。200 留饭钱(2更求订阅)
今天这午饭吃得还不错,虽然饭菜味道很一般,虽然碗筷陈旧有破损。
但吃饭不只是简单地摄取能量来维持身体机能,吃好、吃饱也是要看和谁一起吃。
这有些年代感的房间让赵启明想起上一世那已经模糊却依旧挂怀的画面,眼前这老头老太也都面容和煦、和善,虽说这老头胡子拉碴满脸是褶,而这老太看上去也不像是有文化的人。
但是,这已经很好了。
现在猪肉三四十一斤,人家这么一个普通甚至是贫困的家庭里,四个菜里有两个放肉来招待他,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严格来说,猪皮也算肉。
不严格来说,鸡蛋也算肉。
四舍五入,今天这菜都带肉!
饭后,看到余山彤起身要上厕所,赵启明也下地跟了出去。
“赵哥,你要干嘛!”余山彤很是警惕地看着赵启明,生怕他来个不正经地偷窥。
村支书的家是老房子,左手侧是平方,另外三个方向是围墙,小号的话在家院门后面有个蹲便,问题是这蹲便就左边和后边有墙挡着,这要是有人出屋,虽说距离远未必能看清楚,但动作上肯定是能辨析出来点什么,因而她还是蛮在意的。
至于说为什么不去四周遮掩上面带顶棚的公厕,村支书表示那是大号才去的,据说一层层累高成金字塔形状的便便,已经超过蹲便两侧的脚踏板了,如果不擅长用蹲便的话,很大概率会戳到菊花……
心中笑着丫头年纪不大懂得不少,但赵启明并未把心里的想法展露出来,而是表情如常、压低声音说:“一会走的时候你留在后面,给人家留……500、不留1000块,放个他们一时半会注意不到的地方,等晚上咱们回去了,你再通知一下这村支书,人家也不容易,饭钱还是要给的。”
虽说这次过来工作是阮正业主持的,但赵启明不认为自己是个透明人,村支书老夫妻和吴科员肯定会随时留意他的举动甚至是神情,这种藏钱的高级工作他肯定是搞不定。
至于说这四菜一饭值不值一千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哦,我明白了。”听到是在说正事,余山彤松口气的同时,心里也是有些懊恼。
‘果然就不该和我老爹说和老板出差这事儿,都给我带歪了!!!’
余山彤内心中有个Q版自己在疯狂地捶打胸口,然后仰天长啸。
不用这小丫头撵自己走,嘱咐完之后,赵启明转头就回屋了。
脚步快挪到院门附近,余山彤直勾勾地盯着左手墙壁延伸至十米开外那看不见的房门。
寒风肆虐,也不知是天上自然降雪,还是这风吹落些许房檐上的积雪,余山彤哆哆嗦嗦地蹲下。
酒足饭饱后,大家稍事休息就又去村委会了。
倒不是非要很形式地在那办公,而是村支书年岁也大了,虽然能背诵全村的情况,但多多少少也是要对着村里人的名单,否则容易漏掉。
作为最漂亮、最年轻的女……孩,余山彤如赵启明所预料的那样被忽略掉了。
坠在最后,把早就准备好的一沓钱从怀兜里掏出来,装作低头系携带,她顺势将钱塞进柜子下面,随后假装自己系好鞋带起身,若无其事地起身跟在最后。
午饭闲聊的时候,聊的是家常话,赵启明自然也没保留地表示他过几天就要去春城丈母娘家,因而回到村委会后,村支书不再像上午一样有的没的一通絮叨,而是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挨家挨户说明情况。
73户人家、178个18岁以下的儿童,27个有书念的儿童。
细分的话,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困难,每个儿童都有各自辍学的理由。
听着这一桩桩具体事例,赵启明有些茫然,他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激发儿童学习热情、帮助困难家庭的同时,不会滋养出好吃懒做的学生与家长了。
‘或许,这也是他明明以前所在基金会有过调研工作,但最后没能落实的真正原因吧。’
看了眼认真记笔记的阮正业,赵启明心中感慨一句。
同时他也好奇为什么阮正业、余山彤,明明手机录音功能可以代替写字做笔记,但这俩人却偏偏要用手写这种缓慢且容易遗漏的方式来记录。
赵启明有看过高中毕业生余山彤的记录本,不提那稍显简陋的笔迹,单说其发明的‘通假字’,就让赵启明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种天生自带密码的记录方式。
村支书一个下午嘴就没停过,最后在老人一脸不舍的情况下,赵启明四人驱车返回光明镇。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没多言,因为赵启明三人需要在脑子里过一遍今天的所见所闻,然后根据今天的所见所闻来提出各自的想法,这种想法最后将会被打磨成本次教育扶贫的具体内容。
中午这顿饭对赵启明而言,无论是味道还是类别都有点素,晚上在旅店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点了好几盘肉和烤串。
东北的锅包肉不用番茄酱,因而外表看上去就是淀粉炸过后的金黄,外面裹着一层白砂糖熬制成的透明包浆,有点琥珀的感觉。
厨子做得不算地道,肉酥过了头了,不过好在这烤串味道着实不错,念在宁玉燕不在身边,赵启明也没点诸如腰子、韭菜一类据说很补的串,免得晚上念想太多。
虽然赵启明有邀请,但吴科员表示他还要去单位汇报工作,因而就没跟着一起吃,饭桌上,大家也以闲聊的方式阐述自己的想法。
为此,余山彤特意拿出一根据说可以连续录制8天8夜的录音笔。
赵启明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她,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老了,他有点理解不了为什么明明提笔忘字的余山彤,之前在有录音笔的情况下还选择手写。
看到余山彤连忙低头看看自己哪里有不对的地方,赵启明撇嘴,然后扬扬下巴,说:“边吃边说,老阮啊,咱们这次的项目要多方面考虑,最重要的是,如何鉴别家长、家庭层面的东西,咱们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咱们不养懒人家庭,要知道读书的确能改变一个家庭,但过度得慈善也会改变一个家庭,我可不想未来咱们资助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上网诉苦谴责咱们不继续帮扶,又或者跑出来几个家庭天天无所事事就指望着咱们的捐款过日子。”
“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