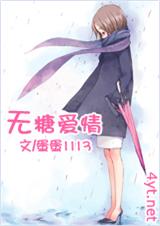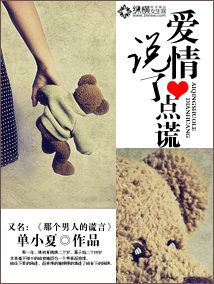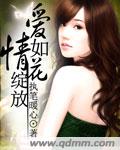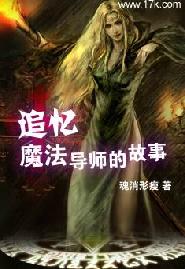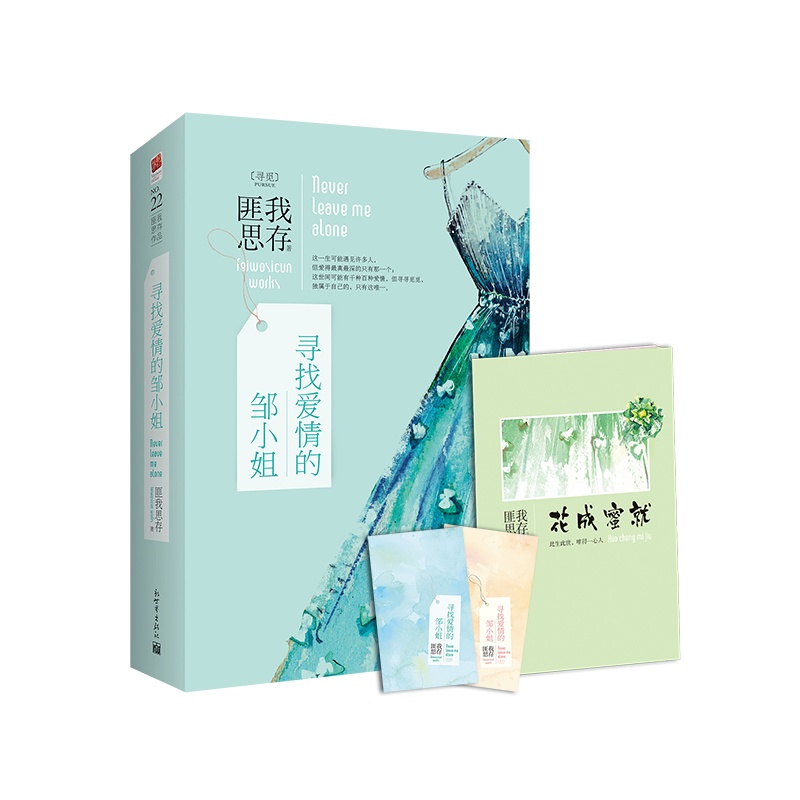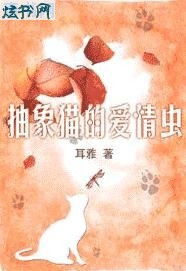琴岛爱情故事-第7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长荣外运(二十五)
一个多月没有回来了,怎么感觉有很长时间一样。坐在车里,孟林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象,回想起读书的两年,不少次都是骑自行车奔跑着近一百里的路,早已成为过去了。
坐上跑六水的车后,立马就觉出比起灵水到胶原那段路差远了。真是两种景象,人家那里有山有海的,而出了胶原西行五六华里就进了重重山麓包围的山里。这条路又是回家最近的必经之地,光上下的大陡坡就有十好几个,想想读书时骑车那是什么样的劲头啊!
这两年自从这路铺了柏油路后,好走的多了。
“孟辉,你说我们这地方啥时候能开发过来啊?”孟林闲的无聊跟哥哥聊起了天。
孟辉摇了摇头,感叹道:“我看够呛,胶原都才刚刚开发,十年二十年的就别想了,你看咱这里那有平地啊,丘陵除了种地还能干啥呢?”
“是啊!办企业也得需要水啊,咱六水还不如胶北乡好呢,人家那里还基本都是平地,相隔三十来里地差距就这么大。”孟林也不得不抱怨自己出生的地方了。
车到五道口时,离家就近了。
“这个地方倒是个好地方,只不过没人来开发,你看连个饭店修车的都没有,不过这里早晚会兴旺起来的。”孟辉指着窗外的五道口自赏道。
孟林也觉得这三岔路口地理位置不错,不得不佩服起哥哥的眼光来,不过凭现在自己的能力,想在这块地上立足发展谈何容易啊。不过一直藏在他心底的一个疑问,“这里不是三茬路口吗,怎么会叫五道口呢?”
孟辉说,他也是听爷爷讲过:五道口这个称谓也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具体啥时候就叫五道口了也没有记载,相传这边没有修路的时候,四通八达的有五个路口故此就叫五道口了。
与五道口紧紧相靠的就是东西蔓延数十乡铁镢山,这因此就成了六水镇的天然屏障。
又是丘陵地势的山地,到了夏天这海上的风吹不过来,因此热就在所难免了。而到了冬天,这东北风没有遮挡的从北方呼呼的刮来,冷又成了六水镇这带的独特风景。
要不这里的百姓看天气从来就不依着胶原的预报为准,夏看西南,东看西北。因为东有月季山,南有铁镢山,即使有雨有风的也就给挡在山外了。
现在已进入九月份了,离中秋节也只有二十来天了。八月十五的临近,标志着农民一年当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秋忙就要拉开帷幕了。
看来这小哥俩别说秋收帮不上忙,就连中秋团圆节也要在外面过了。
俩人在村口下了车,正好碰到二婶。
“婶子,上坡来啊?”孟林走上前要接过她挎的篮子。
二婶子憨厚的一笑,这才发现面前竖着的两个大青年是自己的大侄子。
“是小林、小辉啊,你们这是刚回来啊?”二婶热情的问候道,“不用,我来挎就行,弄身上泥。”
“没事!”孟林还是抢过去篮子,里面是几墩花生,“婶子,花生熟了啊?”
“哎!对了,你哥俩摘着吃。我去北坡那地里拔了几墩看看,还行挺饱成的,就是让‘地里滚’给吃了不少。”二婶说着摘了一把递给孟辉。
“婶子,我叔回来了吗?”孟林怕上次带给叔叔的话,他没有兑现。
二婶兴高采烈的说,“回来两次,你去琴岛没多久他回来过一次,这不前两天你大妹妹去上学,他回来去送的。”
“孟洁考上大学了?考哪里去了?”孟林听到消息高兴的问这问那。
“去北京清华了,读得鸡算鸡,我也搞不懂,鸡怎么还要算鸡呢,反正还要读四年!”没什么文化的二婶说也说不完整,不过大体意思还是表达出来了。
孟辉猜测了一下,呵呵一乐:“二婶,是计算机吧?”
“可能是吧,我也不明白,你妹妹说还叫电脑。”二婶又解释了一番。
“对,没错。这是好专业啊,还是本科生。真不错。”孟辉也替孟洁高兴起来。
孟林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喊了起来,“我们孟家也出大学生了!还是去首都,哈哈!”
“孟林,你喊个啥?”二婶见他为自己考上学的女儿这样高兴,心里也乐滋滋的。
这种人前的感觉在女儿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在整个孟家村就沸腾了好长一段时间,连村里大小干部都来祝贺,二婶家真是添了彩。
侄女考上了大学,孟庆安也跟着高兴了好几天,怎么也得摆酒庆贺一下吧。那时兄弟庆国还没回来,全家只好帮着兄弟媳妇忙活了一些日子,孟庆国收到信时说要亲自去京城送女儿。
他觉得也是孟家的福运到了,孟洁毕竟也是在近年来,第一个从孟家村考上名牌大学的学子。大队里还特意从有限的经费里拿出八百块钱表示鼓励,希望村里能有更多的孩子考上大学。
听着母亲讲述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孟林不时的打断询问细节。孟庆安在旁边半天说了一句,“有本事你也考啊?看人家小洁,这才叫真本事呢!”
“就是。”母亲也响应孟庆安,关心起儿子来,“小林,学校给你分的活咋样啊?干什么活啊?”
这从何说起啊?孟林收起了刚才还兴奋的脸,有些无奈的说:“娘,现在这事真的不好说了,上次那事早就过去了,我是前天刚收到信的,昨天又刚到学校看了看。”
孟庆安明白了儿子所说的意思,有点生气的说:“你看看,闲的没事瞎跑,把正事给飞了吧。”
孟林只有认真的听着父亲的责怪,也不敢反言。母亲倒是帮是出言相劝了,“行了,你也别埋怨儿子了,以后还分不分了呢?”
孟庆安气的又掏出烟袋包卷起了纸烟,眼看着14寸的黑白电视但耳朵却听着她们娘俩的对话。
孟林不愿意再让爹娘为自己牵肠挂肚,只说是在琴岛的一家外运公司里上班,待遇还行钱能每月按时发。什么扛包啊只字没提,他怕让父母知道后担心起自己的体格是否受得了。
然后又从口袋里拿出三百块钱来,递给父亲说:“爹,这是我上个月的工资,给你们一半用,剩下的我还得当生活费。”
孟庆安瞥过一眼,憨厚的说:“算了,你快拿着用吧。”
父亲没去接自己手里的钱,又跟母亲说:“娘,你们拿着用吧,我也没有多,等能挣大钱了再给你们多钱。”
“大钱?什么是大钱?现在刚找活,能挣的刚自己花的就行了。”孟庆安又在用语言打击他。
老伴听不下去了,埋怨孟庆安说:“你就别说风凉话了,孩子找个活就怪不容易的了,你还不住下的说他,拿来家钱就是好的。”
孟林见母亲帮着自己说话,心里挺高兴的,把钱递到她跟前,“娘,你就把钱收起来吧?”
“小林,这钱娘就先替你存着,给你留着娶媳妇。”
母亲也不过是找个籍口给儿子放着罢了,要真每月就这么点钱,估计娶媳妇也不会够。
孟林告诉他们,已经把联系电话留给李霞老师了,有什么通知就知道了。
这一夜孟林睡的很香,自从去了琴岛后,已没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了。那木头板子支的床,确实睡不好,但又想挣钱,就得学会忍受吃苦。
孟林回家的第二天,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老天爷整整得淋了一天的大雨。
这场雨,把六水集给延了,还没有到秋忙的时节,下点雨也无所谓。就怕碰上涝水天,那可就麻了烦。
当地的农民,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最担心的却是那总让人琢磨不透的天气。要在平常也没什么关系,一年农忙的两季要是凑巧赶上了都不是好天,那这一年减产的收成可就无可估量了。
本来就指望靠天吃饭的百姓,再赶上个不收年,损失可就大了。听老人们说,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遇上过。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丘陵地带的因素,干旱是常有的事,要不说农民种地真是不容易啊。
孟林记忆中,有一年的涝雨天致使收花生时,地里的水浸到了脚腕。泡水半个多月的花生,收不及时的花生好多在田里就扎了芽,倒置那年大副减产。
透过还是那种五六十年代流行的木头栅格窗的窗棱,望着院子里落地成流的雨水,孟庆安叭哒叭哒的抽着旱烟,脸上布满了一种对前景的担忧。
老伴坐在炕头上,旁边守着针线筐,手里在补着一条称裤。趁着下雨天有空,就收拾出过秋的衣服来缝缝补补。怕八月十五一过,就一个心思的忙着收拾庄稼,哪还有时间做家务。
孟林贴着炕头伸着腿,身子靠在墙角的被子上。秋雨带来的寒气,使他也懒得出去串门,不时被炕灶热火的余温烙的腚有点麻,就不时的侧侧身子。
母亲看见情形笑着说:“儿子,你要嫌烫人,就往那边挪挪。”
说着把摆在炕上的衣服和针线筐往边上推了推,孟庆安坐在一边悠闲的喝着茶水,他也难得能有空像今天这样在炕上喝着个茶水,看着电视。
孟庆安看了一眼儿子说:“年纪轻轻的,没有骨头没有腰的,往炕上一躺成什么样子,到人家里可不兴这样啊?”
“知道!我也不是小孩子!”孟林眼睛紧盯着那台黑白电视上的节目。
老伴也接着嘱咐自己的儿子,笑着说道:“你爹说的对,等你找了对象,去你丈人家出门可不能就这么一躺,那人家门上的会笑话的,说咱没有家教。”
“娘,你真说的吓人,这事我哪能做的出来啊?”孟林不服气的给自己争辩着。
孟庆安扔掉手里的烟屁股,又把手伸进烟袋包里捏了一撮烟丝,撕了一张卷烟纸,目光也落在那台14寸的黑匣子上,说:“这可说不准,你这小子没有做不出来的,从小就办事跟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到时候他丈人还不得拿着笤帚揍他啊!”
“你就看得出来啊,会算啊?”母亲不愿意听着老头子啥说,一句话给顶了回去,停下手里的活说,“你就知道吃你的烟,看看把屋子里都快熏成垄烟屋子了,怪呛人的,再吃到天井里吃去。”
孟庆安嘿嘿的一乐,继续卷着那袋烟,笑着说:“看看,在家你娘成大管家了。好不容易歇一歇,在家喝个水挨说,抽个烟也要挨批。”
孟林看见老俩口伴嘴,他知道爹娘也吵不起架来,笑着说:“爹,我娘嫌你吃的旱烟呛,你吃我给你买回来的烟卷吗?”
“你那烟卷没劲!”孟庆安还是把烟放进了嘴里含着,用火机点上说,“算了,你们嫌呛,我到堂门去吃。”
孟庆安下了炕,拱上黄胶鞋就走堂门了。母亲小声说:“你爹他不是嫌烟卷不好吃,是不尬舍吃,来个帮着干活的来个客的也就分散了,他是留着充门面。”
孟林顿时觉得父亲很伟大,伟大之处就是他考虑的事情那么细致,干的农活比谁都上心。但同时,在孟林的心里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很大,是自己发现的。
不用说远的,就说眼前的吧。箱顶上那摆着14寸的电视机是两色的,还是二叔三年前从琴岛旧货市场寻回来的宝贝疙瘩。说是一百块钱买的,钱也就不要了。而他自己家里也是一起弄回来的一个14寸的旧电视,不过是个彩色的,有七八成新。说父母都不在了也算是孝敬哥哥嫂子,为此孟林的母亲还老觉得欠了兄弟的一个人情。物非所值,在孟庆安眼里给就拿着不给也不要,每年光帮着兄弟媳妇忙收忙种的,出多少力啊,一台旧电视机的到来显得就不那么兴奋。当时孟林正好读初三,还担心影响了儿子的学业呢,事实证明孟林确实也没考上重点高中,但孟庆安也没有把帐算在兄弟送的这台黑白机上,学没考上只能怪自己儿子不争气,与别人没有关系。但说实在的,要让孟庆安俩口子花一百块钱去买个破电视机回来摆着,他才不会同意拿着能买一袋子复合肥再加两袋碳铵肥的钱买它回来呢。
电视机好看是好看,但它是要吃钱的。就像拖拉机没有油不跑,电视机没电也不出影,不知不觉的在每月的电费支出中又增加了额外的一份开支。自从孟林去灵水读书后,电视基本上成了装饰品,除了定时看看中央、省、市的天气预报外,孟庆安都懒得去理这台喝电如喝水的四方盒子。
再说说这栋房子,历史可真是相对地悠久,那是在孟林三岁的时候盖的,转眼孟林都十八岁了,而这座安乐窝也风里雨里的经历了整整有十五个年头了。
说到房子,就不得不提孟庆安。
孟庆安自打成为家里的主劳力以来,加上现在的南屋。光大的建设就盖了三处房子,现在二叔住的那座房子也是孟庆安一手操持的,期间出的力就无法估量的了,尤其在那个吃不上饭的年代,盖座房子可想而知是多么艰难的事。
就说现在住的这座房子吧,窗户还是老式的木头栅格窗,而如今村里有钱的人都换上了透明的玻璃窗。现在屋里流行刷涂料刮泥子了,家里的四壁还贴着厚厚的报纸。这确实是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