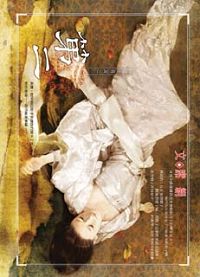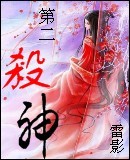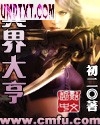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2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新的工党并不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简单延续或改组,而是其他传统政党中进步人士的融合,社会民主党在这里面仅仅起着一个核心的作用。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很可以被称为“传统的”政党,这同各个教派政党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该党迟至大战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党派合作,也尽管该党在战前最后两次大选中都取得了议会中第二大党的地位,但这些都并没有给该党带来什么好处。它象其他几个西欧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那时就已患了一种慢性衰弱症,而随着大战的进行和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显了。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各个社会党工会,都没有能在德军占领期间起来应付时艰,结果是,共产党工会从社会党工会那里吸引走了大批成员。
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意识到共产党在吸引他们的追随者,但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些损失的机会,其办法是,把自己同那个正在席卷政治上的整个中间派阵地,甚至还渗透到了一部分右派人士中去的强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他们可以说,这个运动无疑是由社会主义思想所启发的,虽然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基督教的个人神圣原则。因此,该运动在荷兰的第一号旗手舍默尔霍恩把它叫做“个人人格至上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个人人格主义”。它的宗旨是要实现所有那些基于各自个人的人生观而倾向于同一政治理想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生活上的多样性,在一个稳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统一起来……同时保证各个不同的团体在社会结构范围内各自保持其个性,而不致被某个中央机构的权威所淹没——甚至也不被国家的权威所淹没。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党,是由背景和见解很不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都希望创建一个既是民主,又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而基本上却是基督教的新型社会,在这一共同目标上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党无疑填补了荷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随者对它在战后第一次选举(1946年5月17日举行的议会第二院选举)中没有能取得更大胜利颇感诧异。该党原希望在第二院的一百个议席中获得三十五席,但实际仅得二十九席,而天主教党则得三十二席,三个新教的政党得二十三席。正如人们所预料,工党采取的那种断然拒绝共产党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它失去许多选票,特别是前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这些人转向了共产党,从而有助于增加共产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使其从1937年时的三席增加到十席。另一方面,天主教党成了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有百分之三十一的选民拥护它。它由于割断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个加尔文派政党的关系,由于消除了反动的嫌疑,又由于1945年12月间向赞同它的总政策的非天主教徒开了门,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的确,可以这样说,在荷兰象在比利时一样,从敌占期间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最大的好处的是天主教徒。尽管社会上有贬抑教派主义的倾向,但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教会——只要它的门面稍加现代化——还是比新的含糊的“人道主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因为工党没有能在选举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制局面的地位,它面临着或者同天主教党合作或者进入反对党行列的抉择。虽然该党领袖们由于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对同天主教党合作可能有些踌躇,可是,他们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同共产党人在反对党行列内携手合作,而且,反对党行列中除有左翼极端分子外,还有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同后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兰,现代社会党人同进步的天主教党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难之所以比在大多数国家少些,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党内极端派的掣肘。同时女王选中贝尔博士为新首相,这也使工党作出抉择更容易些。贝尔博士属于天主教党的左翼,以进步人士著称;而且他也曾是舍默尔霍恩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制订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明政策。所以天主教党和工党在这一殖民地问题上进行合作,将是比较容易的,而政策的连续性也会得到保证。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否认1946年5月选举的结果是舍默尔霍恩及其社会和财政政策的失败,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天主教党虽然参加了他的政府,但对他的社会和财政政策是常加攻击的)。因此,天主教党人现在似乎得到了选民授权来改变这些政策,如果它愿意作这种改变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要同工党成功地进行合作,在它这方面显然也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并改变它迄今为止所表明的政策。
总之,贝尔博士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间派集团是当务之急,因此,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点。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时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宣布:荷兰银行将实行国有化;某几个工业部门也将国有化,如果调查结果表明这样做是可取的话;但是他又宣称,政府认为国营的办法将逐渐让位于私营企业,让位于一些被赋予特殊权力的半官方性质的职能性团体。这样,他一只手抛出一点东西去讨好社会党,另一只手也抛出一点东西去取悦于他自己的天主教党。关于帝国政策,贝尔表示他不打算明显地背离前届政府关于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妥协的政策。由于上面讲到过的理由,印尼问题深深激动着公众舆论,在议会的大部分讨论中占着支配地位。共产党主张让这些殖民地完全独立;工党赞成和解,赞成给予“自治领地位”;反革命党和国家改革党则反对一切妥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虽然都是右派政党,最后还是同意了政府对印尼的政策。天主教党的态度起初游移不定,但最后该党的多数派支持了政府的妥协计划,那些接受不了这个计划的人则从该党分裂出去,组成了天主教行动委员会。
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天主教党取得了第二院一百个议席中的三十二席,工党取得了二十九席,两党合起来就几乎控制着该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三个新教政党共计有二十三席,共产党有十席,自由党有六席,合起来成为内部极不一致、极无组织的反对派。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显然完全不是一种健康的局面。共产党人——虽然他们不论在朝在野都无疑地将扮演他们那种现已习惯了的“别有用心”的角色——无论如何总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对党派(自由党也应算是其中之一),看来目标既如此模糊,所依据的概念又如此陈旧过时,因此很难提出一般选民会感兴趣的东西。
例如反革命党,它至少在理论上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执,然而仍在拼命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作斗争。虽然它自称在社会问题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种刻板的加尔文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沙文主义的味道,几乎无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个极端保守的政党的烙印。舍默尔霍恩曾这样谈论它:“它尽管原则上讲不保守,却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阵营里。”但他接着又说(这些话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练成熟):“我认为,没有一个党派敢公开自称保守,这种情况对荷兰的政治是有害的,因为我深信,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义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从理论上说,第二个新教政党基督教历史同盟应当算是典型的保守党派了,因为它是从反革命党分化出来的,是由反革命党中那些对该党在1900年前后日益增长的民主倾向表示不满的成员组成的。然而,这个新党到头来恰恰在宣传劳工立法改革这一点上,试图把调门唱得比它的母党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第三个新教政党国家改革党,象反革命党一样,主张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面严格按加尔文教派的原则行事,在印尼问题上也和该党持同样的立场;就这些方面而言,它是另一个实际上保守的党派。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所谓“全国基督教阵线”范围内的松散的联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坏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破坏着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么样,他们只能是共产党和自由党的不稳的伙伴。
自由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更有条件来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原来的自由国家党一度曾经是抗衡那些属于两大教派的教条主义政党的一股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可是经过不断的分裂,它的力量大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只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选民支持它。接着,在战后,又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党里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个“自由党”,吸收了原自由国家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不乐于参加工党的人。自由党举着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旗帜;它主张自由贸易;它虽然在原则上并不拒绝社会立法,却反对国有化,反对限制自由企业。可是在1946年选举中,这一新生的自由党仍然只赢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选民的支持。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理由是,它既反对天主教党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但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已经由当时联合执政的工党与进步的天主教党人之间的联盟所担任了。
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于战后荷兰情况所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批评是,局势过于平静、过于单调了——尽管经历了战争和敌占的巨变,尽管在殖民帝国内发生了造反,国内开始时也有过向往改革和进步的热忱,政治生活却仍回复到了几乎令人失望的常态,或者不如说是回复到了战前的原状。因此,当美国宣布了那个帮助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时,荷兰财政大臣利夫廷克几乎带有哀伤的情调宣称:“我们生活的地方离政治风暴中心还不够近,因而没有条件取得政治贷款。”然而,发生了这么多真正的变化而在外表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改动,这实际上也许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同样享有的那种政治上的顺境的一个象征。
第四章 丹麦
第一节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丹麦已经获得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成功、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国家的名声,而且,虽然它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一些邻国所遭受的许多苦难(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没有遭受这些苦难的全部),可是到战争结束时,它同这些邻国不同,国家生活和各种制度的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完整无损。这一可喜的局面也许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同别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稳定发展的轨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麦人对之记忆犹新,从而使它得以胜利地熬过敌人占领的折磨。换言之,丹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处于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它在被占领期间并没有准备去奴颜婢膝地屈从纳粹的压迫,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中也并不感到有共产党图谋夺权的危险。正由于丹麦改革家们的这些成就,丹麦这座国家大厦已被打扫得如此清洁卫生,那种很易于滋生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不满的病菌已很难找到几个没有打扫过的角落来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丹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较晚,它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所以比较迟,那是由于1849年它在民主政体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过早,也过于突然。当然,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在出现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保留着,可是就丹麦来说,却是为时太早,因为它势必从专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转变为民主,而大多数有关的其他国家,早已在这之前的一系列发展阶段逐渐甩掉专制制度了。
就象别的一些实行议会制过早过猛的国家一样,丹麦先曾于1660年走向另一个极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政权。这个在理论上说来是专制的政权,在其后期却采取好几个走向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而在1849年,国王还居然让这个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宪法。然而,这一措施,却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中间,压出了一阵反动,这阵反动之强大,足以使宪法条文几同虚设,并把民主自由的实现推迟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继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