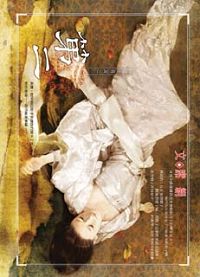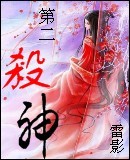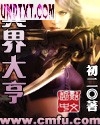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一系列演说和行动来反对英国的政策与目的。这种困难局面于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发表了一次演说后发展到了顶点。他在这次演说中使用的词句似乎修改了早先以他的名义作出的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诺言。他说,法国取得它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从国联接受下来的一项委任统治权而得到的。叙利亚的最终独立一向是法国的目标,的确也是委任统治的目标,但是只有法国才能宣布叙利亚独立。不论他多么希望促进叙利亚人争取独立的愿望,他却不能就这样一个问题用法国人民的权力讲话,而法国人民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国肃清了敌人并由他们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后,才能宣布他们的意志。这至少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对戴高乐的话所作的解释。
因此,近东的不安增强了。这种形势同中东的军事需要完全背道而驰。这使英国政府向民族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要求。戴高乐外出时,民族委员会继续留在伦敦,由普利文临时担任主席。英国政府要求戴高乐立即回来就叙利亚问题,并就马达加斯加问题举行会谈。戴高乐稍事拖延后,表示同意,并于9月25日再次到达了伦敦。
如果说戴高乐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次发生困难的话,那么,他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为紧张。戴高乐在叙利亚时,认为时机适当,曾向美国驻贝鲁特的领事提出两份备忘录,拿他自己的中东政策同英国的中东政策作了不利于后者的对比。国务院并不赞同他的看法,这种局面丝毫没有因为戴高乐同温德尔·威尔基在叙利亚的一次会晤而有所缓和。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戴高乐意见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它们甚至报道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英军撤出近东国家,否则,他将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不论这类报道多么不真实,甚至多么荒谬可笑,它们对于维希和轴心国的宣传却是天赐的资料,同样也使各盟国感到十分为难。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英国外交部同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之间在伦敦举行了会谈,目的在于就叙利亚问题拟定一项新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应该确立一种在包括埃及在内的一切中东事务上进行相互磋商的程序,并建议民族委员会应保证于1943年春在近东举行自由选举。这个计划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民族委员会征求贾德鲁的意见时,他对这项计划横加批驳,于是戴高乐拒不接受。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为此辞职。普利文接替了他,一直担任到几星期后马西格利加入到戴高乐这方面来时为止。
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一无结果的谈判刚刚破裂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件,使整个战局完全改观,并对“战斗法国”运动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关于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美国当局为了取得法国人的合作而采取措施的情况,均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予以叙述,而在本卷的前面一节里,我们也曾述及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为争夺希望见到盟国事业获胜的全体法国人的领袖的斗争,以及1943年6月最终组成设在阿尔及尔、并由两位将军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谈判经过。这里需要谈的只是,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也规定了结束战斗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步骤。英国首相于1943年6月8日在下院宣布,集体负责的新委员会的成立已经代替了他个人和戴高乐于1940年8月7日交换照会后所产生的那种局面。换句话说,后来称作战斗法国的自由法国运动已告结束。
戴高乐本人以及他的主要合作者在把他们的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以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戴高乐先在北非,后在法国本土的进一步活动,不属于本章所要讲述的范围。
附录: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
1940年9月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远征达喀尔的失败,其全部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仍是一个看法不同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维希政府是否知道这项计划,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么,他们之所以会事先知道是不是因为戴高乐的军官在公开场合上说话不慎所致,总之,失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显然是情报不够准确。自由法国总部声称,他们知道达喀尔有很大一部分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及许多高级军官,都是赞成戴高乐的,不过,他们也承认新任总督布瓦松是坚决支持维希的。达喀尔的防卫力量拥有的大炮比英国和法国情报部门所估计的数量要多、口径要大,驻军的人数也比估计的要多将近一倍。事后才知道,驻军士兵部情愿服从原有的指挥官的命令,而这些指挥官即使不是全心全意一致支持贝当的,也大多对夏尔·戴高乐将军这个他们一无所知的人物抱将信将疑的态度。在商人和居民当中确实有一些支持戴高乐的人,但是,这些人既不热情,又无组织。
虽然如此,这次不幸的远征由于一连串的错误而更为不利,结果,一支由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组成的维希护航队,载着援军和补给品,在英法远征军到达之前抵达了达喀尔。除了这些舰只和卡萨布兰卡驶来的一两艘潜艇为当地的防务增添的力量以外,对米尔斯克比尔事件记忆犹新、满怀怨恨的法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人员也被送到这里来操纵陆上永久性防御设施的大炮,以代替有色人部队的常规人员。弹药和鱼雷的储存量增多了。驻军的士气也相应有所提高。这一不幸的责任不能归咎于自由法国方面。维希的增援部队9月9日离开土伦,当时盟国的远征军已在公海上。这支舰队出发的消息都用电报报告了伦敦,然而,出于行政上的疏忽,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竟拖延了几天后才让最高当局知道。此后,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那些巡洋舰和驱逐舰早已驶过直布罗陀海峡,邻近海域里的英国军舰却不够强大,无法拦截它们。它们于9月14…15日夜间抵达达喀尔,比远征军早到了一星期。
同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不幸事件。象原来设想的那样,袭击达喀尔定于8月份的最后几天里进行。那未其附带的结果将是,盟军应在维希增援部队之前到达。可是,不断的耽延(其中有些是很难原谅的)使日期推迟到了9月22日。刚要出发以前,发现随同远征的某些英国商船装载的只是例行的护航用品,而不是供登陆作战使用的物资,于是只得卸下重装。某些自由法国商船的船员起初拒绝启航,因为他们已经有几星期没有领到工资了。对其中几艘商船的航速也估计错误,因此护航队不得不减低速度。到了准备工作的后期,他们才知道军舰在这次作战前得再添加燃料,于是它们又不得不先开往弗里敦,再回到达喀尔来,而不是直接驶往该地。
商定的办法是,英国海军应护送戴高乐及其部队到达喀尔,戴高乐及其部队则在登陆后获得立足地以前应服从英国司令官的命令。结果,他们根本就没能获得立足地。戴高乐严格遵守他所同意的协议,事后也没有进行什么反责,从而提高了他的声望。
用最简单的词语来说,作战计划是,先让戴高乐通过和平手段使这个城市投到他这边来。预定将从空中散发传单,戴高乐还将在船上特地装置的电台上对民众发表广播讲话。然后,法国军官将乘飞机在机场降落,手持白旗的使者也将进入港口,设法与总督会谈。结果,传单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便被扫除掉了。戴高乐的广播讲话起先是在居民们一贯不收听广播的时刻播出的,所以听到的人似乎寥寥无几。在机场降落的自由法国军官寡不敌众,被逮捕了。进入达喀尔港的使者最初也险些遭到逮捕,后来遭到对方开枪射击。首席使者达让利厄负伤。防御设施中的大炮也打响了。假定这第一阶段失败了,这次战役的下一阶段便要由英国舰队来一显身手了。不巧,当时的能见度已经很差,舰队被迫驶到离海岸两英里以内的地方,因此遭到了半小时的炮轰,有些舰艇被击中了。根据原先安排的计划,舰队未予还击,虽然它曾同两艘摆开阵势准备发动攻击的潜艇交火。这时已经很清楚,计划的第二阶段也没有成功。英国海军的出现也不足以吓倒法国守军。当天下午,他们开始实行计划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由戴高乐的小部队在达喀尔以东大约十五英里的小港口鲁菲斯克登陆,从那里可以从背后夺取达喀尔。先前成为障碍的雾蒙蒙的天气现在倒对这场战斗很有利了。但是,自由法国部队没有在指定的时间下午5时30分登陆,于是戴高乐便遵照这时英军司令官发来的命令退回到船上。随同远征的有些英国人认为,如果戴高乐这时登陆的话,这一战役本来是会成功的。这必然仍旧是一个看法不同的问题。
9月24日上午,英国舰队炮轰达喀尔约两个半小时之久,下午又轰了一阵。回击的炮火丝毫没有减弱,使军舰遭受一些损坏。25日,又继续炮轰,但是,当英国战舰“决心”号被鱼雷击中腹部以后,伦敦的英国最高统帅部就建议放弃这一军事行动。当地的司令官们也表示同意,于是部队撤退了。它们于9月27…28日抵达弗里敦,没有遭到进一步的损失。
第五编 西欧被占领国家
第一章 比利时
1940年5月,在那些陷于失败和被占领的一片混乱的国家中,比利时的苦境具有某些使人对它感到分外同情的特点。第一,国王对待这场灾难的态度同他的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因此比利时人民极其困惑、满怀怨恨,起初得不到明确的领导,以决定自己的态度。第二,德国人对比利时的政策不同于他们对大多数其他被占领国家的政策,一开始就明目张胆地不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及其各种机构制度。比利时东部某些长期发生争执的地区立即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把比利时的大部分领土同法国北部一部分地区合并在一起,完全置于军事管制之下。第三,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初期,比利时政府曾命令一批青年逃往法国,希望他们可以为建立一支光复比利时的军队奠定基础,由于法国沦陷,他们未能实现这种愿望,反被屈辱地弄回比利时来,听任德国人摆布。这批年轻人以及比利时其他阶层的人士所感到的沉痛的屈辱,在占领初期被德国的宣传机关巧妙地加以利用。大多数比利时人尽管内心绝望,憎恨侵略者,却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德国胜利了,因而必须同敌人合作。只有少数人对继续抗战,对当时只有英国所单独代表的那种力量的最终胜利,仍具有信心。
当利奥波德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于1940年5月27…28日夜间提出比利时军队向德国人无条件投降时,他决定按照自己较早时候发表的声明,本人也跟着投降。另一方面,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转移到法国,在那里用奉到特殊命令撤退的青年组成的比利时新军继续作战。人们当时希望国王也会从国外继续行使国家元首的职责,并指挥这支新军,但是,他顽固地不肯这样做。然而,他的确就宪法地位的问题征询了三个法学权威的意见。他们正式宣布,投降是国王以总司令的身分作出的一项军事行为,不是一项政治行为,并且鉴于国王已经成为战俘,比利时政府根据宪法有权决定国家今后的政策。尽管这个声明主要是为国王的行为剖白,它的措词以及措词的含意最初仍为大多数比利时人所不知道和不理解,他们倾向于毫无保留地赞同国王的行为,而不赞同政府的做法。甚至当政府成员于5月31日在法国里摩日集会,谴责国王的行为时,这种态度仍占上风。法国的崩溃和比利时政府一时陷入的困境(这种处境使他们考虑返回比利时,谴责先前自作主张逃到英国的一个内阁成员雅斯帕尔),的确使人民的情绪变得激烈地反对所有那些指责过国王的行为而自己又没能抵挡住德军的人,那就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政府。他们认为国王坚守了自己的岗位,而所有逃往国外的比利时政府官员都是逃兵。
公众思想的这种混乱状态,肯定使德国人在初期更易于推行他们的分裂计划,但是,在一系列意义重大的事件的帮助下,比利时人民具有的那种突出的独立和批判的精神逐渐重新显露出来了。由于不列颠之战和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出现,英法两国又恢复了不少信心,正如比利时流亡政府通过在伦敦同英法当局的联合,以及通过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提供的专题广播节目能够同国内的比利时人取得联系,又恢复了他们的信心一样。而且,同德国人合作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大批战俘仍然遭到囚禁。粮食供应情况更形恶化。镇压爱国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经付诸实施,德国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