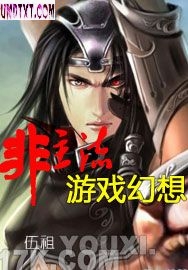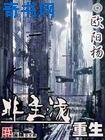非主流清穿(完结)-第4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充当翻译的是传教士,他们自然不会说是他们透露的。胤礽查了一番,在无解的情况下却也生出疑心来了。正好,年羹尧送来的南洋华商里有人懂一点外语,胤礽正好把他们派上了用场。
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善良,同时也是智慧的,在跟着朝廷混与跟着夷人混这道选择题上,坚定地选择了跟着朝廷走。无论是从名誉还是从利益上来看,朝廷都是大靠山不是?大中华的天生优越感,此时还没有被消磨去多少,选谁,结果不言而喻。
摇身一变,商人也加了层官身,派去了理藩院帮忙。一下子得了个顶戴,这更让南洋商人觉得风光,认为跟着朝廷混比较有前途。有了他们的加入,涉外问题就产生了极大的变数。
比如,他们探知,传教士们泄漏了情报给西洋使节。比如,他们对外国比朝廷更要熟悉一点,对于外国的运作机制也懂得更多些。以前还存着点儿外心,现在正式成为公务员了,当然要奋发向上,为国家效力了。
在国人的观念里,无论如何,做了官才是最风光的一件事情。华商也是受此观念熏陶长大的,而今得了机会,自是不遗余力。自家有了出身,再经商就不太体面了,可以使族人、家仆出面,自己官做得越大、越好,经商也就越方便,赚得也就更多。
对外贸易有多大的利润,他们的心里很是清楚,如果让朝廷厌了西洋人,自己等人再立有功勋,或许可以接手这一方面的买卖也未可知,那是多大的利润呢?
卯足了劲儿,三不五时地就说“探听”到了消息,这些消息,有很多是他们在南洋就已经知道了的,只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肯一次全告诉了朝廷而已。以前只是汇报一些南洋的物产等情况,现在才是开始动了真格的了。
随着这个汇报摆上了案头,胤礽的脾气也越来越坏。
拿起一份明显是请了枪手代笔写的折子,上面道,跟朝廷宣战的其实是一伙子商人,荷兰政府给了商人授权,允许他们如何如何。
再拿起另一份也是请的师爷主笔的折子,上面道,传教士里头很有几只不是好鸟,他们辜负朝廷的信任,否则,言语不通,西洋使节何以知道京中如何称呼他们?哦,对了,听说当年跟俄国人谈判,传教士也从中作梗,因为国人不通外语,他们从中偏袒俄国人,否则,咱们不用让出许多土地来的。这一份折子比较敬业,老实说了,跟西洋人打交道,千万别提什么君子风度,你风度了,就要吃亏,他们还以为你好欺负。(言下之意,讨价还价最实在了,当然,我们是商人,很在行,皇帝可以交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比较想走官路的商人上书)
信本国人还是信外国人?这个选择题并不困难,然而满族政权的性质又让胤礽对所谓民人持保留意见,相反,他与传教士的接触更多些,这些传教士至少表面上给人的感觉很亲切。
摸摸下巴,第二件折子里说的又是如此的合情合理——国人没几个懂外语的,有谁能够与西洋使节自由交流呢?答案昭然若揭。
一种被背叛的感觉油然而生!那一点国土,呃,说实在话,他不是特别在乎的;与西洋人贸易的些许利润,也是可以让步一二的。但是事情的性质实在是过于恶劣了!
胤礽沉着脸下令:“所有传教士,不得擅自走动。”一面在心里想:这些黄毛究竟知道多少国家秘密?这一想不打紧,冷汗就冒了下来,至少,在涉外这一块,即对西洋事务一块,几乎全是交给他们来办的!而就目前来看,传教士们根本没有“向化之心”把他们当成朝廷的臣子。
最后一句话才是要命的!
不能用他们了,但是要填补这个空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为此,胤礽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这次会议是值得记念的。因为这是首次,国家把西洋事务摆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认真对待。
诸王大臣传阅了奏折,个个义愤填赝,耳听得皇帝破口大骂:“自世祖以来,朝廷对传教士信任有加,他们竟然做出这等忘恩负义的事情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虽然清廷对诸如“蛮夷”“胡虏”一类的词汇非常的忌讳,心里颇有些被骂的难堪,但是用这些词汇骂起比他们还蛮夷的西洋人、东洋人之类也是绝对不含糊的。骂得还颇有快感,摇身一变,他们也觉得自己很中华。只是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如今逮到一个,真是骂得口沫横飞犹觉不过瘾。
真是太不容易了,清廷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不幸却一直找不到。什么剃发、什么易服,强迫人家改装束的根本,其实不是自豪而是自卑,他们是向往这种文明的,是向往着被认同的。
只是一开始天下掉下来的馅饼太大,砸昏了头,没有处理好开端,骑虎难下,才不得不走下去的。如果真是自豪得不得了,又何必处处仿效被占领者?旗人如今也是以读书为荣,也是爱吟风弄月的,也是读着圣贤书的。
一群“异族”,在紫禁城里骂“蛮夷”,这场景,真是太喜感了!
——————————————————————————————————————————
“这样?”淑嘉惊异地看着胤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再次见证了本朝早期对外关系之并不保守的一面。在对外关系的问题上,这个国家居然是越来越闭塞的,并不是后来者比先人的眼界更开阔。这其实是与国力有关的,一个国家,越是强大、自信,就越是开放,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现在,胤礽居然提出了在理藩院下专设一司,以应对西洋诸国——用本国人做翻译,掌管一应事务,还要培养外语人材?
你干脆设一外交部算了。
这是不可能的!
天朝就没有把西洋诸国当成平等的对手,现在能在理藩院给他们一个位置,用来招呼你们的,至少正眼看你们了,对吧?
这样也好,至少是开始正面接触了。
看着惊讶的表情,胤礽自己的心里也不平静。他也是头一回这样正眼看待一个国家,他的命好,没遇到过什么敌对“国家”,顶多一个俄国,也被打老实了,准部就没有被当成一个正式的国家,而是归入蒙古一部分而已。
现在突然冒出了一大堆的“国家”来,还个个摆出平等的姿态来,他还摸不着人家的边儿,其中之一的荷兰还打败了他的水师,令国人颇有束手无策之感。
冲击不可谓不大矣!
同时,胤礽还隐隐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一条路,一条通往真正的满汉一体,或者说成为真正天下共主、让所有人真心爱戴他的路。
如果他把这种想法告诉淑嘉,淑嘉一定会反应过来:矛盾定律。
根据一个大胡子老爷爷的理论,矛盾也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如果有一个新的更严重的矛盾出现,它就能压制住旧有矛盾。
不过现在,胤礽还没有理清思路,所以他也没有说出来。转而说起了另一件让他老婆跺脚的事情:“乌云珠的婚事,该定下来了。”
淑嘉果然更关心自己的儿女:“怎么说?你……还是想叫她远嫁?”脸上不由现出焦急的神色来。
胤礽显然是打了许久的腹稿,此时说起来也是有条有理:“什么是近,什么又是远呢?成衮扎布是个好孩子,父母为子女,当计其长远。要想女儿过得好,她的额驸就得是个争气的,夫家就得是有规矩的。这些孩子里头,没几个及得上成衮扎布的,六额驸的为人你也是知道的,他们家不会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淑嘉的面色不大好,如果说近亲结婚的阴影已经被几个事例打散了不少的话,那么,把她娇养了十几二十年的女儿放到一个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去,就成了她的心病。
胤礽已经摆出了他的第二点理由来了:“我知道你舍不得她,我也舍不得。她的姐妹们既能出嫁外藩,她也就能。”
淑嘉张了张嘴巴,终于道:“我就是舍不得,统共这么一个女儿,还要远嫁,一年见不着几回倒也罢了,谁家女儿也没有常往娘家跑的,只是……这么远,她要真有个什么事儿,我们够都够不着,你怎么忍心?”摆明了,我就是偏心!
胤礽只得摆出了杀手锏:“我们统共就这一个女儿,你知道她,我难道就不知道了?看她的脾气,是个心性高的。便是在京中,哪怕她是固伦公主,无人敢得罪她,只怕她也不快活。”
这话说得淑嘉一怔,猛然想到,她教起女儿来,却是真的没有只局限于把人往“小女儿”上头教。能让孩子受到更好熏陶,谁愿意让她目光短浅?女儿生来这就是在这权利圈里打滚的,没有一点政治见识是行不通的。存了这样的念头,她并不拘着女儿只学些女工针线、宫斗技巧。兼之近年淑嘉自己也参与了一些朝政,而乌云珠作为所有孩子里与母亲接触最多的人,多少受了一些影响。
说心性高是假的,心气大、眼界宽是真的,那是时不时就会带出来的习惯,困在深宅大院里,胸无大志的种田流穿越者都会偶尔郁闷上那么一两下,何况是固伦公主?
“下嫁外藩的公主,你还不知道么?”胤礽越说越顺,“除开像端静(康熙三公主)那样的,哪一个不过得神采飞扬?她们能够管着旗地事务,能四处散心,不比在京中强么?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她能飞,我就给她一片天地,不好么?”
这是一个父亲的真心话,老婆把孩子教得好也有让他发愁的地方——教得太好了,总觉得不能埋没了她。
下面才是利益角度看问题,外藩公主的权势不小,还是有中央控制外藩的心思在里面的。如果公主只是做深宅妇人,那么这就是个纯“和亲”,本质上是个白痴的举动。如果公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旗地,那才是与中央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才是让她下嫁的本意。对于中央来说,和亲可光不是为了打感情牌。
“他父亲策棱就是个忠心的人,成衮扎布本人也是不错,又不用担心他像噶尔臧一样倒三不着两,这个女婿,我择得很差么?”
淑嘉呆住了,她还真没想过女儿的生存空间或者说“政治抱负”的问题。
如果她在京里,就得遵守更多的清规戒律,而京中的环境,大概会把她磨成个普通妇人吧?想到女儿整日里要想着家长里短,给这家的礼薄了,要再添个宝石盆景儿;那一家里老太太做寿,要准备应景的礼物……哦,婆婆那里的丫头要打点,看住了丈夫不能让他纳小,小姑子有事相求得给她个答复……天天忙得像只没头苍蝇,眼界就那么大一点儿,当只井底之蛙。
不、能、接、受!
女儿可以学会处理这些事情,但是要是放任她的生活里只有这些事情,淑嘉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至少,她是知道的,她当初陷在这些个鸡毛蒜皮里头的时候,绝不是心甘情愿的。直到现在,她老人家最大的愿望就是——不用再管这些乱七八糟!
而外藩的风气比较开放,同时,固伦公主的身份在外藩是极金贵的,清室公主在外藩又有从政的传统,乌云珠可以有更广阔的天地。同时,这片天地又不至于大得让她处理不过来,并且,在政治上的权威,很多时候可以起到稳定家庭的作用——丈夫会打心眼儿里重视她的意见而不是碍于身份必须听她说话。
想明了此节,淑嘉的脸色好了不少:“还是舍不得啊!你什么时候下旨?”
成了!胤礽放下心头一块大石,淑嘉的想法没错,一个女人,承担起越多的责任,她的意见就越重要。对于胤礽来说,淑嘉为他处理了几乎所有的家事,还在必要的时候帮忙他处理政事,老婆的意见是不能不考虑的。如果淑嘉硬要反对,胤礽少不得再多多周旋。
“女儿的仪仗、朝服等都要新制,办好了这些,先册封,再指婚。指过婚,又要督造公主府——她每年都会来京里居住的——再放定、成婚。我明儿就叫钦天监择卜吉日去。”
“仪仗?要准备多久?她的嫁妆……”无奈之下接受了这个选择,淑嘉便关心起女儿的福利来了。
“我还会亏待了女儿不成?呃,女儿那里,还是要你与她说明白些儿,甭觉着远嫁就是吃了。”
乌云珠与所有未婚姑娘一样,听到关于自己终身大事的消息都是要地羞涩一下的。册封的事情她不在乎,怎么也跑不了一个固伦公主,指婚就值得关注了。下嫁外藩,乍一听来是有些打击,却不是不能接受的,清室公主的命运,大半都是如此。
淑嘉看她的表情,心道,好像没有受太大的打击。慢慢地把胤礽的意思用另一套话说了出来:“我不欲你远嫁的,却又想你过得好。你阿玛择的成衮扎布,不为远近,只为你能过得好。若是京中有一个比他更好的,我也可争上一争。却是再也找不出来了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