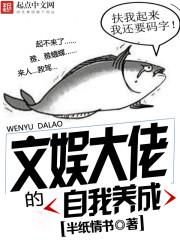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是我一下子就发现,波格丹诺夫具有狂躁性忧郁症。他是沉静的、宽厚的人,是对理想爱得发狂的人。 在布尔什维克时期他很高尚地控制着自己。 他是老布尔什维克,编了许多集子,还和列宁一起办杂志。 在布尔什维克胜利时期,那些丑陋的方面使他嫌弃,他认定那不是真正的革命,只占有有限的地位。但在沃洛格达流放时期则是另一种情况,我的流放时的一位同志,我听说由于残忍和嗜血成性而在革命紧张时刻成了北
147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331
方政治委员。 我和他几乎没有交往。 他却产生具有美德的宗教狂热者的自我印象,革命的美德有时使他产生可怕的结果。在我流放期间,列宁还没选择那种统一的花岗岩般的思想体系和准备专政所必须的少数人的铁的纪律。 我的流放时的同志,后来成了布尔什维克的奥托。 赫利斯恰诺维奇。 奥谢穆(不久做了苏联驻巴黎的领事)
给人以十分善良的印象。他一点也不凶残,他喜欢啤酒和晚会,对理性的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在沃洛格达我交往较近的只是流放犯中不多的一些人,这些人组成了“贵族派”
,其中有我原在基辅联系的一些人,特别是B。 。 。此外,我还到省地方自治局的管理代表那里去,d在那里有时遇见比较自由主义的官员,遇见地方剧院的演员。我和被流放的B。 。特别友好,他是很有智力的人,是真正的哲学家。 当我动身前往沃洛格达时,心情十分忧郁、沮丧,尽管已是初春,但天气不好,谁也不知道流放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沃洛格达我的这种忧郁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我和一小部分流放者被留在沃洛格达,大部分流放者则被分到沃洛格达省的许多县城,当时的沃洛格达省的总督是我的一个远亲(我称他为叔叔)
M。 。伯爵。 这同样给我提供了某B种特权地位。 过了一个半月,我收到一份公文,告知可以选择俄国南方的任何没有大学的城市度过以后的流放日子。 我很奇怪,当即决定拒绝,继续留在沃洛格达。 原来是,我的姑夫兼教父,陛下的侍从将军,H。 。 洛普辛—杰米多夫特B级公爵对弗拉吉米尔。 阿利克赛洛维奇大公说,他的夫人的侄儿和他的教子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他很生气,要求将侄儿转移到南方去。 弗。 阿。 大公立即通知内务部的同事和宪
148
431自我认识
兵首脑,于是便吩咐我转到南方。 我认为这从道德上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我并不觉得沃洛格达的生活有什么可怕,我甚至喜欢这个北方的城市,这里的生活是自由的,对我来说是新鲜的,因为我不了解大俄罗斯的北方。 在夏天,我愉快地骑自行车在沃洛格达周围地区旅行,主要访问古老的修道院的遗迹,在沃洛格达我自己感到十分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基辅还要自由,警察一点也不麻烦我,我能从对流放犯的专政中夺回自己的独立性。
G G G我的第一本书《社会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出版时,我正在流放,这本书引起了不少争论,也包括在沃洛格达流放犯中的争论。 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本书,它一下子给我提高了知名度,虽然大部分评论文章是攻击我的。 我记得有一篇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误刊在我的书上。 马克思主义团体也讨论这本书,我成了被波格丹诺夫称为“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唯心主义”的流派的主要表达者之一。 当我接到这本书时,自己已经对它不满意了。 我在进一步走向唯心主义,走向形而上学,走向精神问题。 在流放期满前不久特别决定要到彼得堡去,因为我已经有了结果。 在我的生活中经常存在着与不同集团交叉联系所形成的对比。我在堂弟C。B。K。大公家吃午饭,一起的还有内务部的一个司长特列波夫,晚上遇见了。 司徒卢威和M。 图根-巴拉诺夫斯基。 司徒卢威B对我很为赞赏,表示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 他决定给我的书写序。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中,我比司徒卢威持较左的观点。
149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531
当我第一次拜访司徒卢威的时候,在他那里作客的有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 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布尔什维克,《通报》的编辑,很多反宗教宣传小册子的作者。 当我见到斯科沃切夫-斯切帕诺夫时,他和司徒卢威一起都持较右的观点,而我则比较左。 但是,当他成了《通报》的编辑以后,我一直没和他见过面。 在这次彼得堡会见之后,我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建立起著作上的联系,完全更加倾向于唯心主义。我和C。 布尔加科夫发生了更紧密的联系,我在基辅时就认识他,当时他是工业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是我们一同流放者之一。 司徒卢威比我一直更加是个政治家。 他由社会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我甚至这样想:他任何时候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热情,尽管他是社会民主党建党纲领的作者。他更接近于伯恩施坦(他的表明德国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书引起轰动)的观点。 我在很多地方同意伯恩施坦的批判,但我的热情是另一类型的。 我向往新的世界,但不是在辩证地经过革命阶段的必然社会进程的基础上加以论证,而是在人的自由和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上加以论证。 我的革命性带有较多伦理性,而较少社会性,我的观点正处在进化过程中。与我的书一起,我的两篇文章更增加了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甚至一般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圈子里不好的名声。 这就是已经提到过的《为唯心主义而斗争》和《从哲学唯心主义观点看伦理学问题》。这两篇文章写于沃洛格达,发表在《唯心主义问题》文集上,很是轰动。 收入文集的文章作者是一些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新的唯心主义者,还有学院哲学的某些自由主义代表:。 诺夫郭洛得切夫、特鲁别茨科伊兄弟,我B
150
631自我认识
的文章拟定了我的“人格主义”。
文章不仅表现了我向康德的接近,而且渗入尼采的主旋律。 在文章的序文中我引用了普希金的诗:“你就是主宰:你要掌握自己的方向。 走上自由的智慧指引的自由大道”
①。由于这些文章,C。 特鲁别茨科伊告诉我说:如果知道你在那里发表了那种尼采主义的文章,就不能同意再参加他们的文集。 所有这些都不能使我受到我的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的欢迎。 尽管我在政治上变化很少,仍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我费了很多精力与这个环境进行斗争,批判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世界观和传统的精神结构。 我认为这是为了使长期忧郁的精神获得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但是,这些妨碍了我的真正的创造性,有时扭曲了我的思想,使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流放的后期和流放以后我进入比较不好的时期,下降的时期而不是上升的时期。 这段时间里我很少写作,尽管我写作很容易,属于有效率的作家。 这个时期里,比起积极的创造性来,批判占了首位。 我力图使生活富有诗意,希望美,但生活中占上风的却是单调和畸形。 我感到我和原来联系的圈子的断裂在不断加强,而任何新的联系尚未获得。 这是我的空虚时期,这个时期里和人们的交往对我内在的生活没有任何兴趣,在思想领域没有任何大的收获。 我任何时候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但是,我也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我永远是矛盾的。 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对我是敌视的,虽然我还保持了某些个人联系。 那些称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团体与我格
①普希金:《给诗人》(1830年)。——译注
151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731
格不入,俄国自由主义类型的社会活动家我也很不喜欢。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起任何作用,甚至也不想起作用,社会民主党人由于我的唯心主义和思想探索而敌视我,并常在刊物上辱骂我。 自由党人由于某种原因而嘲笑和讥讽我。 社会民主党人的敌视和不容异见的态度是由于他们是信教的教条主义者,并想以这种资格来烧死“异教徒”。自由党人所以采取嘲笑和讥讽的态度则由于他们是怀疑主义者,他们认为精神的探索虽然无害,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参加解放运动的渴望使我接近了“解放社”。我与“解放社”的创始人有着思想的和个人的联系。 我参加了1903年和1904年在国外的两次会议,在会上成立了“解放社”。会议在靠近列普斯基瀑布的德国的黑林和瑞士的沙夫豪森召开。 美丽的自然景色比会议内容更加使我喜欢,在那里我首次遇见自由派的平民团体,其中的许多人后来作为国家杜马中的反对党而起作用,并在1917年成为临时政府的组成部分,这些人中有很值得尊敬的人,但是这个集团与我是格格不入的。“解放社”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解放社”
中分出一些分子,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主要基础,我认为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我不参加立宪民主党,我仍然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 我参加开始设在基辅,后来设在彼得堡的“解放社”
委员会,但是,根据我的情况,我没有起特别积极的作用,并且感到自由派——立宪民主党的环境的可怕的异己性,比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环境更大的异己性。 有时,我代表“解放社”和社会民主党人会谈,比如,和当时是孟什维克,后来成了苏维
152
831自我认识
埃大员——人民委员的X。会谈,和犹太崩得的①代表马尔托夫会谈。 在当时俄罗斯到处举办的“解放”宴会②上,我的感觉很不好,我是比较消极的。 我自己感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还相对地较好些,但是,他们不能原谅我探索精神和超验世界的“反动”。批判的唯心主义已经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发现司徒卢威转向精神的时候,我与他之间有了接近的因素,但是,当他坚决把政治置于精神问题之上而且在政治上偏向右倾时,我又开始和他疏远了。我感到和布尔加科夫更接近,我们的道路在外部表现上是相互交织的。 当时布尔加科夫已经坚决转向基督教和东正教,我则还站在自由的精神方面的立场上,我和布尔加科夫在基辅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对我是有意义的。
G在彼得堡的第一个时期我参加了社会集会和社会的抗议游行。 我总是感觉不好,我的嗓子不能发出适应社会运动性质的声音。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左派知识分子的广大集团是否定和敌视首次提出精神文化问题并且在世界观上追随旧的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运动的。 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选择新的意识被当作政治上的反动来对待,但是,这种评价是
①崩对: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在一切问题上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 ——译注②宴会运动:1904年11月“解放社”
在俄国许多城市组织的地方自治派自由主义分子运动。 在司法改革四十周年的宴会上,提出政治改革请愿书。 ——译注
153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931
歧义的和轻率的,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点。 中断了和知识分子实证主义的联系的、以《生活问题》杂志为基础的“唯心主义”团体,积极参加了“解放社”
,在“解放社”彼得堡委员会里也可以发现被指责为反动唯心主义者的那类知识分子。 这样,新的思想运动在左派“社会舆论”中争得了承认。因著作被抨击为“反动”分子,但同时又在解放的团体中讨论解放的纲领,这是令人难堪的。1905年以后的这一代已经不了解这种类型的冲突。 很多人已经获得了精神文化,知识分子的墨守成规和它的政治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动摇了,并表现为陈旧的东西。更广范围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了意识危机,这特别表现为审美意识的尖锐化和新的艺术形式的采纳。 我痛苦地忍受了1905年的小型革命。 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我支持革命,但是,它所具有的特征和它的道德后果引起我的厌恶,并使我产生精神上的反动。 在这之后,革命即使没有完全扼杀但也实质上结束了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英雄时期。 革命知识分子的传统世界观以及意识上的禁欲主义的狭隘性,道德上的过分严肃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宗教态度都在衰落,在某些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集团中由于对革命的失望而开始了真正的道德瓦解。 让我完全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