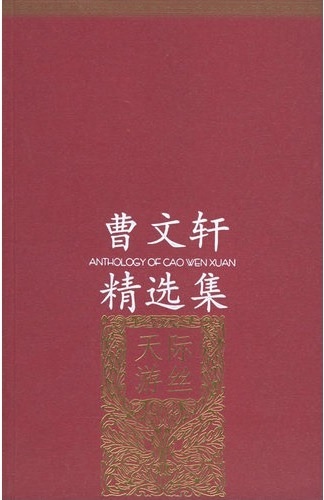曹文轩精选集-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朦胧里,从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鸡鸣声。我用力睁眼一看,屋里已白白的。我不能再睡了,便爬出被窝,穿好衣服。然后就可怜巴巴地袖着手,像一个饿瘪了肚皮、无家可归的小乞丐那样蜷缩在墙角里。其实离天亮还早着呢,屋里白白的,是因为月光变得皎洁了。我等呀等呀,总等不到天亮,天反而越来越黑了。后来就又睡着了。等再醒来时,真的天亮了。
惊乍、出汗、受风,我病了。下午跟她往回走时,脑袋昏昏沉沉。走了三分之二的路,她见我晃晃悠悠地走不动,又见我的脸红得火烧一样,连忙伸过手来摸我的额头,一摸吓了她一跳,没道理地四下里张望,也不知寻找什么。后来,她蹲了下来。
我站着不动。
她就将我拉到她的背上,将我背了起来。
我用胳膊勾着她的脖子,把头埋在她松软的、微带汗香的头发里。
四
来了一个男人,是找她的。
在我以后漫长的生活中,我见到过许多漂亮的男人,但没有一个能与他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气韵、神气相媲美。他不属于剽悍雄健的那种人,也无矜持、傲慢、目空一切的绅士遗风。他是属于清雅、潇洒那一类,但又脱尽了白面书生的文弱和油头粉面的恶俗。他在这个世界上只一个。
他会吹笛子。
他来,好像就是专门为她吹笛子来的。他到达不久,我就能听到笛子声。而笛子声停了不久,我就又很快听到他离去的足音。他总是黄昏时到。校园前面,是一片足有几十公顷的荷田。他从不进她的宿舍,而是邀她到荷田边上。我曾几次借着月光看到他们的姿态。他倚着一棵大树,她静静地坐在田边,并不看他,而是托着下巴,朝荷田的远方望。荷叶田田,被风翻动着。远处仿佛有一个美丽的小精灵在飘游,在召唤着她。
我至今还觉得,世界上最好听的乐器是笛子。
他的笛子吹得很好。声音一会儿像蓝晶晶的冰雹在蓝晶晶的冰上跳着,一会儿像一束细长的金色的光线,划过荷田的上空,一会儿又像有人往清潭里丢了几枚石子。笛声一响,似乎万籁俱寂。那高阔神秘的夜空下,也只有这一缕笛声了。
销魂的笛声,常常把我的魂儿也勾走了。它使我的童年变得异常纯美,充满幻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的心起了什么俗念,当我的灵魂染上什么污渍,耳畔总能响起那清澈如大谷深潭的笛声。
有时,我在心里会对那个男人生出一丝莫名的嫉恨……
五
我长到十岁。
十岁是一个荒唐的年龄。
我变得非常可笑,竟那么乐于在她面前表现自己。这一年里,我所做的蠢事,比我这一辈子所做的蠢事还要多。
我是男孩子,但我天性怯懦,毫无男子气概。我容易红脸,羞于见人。我还害怕夜晚,夜里不敢起床撒尿,憋急了就闭着眼睛喊母亲点灯。而常常是还未把母亲从酣睡中唤醒,那尿就宛如一线瀑布,急急地冲了出来。我家门口的树枝上老挂着被子,上面有许多奇形怪状的淡黄色印痕,很像抽象派绘画。那是我的杰作。自从她来到父亲的学校,这种事就少多了,只是偶尔为之。那种时候,我总是央求母亲别在门前搞我的画展。我不想让她看见。到了九岁,这种羞事就彻底杜绝了。但胆子依然小如绿豆。而到了十岁,忽然地,我就胆大包天了。漆黑的夜,风阴森森地呼号,荒野一派神出鬼没的恶样,我竟敢独自一人到路口去迎接辅导其他孩子学习的她。
“你胆真大。”她说。
“我才不怕呢!我什么也不怕,我小时候胆就很大。”我感到非常得意,并不知害臊地撒谎吹牛。而黑暗里,我的腿却像两根秋风中的芦苇在使劲摇颤。
在我童年的历史里,最荣耀的一页莫过于那次骑牛——
村里有条蛮牛,比我在《海牛》中写到的那头还要雄壮许多,还多一层阴恶。如今电视上经常播放西班牙人斗牛的场景。那场景令人魂飞魄散。每当我看见那些勾首颠臀、扭曲身体、像抽风一样狂奔乱跳的凶顽刁钻的牛时,我就会自然想到那头畜生。它曾撞倒一座泥墙小屋,差点儿压死小屋的主人。一次它野性发作,竟把牛桩从地里拔起,一路旋风,跑出几十里地去,一路撞伤三人,其中一个差点儿没被它用犄角挑死。至今,它的背上,还从未有过一个人敢问津。
那天,它的主人把它拴在学校门前的树上让它吃草。
小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都远远地围观着。
不知是谁说了一声:“谁敢骑上去?”于是,就有很多人问:“谁敢骑上去?”
我总觉得那些男老师有点儿嫉妒我,总有让我在她面前出出洋相的念头,尽管我才十岁。现在我才明白,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反正都是男的。女老师们也是这样,有一个女老师,简直完全忘记了我的年龄,死劲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前面,把我的手举起,大声地向众人宣布,说我就敢骑。
我赶紧埋下屁股。
那些男老师和孩子们就都嗷嗷地叫起来。
这时我一眼瞥见了她——她站在那里脸色微微发红地微笑着。
那个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嫉妒我,都想让我丢丑。当他们还要兴致勃勃地把玩笑往大里开时,我冲出了人群,朝蛮牛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我感到我的身后,死一般寂静,他们好像全都中风了。当我离蛮牛还剩几步远时,那个女老师首先惊慌地叫起来:
“回来!”
“回来!”他们一片恐惧。
我听见了她几乎绝望一般的喊叫:“别——去——!”
而我置若罔闻,继续朝它走去。
蛮牛抬起了它硕大无朋的脑袋,我瞧见了那对琥珀色的阴沉沉的眼睛,听见了它的粗浊的喘息声。
身后又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连连加速,猛地蹿上去,伸手抓住了它背上的鬃毛,然后纵身一跃,竟一下骑到了它的背上——这大概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英勇了。
那牛很怪,几乎没有动静。它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一个十岁的小屁孩子朝它背上爬。当它反应过来确实有人造次时,我已稳稳地骑在它的背上了。
在我向众人俯瞰的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并且非常伟大。
蛮牛立即狂颠起来。我紧紧揪住它的鬃毛。我觉得我的肠子要被颠断了,骨头也要散架了。热血直冲脑门,我闭起眼睛,觉得眼珠子就要一粒一粒地爆裂了。蛮牛挣脱了绳子,驮着我朝前奔突,我的屁股不断地被它颠得离开了它的脊背。
朝田野上冲去。
朝树林里冲去。
朝打谷场上冲去。
现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就只剩下了我与这头牛。而这头牛却横下心来要置我于死地。
我不敢想像我的结局。
日后,我无法理解自己在那样的时刻为什么竟然会想到在我家屋后的竹林里悬挂着的一个圆溜溜的黄雀窝、一条在月光下突然跃到空中的白跳鱼……
事情有点儿出人预料,我竟然获得了一个很体面的下场:在蛮牛冲向河边忽然发现自己没了出路而只好急拐弯时,我被甩到了水中。
蛮牛朝田野上跑了,人们都朝我跑过来。
我从水里爬上岸,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地站在河堤上。
她拨开人群,扑到我跟前。她的眼睛里蒙着泪幕。她的双手抓住了我的手。我感觉她的手冰凉,浑身在发抖。
夜里,我的腰疼痛难熬,把一块枕巾咬烂了……
六
我十一岁那年,因为一件突然发生的事件,我们变得有点儿不大自然起来。
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我和一群孩子在草地上打仗,我的“金箍棒”被打折了,成了赤手空拳者。这时,我想起在她的门后有一根晾衣服的竹竿,便撒腿朝她的房间跑去。
她房间的门关着,我冒冒失失,猛地一推,门开了(事后我想,她本来是把门插了的,但没有插牢)。眼前的情景立即使我变成了一块传说中因偶然回头一望而顿时变成的石头!
我似乎听见她“呀”地惊叫了一声,又似乎看见她用双臂护住胸前,目光里充满惊慌和羞怯。
“快出去!”她跺着脚,水从洗澡盆里溅出,溅了一地。
我似乎还有一点印象:她当时的样子有点儿像我小时候跟母亲发脾气。
而我已经完全吓傻了,竟然站在门口动也不动。
“快出去呀!”她使劲地连连跺脚,并把身体转过去,“快出去……”
我这才猛然醒来,像一名被追赶的逃犯,转身就跑。我也不知跑出了多远,最后跑到了一片寂无一人的草地上,浑身发软地扑到上面,久久地把脸埋在茂密、湿润的草丛里。
其实,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只觉得屋里闪着一团亮光。这种经验,在后来的生活中又多次被唤醒过,那是在我有一次走进一座幽静的大山,看见绿阴深处倾泻下来一道雪白的瀑布的时候;那是在我有一次去草原,看见一个年轻姑娘把一桶鲜洁的牛奶往一只更大的木桶里倾倒的时候;那是在我有一次去北方一座城市,看见一座少女形象的晶莹剔透的冰雕的时候……
天黑了,母亲在呼唤我回家。
我坐在荒野里,没有回应母亲。
一直捱到月亮爬上田野尽头的树梢,我才回家。
我不敢看白栅栏那边微黄的灯光。第二天上课,我一直不敢抬头看她。那天,她的课讲得似乎也有点儿乱,声音有点儿过于平静。在以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一见了她,总是低头贴着墙根溜,没有必要地把一块老大的空地让给她。我们的目光偶尔相遇时,她虽然还像以往一样微笑着,但脸上分明淡淡泛起羞涩的红晕。许多次,她力图要摆出她是我的老师的样子来,并且想使我相信,我在她心目中纯粹是一个孩子,并且永远是一个孩子。
打破这种僵局,是在一个月以后。
那个吹笛人有一个星期不来了。我看出,她的眼睛里含着一种焦急,一种惶然和担忧。一天下午,她把我叫到她的宿舍,一把抓住我的手:“替我送封信给他,能吗?”
我点点头。
我拿了信就跑。我现在太乐意为她做事情了。我觉得现在为她做点儿事,绝对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我并为她给予我的信任而深深感动。我几乎是一口气跑完十里路,来到了镇上学校——他就在那里任教。然而,当我跨进校门,想到马上就要把她的信交到他手上时,刚才的兴致勃勃顿时消失了。
我没有把她的信送到——他已在三天前调离那所学校,回三百里外东海边他的老家去了。
我痛恨起他来,并在心里狠狠地骂他。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却又觉得自己走得很轻松,双脚极有弹性,仿佛踩在了云彩上。我好几次从高高的大堤上冲下去,冲到大河边上玩水漂漂。记得有一个水漂,在水面上像一只调皮的小鸟欢跳了十八次……
七
后来,我从父母亲的谈话中得知:那个吹笛人要带她远走,而她却希望他调到我父亲的学校,他不干,丢下她,坚决地回到了他的母亲身边去了。
她还是认真地给我们讲课,微笑着,把日子一寸一寸地打发走。我十二岁那年,当栀子花开了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由于她精心的教育,全部考上了初中。当我们簇拥着她,把喜讯告诉她时,她转身哭了。
发榜后的第三天,我从外面玩儿回来,母亲对我说:“她要走了。”
“上哪儿?”
“海边。”
“什么时候走?”
“就在这两天。”
我走了出去。
晚上,我收拾着一个行李。母亲问:“干什么?”
“二舅下芦荡割芦苇,我帮他看船去。”
“你不是已对二舅说不去了吗?”
“我去。”
“你这孩子,也没有个准主意。”
第二天一早,我夹着小小的行李卷,望着白栅栏那边的屋子发一阵愣,跑到了二舅家。
当天,我们就开船,向二百里外的芦荡去了。
日夜兼程,两日后,我们的船已抵达芦荡。
密密匝匝的芦苇,像满地长出的一根根金条,一望无际。这里的水绿得发蓝,天空格外高阔。水泊里,我不时看到一种又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鸟。有的叫得非常好听。二舅去看芦苇,还发现一窝小鸟,给我带了回来。那鸟是绿色的,十分可爱。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愉快地给二舅看船,帮他捆芦苇。
我在芦荡很有兴致地生活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却向二舅提出:“我要回家了。”
“这怎么行?我的芦苇才割了三分之一呀。”
“不,我要回家。”
“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