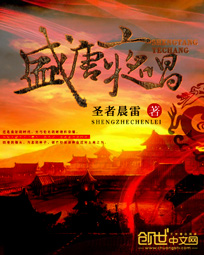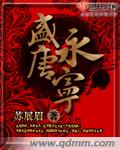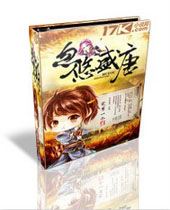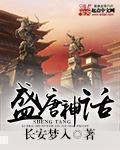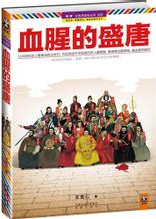盛唐夜唱-第1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恰好这时,叶畅回过脸来,两人目光相对,娓娘不由自主避开目光。这豪气不逊于须眉的蛮人女子,竟然觉得了畏惧。
叶畅并没有动手,但是那个得罪他的泼皮死了,而且还是死在他惯熟的乡亲手中。
叶畅甚至没有说要那些村民击杀二蛮,他只是说与二蛮不共存,于是乡民们几乎不约而同,选择害了二蛮性命,以讨叶畅的欢喜。
这种事情,让娓娘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
“现在,你还敢让我随你去越析诏么?”她正琢磨着是哪儿不劲,突然间,便听得叶畅低声问道。
“我……”
娓娘原本是想说“我有什么不敢”的,但旋即,她明白自己方才在担忧什么了。
她真的不敢。
叶畅到了越析诏,如同帮助这些灾民一般,建立制度,培养习惯,帮助越析诏壮大起来,甚至打败南诏,取而代之统一六诏及乌蛮白蛮诸部——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叶畅的声望会高到什么程度?
叶畅会不会利用这个声望,将她,还有她的家人,也如同二蛮一般处置?
想一想这样的后果,娓娘一时间就无法回应叶畅的问题。
“这几日里,你盯着我行事,也应该有所获吧,回去之后,凭着这些,让你部族离南诏远些,依然有复兴可能。”叶畅从她目光中看到了一丝惶惑,心中暗暗高兴,于是又道:“至于短时间里想要打败南诏,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须待天时。”
“什么……天时?”
“南诏吞并六诏,成为大唐之侧一强国,而剑南节度使节制南诏,仍以当初小部落视之,必引发事端。地方官得力,还可安抚,地方官若不得力,只待小挫土蕃,大唐与南诏之间必会反目。那个时候,便是你的时机了。”
这一次,娓娘没有再说什么。
她看着叶畅说完这番话,便又从木筏跳回岸上,又看着那些村民欢呼着迎向叶畅,将叶畅簇拥而回。看着叶畅吩咐村民们依先前分组行事,又看着叶畅自己回到宿处连头都不回一下。
“郡主?”对她最为忠心的蛮人大汉见她还留在木筏上发愣,开口唤了一声。
“啊……你觉得,叶郎君这个人如何?”娓娘问道。
“很厉害……还有,唐人原本就奸猾,他绝对是唐人中最奸猾者。”那蛮人大汉有些吞吞吐吐。
“是,他是那种把人卖了,还能让人替他数铜钱的人……若真将他带回咱们越析诏,只怕是引狼入室,比起南诏还要可怕。”
喃喃说到这里,娓娘决心已定了。
在决定放弃将叶畅带回的一刹那,她甚至动过念头,是不是要杀了叶畅以绝后患。
不过看到村民们对待叶畅的态度,她又改了主意。
现在叶畅在这些难民当中声望甚高,叶畅几乎就是他们的性命,自己这十来个人动起手来,就算能杀了叶畅,只怕也挡不住村民的报复。
想想这两三日的经过,娓娘也觉得荒唐,叶畅最初是利用他们蛮人来压制这些村民,但现在反过来,又利用村民来压制他们这些蛮人——这一切,难道都在叶畅的料想之中?
她在那里瞎琢磨,叶畅却没有时间想这些,回到宿处,他第一件事情,仍然是去查看那些病人。
毕竟顶着曾给药王当丹童的神话,叶畅颇花了一番时间学习医术,老师自然是药王观的骆守一。别的不行,结合另一世的医理进行一些基本的判断还是会的,认定几位病号的情形都没有恶化,而且其中两人喝了汤药后还有好转,叶畅算是松了口气。
不过他明白,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灾后有疫,几乎是这个时代的惯例,他能控制住这座小小的山头,却控制不住整个灾区,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受灾的地方不是太大,而此地的官府反应也能够及时了。
前者还可以祈求老天,后者嘛,以到如今仍然没有看到救援者身影来判断,实在没有什么希望。
第127章 乡有贤者佑四邻
偃师县令白铨苦恼地揉着自己的额头,长长叹了口气。
旁边的县丞蒋清也同样叹了口气。
“怕是顶上这冠冕难保了。”白铨又叹道:“偃师乃东都门户之地,据闻圣人又有意驾幸东都,却出了这一摊事……”
“此事如何怪得明府,谁曾料想一场暴雨竟至黄河漫堤?”县丞勉强安慰道:“况且如今算来,就是三个村子受损,不过一百八十户,已经是平日里明府维护河堤之功了。若真要追究,水陆转运使也脱不了身!”
如今水陆转运使仍是韦坚,他正得三郎天子的欢心,便是李林甫都要暂避其锋芒,黄河漫堤乃是天灾,若要顶,也该由这大个头先顶。
白铨却没有那么乐观。
蒋清说这番话自有底气,他的父亲乃是先吏部侍郎蒋钦绪,他自己原本说是要授巩县丞的,但后来不知为何,变成了偃师丞。与白铨在朝中没有后台不同,蒋清父亲当初提拔举荐的人物当中,颇有在朝廷里担任要职的,因此这点事情,他并不怕。
“小况村地势最低,离得漫堤处又最近,此处灾情最重。前来探看时,并未发现一人,全村尽没,只怕无人幸免。”带队的差役指着船前的一片水道:“此村情形最惨。”
“唉……”
白铨又重叹了声,若是避之不及,这座村子怕就是要毁了。
从目前的情形来判断,相当不乐观,另外两座受灾严重的村子,还没有象小况村一般完全淹没,有些人正在屋顶上等待救援。即使如此,那两座村子淹死者已经超过了半数,而且还有数十人生病,甚至隐约有疫疾的苗头。
这才是受灾过去七日,便出此状况,若是扩散,情形不堪设想!
偏偏对这个灾情,白铨无计可施,这是天灾,不是人祸,他能有什么办法!
“咦,那是……木筏?木筏上有人!”
正忧心忡忡之际,突然听得差役叫了起来。
只见绕过一丛树梢,一架木筏出现在他们视野当中,木筏之上是五个百姓,一人撑篙,另外四人则坐在木筏上歇着。除了他们四个人外,木筏上还装着不少东西,有木板,也有萝筐,甚至还有一只小狗,一边摇着尾巴,一边对着这边汪汪叫。
“是相邻处的百姓还是这小况村的?”白铨稍振作精神,带着一丝希翼问道。
差役是常下乡的,眯着眼望了一会儿,然后欢喜地道:“明府,是小况村的,有两个我认识,乃是小况村村老况桧之四子,我们都喊他况四郎的!”
“小况村还有人活着!”这个消息,让白铨紧紧捏了一下拳头:“唤他近前答话,唤他近前来!”
差役大声喊了起来,那边木筏瞧着这边的船,也向这边撑了过来,不一会儿,双方相距便不远。
“明府老爷、县丞老爷在此,况四郎,还不上来见礼!”那差役喝道。
况四郎早看到船上穿着官袍的人,听差役喝斥,当下在木筏上行礼:“某况四,拜见明府、县丞。”
“你是小况村人?”白铨顾不得答礼,急切地问道:“村里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活下来?”
“村里死了两人,其余人等,都安然无恙。”况四郎答道。
“可怜,可怜,只剩余你们两个……”白铨听岔了,但才说到这,旋即意识到不对:“只死了两人?你是说,村里只死了两人?”
“正是,叶郎君及时来示警,故此村里有足够时间撤离,死去的两人,都是不肯离屋的。”
“真是……太好了,太好了!”白铨闻言大喜,在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这是他听得的最好的消息!
其余靠近黄河边上的村子,或多或少都受了灾,好些的没有人员伤亡,只是田地被淹,但是几个灾情严重的,都是伤亡惨重,甚至死伤过半,偏偏这受灾最重的小况村,却只死了两人,而且是两个坚决不肯撤离的老人!
小况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白铨此时心中全是欢喜,一时间忘了问,那边蒋清却还有些怀疑,开口道:“老弱都无恙?灾民都安置于何处?另外,这几日里,都是如何过的?有无疫疾?”
这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白铨连连点头,显然个个问题都是他想知道的。
“好叫两位官人知晓,老弱中原是有六个病了的,不过这两日都渐好了。大伙都安置在北邙岭的一处山包上,这几日,我们靠着撤离时带的粮食支撑,不过现在粮食也已经有些紧了,故此我们来四处搜寻,看看能不能找着些吃的。至于疫疾,绝对没有!”
况四在况老汉五子中是比较伶牙俐齿的,故此回答问题颇有条理,他将蒋清的问题一一应答完毕之后,又涎着脸道:“两位官人在此,想必有赈济的粮食?”
“某已向朝廷请旨开义仓了。”白铨长舒了口气,小况村的情形,竟然比他想得到的最好状况还好,这可是实打实的功劳!原本担心因为漫堤而被追究,现在看来,将功折过是没有问题了,最多也就是被上司训斥罢了。
不过放松之后,他就意识到不对。
小况村的情形这也好得太过份了吧?
走的时候,洪水上涨,他们不但把绝大多数人都撤离了,而且还能携带支撑几天的粮食——仅这一点,就绝不是一般太平百姓能想到的。
至少其余几个村子逃出洪水的灾民,身上就几乎完全没有粮食。
蒋清同样也意识到这一点,低声对白铨道:“这村子里,必有能人。”
“是,乡有贤者,庇护四邻。”白铨点点头:“况四,你们村中,可是有贤达人物带领,才得如此,不知这位贤达,乃是何许人也?”
县令有向朝廷举荐乡野遗贤的义务,小况村这情形,定然是要在偃师名声大噪的,这种情形下,白铨就是想将功劳全按到自己身上也不可能,倒不如自己得育民有方之功,再得一个举贤荐能之功。
“贤达?那是什么?”
况四却是愣了,他便是伶牙俐齿,但见识总是少了,“贤达”是什么东西,他当真不明白。
“就是村里有什么能人,带着你们避开洪水,又做了这么多准备。”那差役倒是明白,喝了一声道。
“我们村哪能有什么贤达,是一位外乡姓叶的郎君!”况四将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乘船经过此地,途中遭遇暴雨,不得不靠岸避雨,然后发觉水将漫堤,便到了我们村子。”
“叶郎君?”
听得不是自己治下之民,白铨就有些失望,不过小况村的情形究竟是什么样,他还是要眼见为实的。因此便让况四带路,回他们的临时避难所去。
然后他就有些后悔了。
这位况四,他能在一群闷葫芦般的乡民中练出这副伶牙俐齿来,靠的便是足够唠叨。一路上,况四没少唠叨这几日的情形,同一件事情,翻来覆去说几遍,还要多角度全方位展示,当时这个人怎么想的,另一个人又是怎么想的,还有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在他的面面俱到中,白铨与蒋清发觉,唯有一人心中怎么想,这位况四是不会去猜的。
那人就是他口中的“叶郎君”。
“你为何不说说当时叶郎君如何想的?”
“哪敢,哪能?”听得这样的问题,况四一脸讶然,似乎觉得这个问题甚为愚蠢:“叶郎君那是何等人物,神仙一般的,他心中所想,某这凡夫愚子哪里猜得到?便是一般的读书人,只怕也猜不出……”
说到这,他看了看白铨与蒋清,明知不该多嘴,结果还是忍不住补充:“我瞧便是明府与县丞两位官人,怕是也猜不出……”
“哈哈……”
白铨与蒋清相视一笑,自然不会与这个愚笨的乡民一般见识。见他二人不生气,况四又开始说了起来,他虽是罗嗦,但从他口中,二人还是渐渐听出叶畅这五日来是如何带领小况村的灾民们战胜水灾的。
“这位叶郎君,当真非同一般。”蒋清对白铨道:“明府,一个外乡人,能让小况村百姓如此折服,而且不只是一人,你瞧,那况四每赞叶郎君,另外几个乡民也都是连连点头!”
“嗯,而且这位叶郎君所谋甚远,一步步安排,都是智珠在握。”白铨也甚为赞赏。
他们二人对叶郎君越来越好奇,不知道是何等人物,才能做到这种程度。
待况四说到叶畅带着他们搭好临时的窝棚遮风避雨时,他们已经到了那座暂时安置的山头之下。白铨手搭凉棚,放眼望去,只见山上缓坡平整处,被开出一块空地,空地上搭起了四排棚子。虽然简陋,但这些棚子布局却是齐整,一看上去就让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