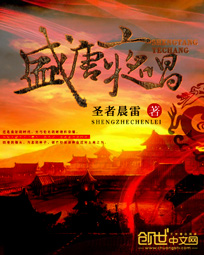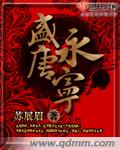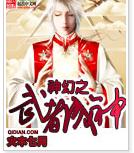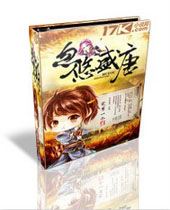幻之盛唐-第2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同样的疑问,也出现在城外大帐的诸将领心中,
明黄色地大帐金幔下,做在正首位置的史思明。 背靠全张白虎皮裹的大墩。 金瓜节钺的旗仗、龙纹的金甲、具装,依次在背后陈列开来。
他生的眉眼细长而深有城府。 相比容姿魁伟,身形肥大地安禄山,他显的很是清瘦,不多的须发,稀稀拉拉的掩在华丽的金冠紫带下,但与官军邸报上形容的所谓“鸢肩伛背、钦目侧鼻”的描述,其实相去甚远。 长久的兵戎岁月和塞上风霜,让他的面容如沟壑般深刻,也让他的形怒喜乐,一言一颦变地越发地威德权重,凌人心魄。
左右侧立是顶盔贯甲的李廷让、符敬超、左渝德、任瑗明、独孤允、杨日休,恭容光、荣敬、周挚、徐璜玉、李秦授,杨希仲、安武臣等一干文武能臣干将,这些在叛军声名显赫,一言九鼎地的人物,都沉默在一片让人的窒息噤声不语中。
为什么刚取得邺城大捷的这位王上,突然放弃主持大局,追击官军的残部,而星夜转道南下,以前彪卫夜入大营,突然夺了南路元帅史朝义的兵权,而亲临诸军。
心中虽然在犹疑,但不管是正当幸灾乐祸,还是惊疑不定,或是恍然自度,或是心起波澜,或是战战兢兢,被召集列席的人们,无论是真心假意,都挺胸凹肚,做出一个精神抖擞、荣有幸哉的模样来。 只有被他眼角扫视到的那一刻,哪怕再是凶名昭著,或曰桀骜不逊,或是心机沉沉之辈,也不禁要收敛了气机和棱角,露出最无害的一面来。
“把宁公公带上来罢”,在这死一般的静默中,史思明终于开口了。
话音未落,帐子哗啦挑开。
一个身如筛糠的紫衣中官,在身材高壮的前彪卫驱使下,巍巍缩缩的碎步上前,左右惊顾的看了一眼,才哆嗦着行礼,开口唤了声
“大。 。 大王”
“这是孤在乱军中所获的一个妙人,旧朝的军容使,宁知远,宁内丞,他刚好知道一些有趣的内情,正好叫唤大伙儿听听。 ”
史思明轻轻收回眼神,轻描淡写的说
“就是城里的这位,一开始就说孤,早有反心么”
宁知远被他这么一看,脚儿顿如化水软了半截,管不住腿要一屁股坐倒,却有被卫士提擎住。
“就。 。 。 。 就是他,在成都行在时就屡屡公开言称,说安氏逆众。 虽然颇多骠勇者,然多或无谋短近者,或贪婪私嫌,唯史氏如蛇蝮,声名不显,而首为大防。 。 。 。 。 。 。 又编逆党诸将图谱,。 罗列以性情,喜好之属。 ”
正是一头雾水的众将,听到完这段急急巴巴地细蔬,个中有心事机巧的,已然心中咻然抽起冷子来,三年前,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 三年前,这位王上。 可还是那位追随那位安皇帝的众多战将中毫不起眼的一员,难道就。 。 。 。 。 。 。
宁知远终于说顺了气一些,
“。 。 。 。 。 至河北,又屡屡上言,安氏之后,史。 。 。 。 ”
说到这里,他心惊胆战的看了眼史思明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
“。 。 逆为继之。 患除之,然诸将帅,笑而言他”
“。 。 。 。 后来,亦是此人执言大王必反,必慎防之,行营不胜烦之。 遂使南下,又移防诸镇预其事,。 。 。 所留太子对应之法,宪军、神机、战护诸属之议,皆从他出”
。 。 。 。 。 。 。 。 。 。 。 。 。 。。
话说到这里。 素为史思明亲信一些的大将,心中有些了然了,史大王在邺城下势如破竹,却在最后功亏一篑,被走了旧朝地太子,未尽全功。 竟然还有这样的因果牵擎。
“既蒙一直以来对孤家看重。 关照有之,这分殷切心情怎么也得还他不是”
史思明终于开口。
“再说。 自从蛰事范阳,某一贯厚币旧朝内结殷情,外屈事天下示以诚,费了偌大地工夫,被他一句话就点破了”
说到这里,他细眼猛挣做圆长,透出一种犀利无匹的让人胆寒的狠绝。
“这样的人物,怎么也得来亲眼见见,才甘心的不是”
对于这一切,史思明也有一种沧桑满怀的感触。
这些年天下风起云变,谁曾想赫赫大唐,百年的鼎盛之势,顷刻崩解萧墙,栗末人安禄山崛起于幽燕,帐下精兵猛将如云,什么曳落河四卫将、安家五子良将、近族六大亲直,十六家藩从子弟,十二姓外系将领。 。 。 何等地威赫连天,兵强马壮,不过数年,却也土崩瓦解,散若烟云。
作为最早追随安禄山的同乡,当年一起诱杀契丹小部酋首,而起家十数骑之一,俱以骁勇闻的同代人物,能够走到如今的地步,决计不是一个简单忍耐和心机,可以悉数的。
安禄山为人以知人善任,又多疑富有心机著称,虽然残忍好杀而重权柄,却对部下恩宽不吝,因此使将士敬畏而效死,仅仅一个同乡的交情,不足以让在他在战将如云的安军阵营中,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位置,
比如在安禄山登基时,别人顶着宰相、仆射、尚书地头衔相互攀比的时候,他只能作为一个小小的平卢兵马使,卑笑的站在百官靠后的队列里,做出一些可有可无的欢呼和恭贺。 正当无数庸碌苟且之徒,穿着公候才有地紫衣,前呼后拥的招摇过市,仅仅只因为他们姓氏中有个安字,或者是早年资给过安氏的栗末族人,他只能穿着发红的袍子,一一给让开道路。
作为一个不受特别重视的外姓将领,他所能做的,就是比安禄山更能隐忍、更有心机的低调和等待。
因此,他喜欢乱世,因为不经意中,机会很快就就到来了面前。
崔佑西征,安忠志出镇长安,。 。 。 。
利用安禄山那些亲族、裙带出身的心腹干将,纷纷大举出征,争抢地盘,为那些空许的封辖之地,拼命扩张之机,他却以厚币打点,留在了河北做了一个留守经略。
随后的事情,就如他所意料地,颜氏兄弟地断然举事,有如燎原大火,在河北数十州蔓延开来,大军在外的洛阳方面,竟也一时被烧地措手不及,心惊胆战,恰逢这时,通过适当的进言,正逢四面楚歌,突然发现身边少人可用的安禄山,一个沉厚低调,资格更老也更可靠的老乡,就重新回到了视野中,更关键他是个胡人,还是个杂胡,背后没有那些边藩大部的根系和触角。 看起来,总比那些投附过来地三心两意的汉将更让人放心,
面对此起彼伏的反叛和聚入蚁附的义军旗号,为安禄山不辞劳苦的到处救火平乱,两战常山、袭破饶阳,三围太原,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事下来。 一边还要暗中内结军心以恩义,外敛物力蓄以大势。 然后还要送上足够的金帛子女,让洛阳那些“新贵人”满意。
无疑,他也是幸运地,蔡希德战死晋阳,程千里常山被俘、高秀岩阵亡于大同,崔佑乾、孙孝哲、安忠支这些西征的重量级人物,都相继折损在关中战场。 而负责留后地刘客奴,更干脆投附了旧朝朝廷,在这期间,更有无数野心勃勃的年轻才骏,如慧星般崛起,又如流星般陨落。
但他总能凭借比别人更多一分心眼的谨慎与小心,屡屡逃过杀身的危险中,战败并不可怕。 只要活着就好,同时代能够与之并肩的重量级人物,终于越来越少,硕果仅存的他,也越来越发的德威权重。
战打地多了,人杀的多了。 部下也多了,地盘也大了,自己的位置和权势,变的越来越重要,欲望和野心也在勃勃而涨,终于利用安禄山不理世事,外事委于高尚,洛阳官职贿卖成风,得到了范阳节度使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于是更大的目标也出现。 。 为什么要甘心于只做一个生杀全权的强藩。 在那洛阳的紫圜殿上,应该有一个更好地位置。
当别人都觉得大业既成。 肆意搜掠金帛子女,圈占田地庄园,营造华物大宅,以遍衬的上自己新朝勋贵、王侯的爵衔,他却在抹兵利马,勾通诸胡,收买人心、阴蓄实力。
终于安禄山安逸于酒色的昏聩,而任事不明,使将士逐渐离心,而安氏诸子为了继立大统而明争暗斗,乃至攻杀相拭的内乱,更让本来就已经虚弱的安氏一族四分五裂,也给了他取而代之,一跃成为代表整个河北武人集团利益,成为领头人地机会。
当越来越多的安军将领,在朝廷卷土重来的步步进逼下,不得不的避开了纷争不休的洛阳,而越来越频繁的转向范阳求助和请教,这也给了他一个新的机遇。 按照态度和实力,或是适当的拉以援手收买人心,或是假借官军剪除异己,或是干脆制造一个借口和理由吞并所部。
然后是暗中谋划的种种。
从纵胡入关,搅乱局势,到离间朔方和晋阳军,利用河北守臣的恩怨和党争,相互孤立又个个击破,既要算计官军,也要时刻提防着自己人,毕竟在着乱局中,有野心又能把握机会地人,可不止他一个。
现在一切地隐忍和付出,都收到了回报,栗末人安禄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史家王朝地时代就要来临了。
他虽然祭天告地誓师伐罪,誓位安禄山报仇,但却从来不信鬼神天命什么的,什么叫天命,手上的兵强马壮无人能当,就是这世道最大的天命,什么大义,什么正统,在这绝对的武力面前,几乎都是不堪一击的,李家王朝在这场战事中,表现出来的庸碌和无能,让世人也知道了,旧朝廷虚有其表的强盛,几乎是一捅就破的泡影,
要知道,百年前的李家,也不过是一支假冒汉人的鲜卑种,窃据了旧隋的遗产,才得以进位天潢之族的。
这种自己有天命在身的信心满满,在他亲自策划的邺城之战后,更是达到了顶峰。
自从在心怀鬼胎的告谢宴上,将邺城那位已经山穷水尽的所谓“皇上”安庆绪,勒杀当场,居然没有一个人敢来劝说或者阻止,当高邈、吉温、张万顷、独孤问俗、张休、张通晤,李感义这些安氏的资深旧臣,都战战兢兢的跪伏在席上,口中高声说篡党该死,山呼燕皇万岁之时,他就更加深信不疑,甚至连走了那旧朝的太子那点不完美,也变的不那么重要了。
但是这持续的大好心情,却因为一个意外戛然而止了,这个叫宁之远的旧朝宦人,为了保命,居然上告说有重要内情密报,虽然他不大看的上这类卑下之徒。 要知道前朝就是坏在这些人手中地,但宁之远的观军容使身份,还是让心情大好的他,还是想听听这位阉人,为了保命,能够胡撰出些什么。
但听了他匪夷所思的开口,第一反映就是把这个满口胡话的家伙拉出去让乱马踩死。 开什么玩笑,前朝朝廷那些贪鄙之徒。 要有这分先见之明,还用的着被安氏一族,攻入长安追落荒而逃么。
但是出于一贯多疑性子,他却没有断然处置,毕竟邺城之战最后急转直下的变故,让他心中尤有疑义,想通过拷问其他被俘将官地验证一二。 结果意外的是却又从侧面隐约证实了这位所言。
说实话,他讨厌意外。 虽然他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什么未卜先知地本事,但是他也讨厌变数,特别是这么一个,看起来似乎能够事事多料于先手的变数,不免特别留了心来。更该死的是,这人还与旧朝的李家关系亲近。 手握重兵,对前朝来说并不是一个人微言轻的所在,现在不予信他,不等于将来也一直不会相信他。
后来又知道,而史朝义率领的负责攻略河南的大军,居然会被一支以外出现禁军被缠住。 费了老大工夫和代价才击败之,困守在卞州,却也因此无法按时前来会兵,以至于未能完成合围官军地最后一击。
一切的因缘际回会,竟然都错杂在一起。
想到这里,他微不可觉的叹了口气
只可惜,这位可没那么容易,再把他变成第二个安思顺
(安思顺,前朔方节度使,提拔郭子仪的前辈。 因为他很有先见之明的。 在事前屡屡示警说安禄山必反,后来安禄山真的造反了。 他又因为和安禄山是族兄的身份,再加当权的都元帅哥舒翰又与他不和,被朝廷削夺权力,以通敌名义赐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执送出来,随行地大燕行军司马周挚突然开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