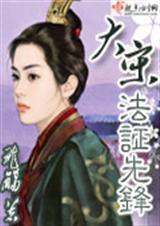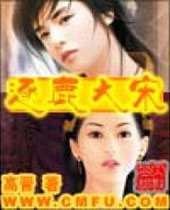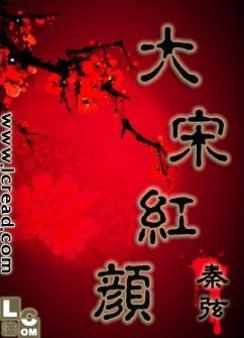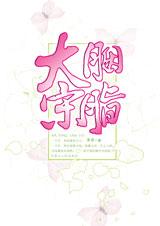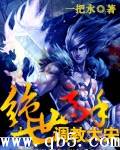权倾大宋-第2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只恐朝诸公多不愿远行,不能不深虑之。”
王秀明白秦桧犹豫最主要的原因,朝廷诸多大臣们的反对力量的确不容忽视,秦桧是是怕附议后,会被视为他的一党,受到不必要的责难。
尽管他握有兵权又有太后支持,但大宋的政治体制有它的独特之处,面对众多顽固势力与天下士林,他的胜算在秦桧看来还是不大。想到这一层,心胸豁然,这不过是人之常情,倒是不能责怪秦桧犹豫,换成他也得掂量一下。
女真人把很多大臣掳走,开封许多世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剩余势力仍让秦桧忌惮,可见放在平时,那些既得利益阶层会多强势想想林灵素的遭遇,再想发生过的很多事,包括他的经历,哪次不是和这些势力联合或对抗,换句话说,他还得感谢女真人,为他扫除了相当的麻烦。
越,真不是乱穿的,你是有王八之气,虎躯一震,或许能起到强势的效果,像手握十万雄兵,能够弹压别人的不满。但是,随着那些势力的不断合纵,迟早你要为强势付出代价,历史多少强势人物,拥有精兵强将,打压的既得利益阶层抬不起头,但最终还是败的连身家性命也没了;还有一些人会利用天下大势,审时度势地争取和妥协,最终开创辉煌的时代,他显然要做后者。
“会之兄说的是,小弟明白此事非易,但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策,无论有多大的阻力,多少人反对,小弟也不能眼见娘娘和官家身处险地,这不是妥协而是原则。”王秀的口气非常坚决,看向秦桧的眼神异常坚定。
妥协是必须的,但有时候强势也是必需的,看你怎样把握两者间的度,他认为迁都势在必行,哪怕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是原则性问题。
原则是决不能妥协的,不然,还能叫原则
秦桧的指尖微微颤动,他明白地听出王秀话,所隐含的另一层意思,这绝对是王秀下定决心要做的事,且不惜一切要成功。同时,他更清楚王秀目前的实权,能取得太后绝对支持,迁都占住大义的立场,成为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让他有点心动了。
何况,王秀的话很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必要时会动用武力,想想王秀敢面对强敌冲入孤城的做为,相信在必要时这厮绝对敢杀人,他可不愿触碰晦气,在女真人面前有风骨是一回事,但在自己人面前不不必。
“小弟希望会之兄助我一臂之力”话说到这个份,王秀则是单刀直入,一点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逼秦桧表明立场。
或许,是有些霸道,很有可能引起秦桧的反感,但相较秦桧的暧昧不定,他感到有些事情必须要直接,在这乱局还是用些霸王手段来的实在。正如秦桧揣测的那样,一旦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吝惜手段,哪怕是杀人也必须去做。
看来今日不表明立场,王秀是不会善罢干休的的确,话说到这个份,秦桧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确实也知道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策,王秀的逼问也是迫于形势所迫,尽管对王秀用此霸道的手法逼自己有些不快,但面子却不能表露出来。他慢慢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品着茶,心里却是权衡着自己的政治筹码,倒底是投向王秀,还是和孙傅、唐格等人分而治之,成为多极权力的筹码。
但是,强势的王秀能甘心为他人做嫁衣显然是不可能,首鼠两端最不得人心,当他放下杯子,心已经有了计较,慢吞吞地道“若有太后懿旨巡幸,择一大郡设为行在,小住些许时日,想来他人也必不会多说”
秦会之,好一个老狐狸啊王秀一怔,旋即明白了秦桧的意思,不由地心生感叹,有感觉很好笑。
秦桧的策略的确是高明,也避免了因公开支持他,而开罪别的大臣,开封依旧还是京城,太后和皇帝巡幸东南所到之处,设立行在理所当然。也是说,没有迁都而行迁都之实,虽然朝堂之必有人反对,但阻力较强行迁都要少得多,大家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反对。
他再看秦桧,觉得这厮鸟能在历史风起云涌,确实不简单啊自己还得要重新审视此人,绝不能被表象所迷惑,不由地面带笑容,道“好啊小住几日,会之兄高见”
秦桧嘴角一抽,翻个白眼,索性不再理会王秀。
。。。
第四五零章 南迁3
小皇帝赵谌,如同木偶地坐在龙椅,玉帘后的太后朱琏与五位辅政大臣各怀心事,殿内的气氛有些紧张,却又静的令人窒息。
“各位卿家,哀家是妇道人家,不懂国家大事,朝事仰仗各位权衡,可王卿家提倡巡幸东南事,议一议。”朱琏终究是开口说话。
王秀听得朱琏说话,禁不住轻轻叹气,有感于大宋的政治民主的有些迂腐,昨日里自己的札子,孙傅、唐格等两府重臣都以知晓其意,谁反对、谁赞同,大家都心知肚明,却还要拿到明面冠冕堂皇地庭议。
“臣以为王大人所言巡幸东南之事,多有不妥。”
王秀眉头微挑,他知道无论迁都还是巡幸,都会遭到那些君子们的竭力反对。不过,让他意外的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不是孙傅,更不是唐格,而是张叔夜。
张叔夜看也没看王秀,朗声道“如今大事方定,百业待新,天下臣民无不瞻望朝廷。臣以为应以稳定大局为重,请九大王回京。此时巡幸东南,难免让各地守臣不安其位,百姓不能安其业。何况开封是百年故都,国家之根本所在,天下哪有一处能开封城池坚固”
不能不说,张叔夜说的有理有据,自太祖开国,为防备晚唐地方割据,五季诸国相互攻伐,在全国范围内拆除各地城池关防,除陕西五路与河东、河北各路为防御而保留各军州城隘外,内地军州的高城深濠拆除大半。如,整个四川只保留四座坚固的大城,东南各路虽在方腊做乱时建有不少城池,但那只是临时仓促建成,根本无法与北方大郡城关相提并论。
真是老生常谈王秀对张叔夜的理由极为蔑视,他相信张叔夜绝非以此理由拒绝迁都,借口、纯粹是个没事找事借口,心应该另有它想。
朱琏似乎有些犹豫,她的目光紧紧洒在王秀脸,却见王秀神色如常,丝毫没有要出班反驳的意思,实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当下犹豫地道“张卿家说的却也有理。”
王秀下意识地看了眼秦桧,却见秦桧的双目直直地望着前面,正专注地研究精致的地面花纹,无奈地轻轻一叹,这贼厮鸟真是滑头,不见兔子不撒鹰。
他缓缓地出班,沉声道“臣以为张相公所言不错”
此话出口,在场众人无不惊讶,都以为王秀要据理力争,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自我否定,是朱琏也惊讶说不出话,张叔夜更是转脸不解地看着他。
却听王秀淡然一笑,缓缓地道“只是,臣以为张相公只见其弊,而未见其利。”
张叔夜眉头微蹙,道“哦,还请王大人指教。”
“不敢。”王秀淡淡地道“张相公多年来为天子牧守一方,自是见识广博,在下岂敢妄自菲薄。”
说着,话锋一转,语气渐渐加重,栗然道“张相公所倚是寇莱公固守开封成例。当年寇公力排众议,请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击退契丹,不可不谓之善,下官亦是甚为感佩。不过,相公以为当今天下局面,与真宗皇帝时可有出入南北盟约再定,朝廷暂时无力收复河北、河东,虏人铁骑和开封隔河相望,能否养兵百万御敌”
张叔夜摇了摇头,没有做声,养兵百万是言过其实,但他也明白留在开封,非得数十万大军拱卫不可。不要说现在一片凋敝,放在平时朝廷也负担不起。
他顿了顿,强辩道“只要政令清明,天下士民必然归心,区区虏人又有何惧。”
王秀眉头一挑,玩味地道“相公是说两位太政令不清,误国误民”
这大帽子砸的,张叔夜一阵白眼,赵家父子怎样大家都明白,但明白是一回事,说了又是一回事,要真被王秀扣严实了,御史台那帮疯狗一阵乱咬,那真悲剧了,他不得不牙疼地道“此一时彼一时,这个、这个。拒敌国门外,在德不在力。”
狗屁在德,王秀听的一阵牙疼,他也知道在场的包括张叔夜本人,也拿这话当放屁,不由地微笑道“既是相公也认为此一时彼一时,那下官只能明言了。以下官愚见,当年契丹执政萧太后年事已高,其南侵本意不在掠我国土,而是顾及朝廷强盛,孤注一掷迫使结成百年之盟,让南北休兵、生民休息,其立意可谓甚善。寇公洞察其意,才反对天子巡幸,终成南北百年良家之好。”
对于王秀的这番见解,在场大臣都很是吃惊,唯独朱琏饶有兴致地隔帘而观。
“如今,虏人两次南下,山河破碎、民生疲弊、军力不振,大河之北尽染腥臊,不为我汉家所有。虏人虽然退军,但狼子野心、贪念不足,随时可能南下,他们的马队渡河,一日夜能直抵开放城下,可谓朝发夕之。如今大宋近支皇族只有官家与康王,一旦再次围城,张相公可有把握退敌”
张叔夜依旧不服输,争辩道“只要朝廷政治清明,精练禁军,据河而守,何惧区区虏人。”虽是如此说,但他心还是有些感到不安,王秀说的并非虚言,金军的再次南下只是个时间问题,这也是两府重臣的共识。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大宋君臣一体,勤修政务,待虏人稳定河北、河东再次南下,相信以区区十余万金军,朝廷应该能守的住。对于迁都,他本无太多意见,也很赞同避开锋芒,但耳边回想起孙傅的话虏人不足为患,开封乃天子根本所在,一旦迁都如龙入浅滩,虎落平阳,恐祸起萧墙。
他微微一颤,不经意地瞥了眼王秀,想到王秀闯营夺兵,血战入汴的胆识能耐,笑谈间让女真大帅无可奈何,手握十万锐卒,使人感到不栗而寒。一旦天子南迁,王秀若有异心,必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和孙傅、唐格三人担心所在,唐格虽然看不孙傅,但在这件事,却出的与孙傅保持一致。
大宋朝廷养士百余年,善待读书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士人对赵家拥戴深入骨髓。朝廷的制度也被臣们所接受,任何有违制度的事情,在他们眼都是不能容忍的。而王秀闯营夺兵,擅杀大将还可说得过去,但如今还是紧握兵权不放,门人更是直入班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接受。
东京开封府是经营百余年的都城,纵然遭到女真人掳掠,王秀又兵权在握,但保皇的势力依然强大。在众位大臣和京城百姓的睽睽目光下,谁也也不敢过分造次。一旦南迁,失去这等根基,难不保王秀会为所欲为,到那时可什么都晚了,这是他们反对迁都的根本原因。
“据河而守”王秀面露出讥讽的笑容,风淡云轻地道“千里大河,不知相公如何据守时至今日,谁还认为短期内朝廷能与虏人抗衡”
“只要、只要我大宋君臣一体,何惧鞑虏。”张叔夜压根不相信与女真抗衡,但有些话却不能不说。
“相公风骨,在下佩服,但老生常谈,是自取灭亡。虏人入汴,娘娘和官家出宫,何人以德服人君臣一体,怎么丢了开封城血肉之躯怎能和甲骑具装抗衡”王秀嘴角,挂着一抹讽刺意味地笑。
不要说朱琏母子遇难,百官生民无可奈何,单说两场大战,北方禁军基本损失殆尽,只有陕西六路保留相当兵力,再者是赵构的兵马大元帅府,他的十余万大军还有战斗力,东南禁军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抱有幻想。
西军还要防备党项对横山的窥视,仓促间不能调动。赵构的兵马太少,自保尚且不足,谈何言战,整个大宋能和金军对抗的也只有他,而且确实取得了局部胜利。
尽管,王秀的胜利挽救了天下,但一个才华出众的臣,取得如此的威望,手握整个大宋的命运,不能不让对赵家忠心大臣感到阵阵的不安。
“王大人言重了”孙傅见王秀言词犀利无,大为不满,出班道“大人也是孔门弟子,读的是圣贤之书,岂不闻兵者凶也,圣人不肖此道。虏人虽是凶蛮,然我等可以圣人之道循之,以礼义感知。”
王秀对孙傅的迂腐感到可笑,又有些可怜,这种人对国家确实是忠心不二,但往往国事也败坏在他们身,空谈误国,书生之见,酸不可闻啊也不待孙傅说完,他冷眼看着孙傅,嘴角依旧挂着充满讽刺意味地笑。
孙傅无意看向王秀,那副玩味的表情,心一颤,似乎想到了什么,老脸顿时一红,再也说不下去了,那道笑容,让人想到不堪回首的往事。
“王大人,虏人若再来,迁都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