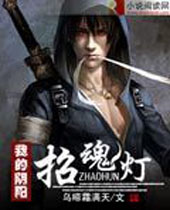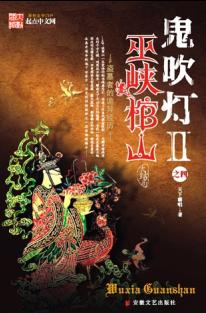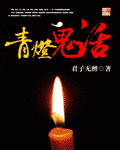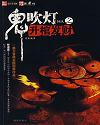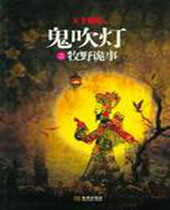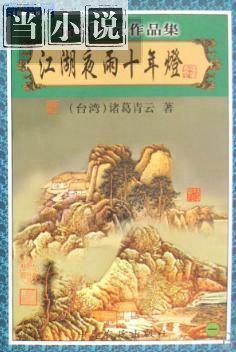点一盏心灯-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什么要把墨丢到水里呢?我心想。不过跟着便偷偷把我的“极品墨”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奶粉罐里,并藏在柜子深处,直到有一天母亲说柜子里必定死了老鼠,才发现那罐子已冒出了白毛,臭得比阴沟水还可怕。
极品墨后来总算被瓶装墨汁代取了,小学五、六年级,有人用化学制的墨膏盆,有人用蜡纸装着墨汁瓶,我则承继了父亲的铜墨盒。
铜墨盒原是父亲在办公室用的,方正而略带圆角,盖子及盒边都是黄铜打造,上面精工刻着两个殷商铜器的图纹,盒底则以一块红铜镶嵌。墨盒打开,里面装的是泡了墨汁的丝瓤,盖子里层有一方石版,大概是专用来添笔的。
墨盒拿回家的时候,已经是父亲过世百日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墨盒打开,里面却早已干成了一小块。母亲去找了些丝棉,用水烫熟,又把墨盒洗干净、将丝棉放进去浇了些墨汁:“从今你就可以不用磨墨了,干了就将瓶装的墨汁加进去,比磨的好,你老子磨了一辈子,也没磨长久,而且磨出来的墨汁倒在墨盒里容易臭,像他的臭脾气!”
“用咱们家如兰似麋的墨去磨,就不臭了!”我说。
“照臭,把麋香闷着,只怕臭得更凶!”
墨盒确实比较好用,由于有丝棉的滋润。它不必像用瓶装墨汁般地不断添笔;否则会有渗碗晕浸之忧,也不像磨墨费时间。但是我只用了一年多就停止了,因为我不高兴同学们好奇地把玩我的墨盒,也不喜欢老师的讯问,尤其是一个初次上课的国文老师,在观赏我的墨盒之后说:你真有福气!这么小,就用这么讲究的东西!
我把墨盒洗干净,用父亲丧礼后摘下的自帐白布层层包好,交给母亲,她不解地看我。
“把它跟黑金条放在一块儿吧!爷爷留下的墨,爸爸舍不得用;爸爸留下的墨盒,我又何必用呢?”
有些东西,似乎是当然应该跟着它的主人去的,它属于上一代,能使下一代,有所感动,却无法进入下一代的生活。
我又回到了磨墨的日子,而且渐渐开始喜欢那种“墨与砚若相恋恋”的感觉,一块平凡的石头,一块黑黑的墨条,当注上水,轻轻磨几下,居然就能产生淡淡的幽香和纯纯的墨汁。它不像瓶装墨汁那么浓,却比墨汁来得细腻;它容易晕散,但晕散得均匀而优美。尤其是在学国画之后,更知道了墨有“干、湿、浓、淡、黑、白”五韵,又有焦墨、宿墨、埃墨,乃至松烟、油烟的不同。
那时我用的是一块日本制的吴竹墨,通体包着金,仿佛一块真的金条。
我花了好几次赚得的稿费买下它,却发现它是那么难磨,画小小一张图,单单磨墨,就得耗上10多分钟。
但是我一直把吴竹墨用到无法再抓得住,才收进柜子,因为尽管难用,它却是我所用过的最贵的墨,使我想像自己也是昂然的一介书生,如同父亲口中的祖父一般,用那上好的李廷轩墨,飒飒几笔,就成为众家争求的墨宝。
每一次看到古画,我都会想,不知道这画家用的是什么墨。如果在裱画店里,我甚至会贴近那些作品,细细地嗅一下墨的味道,并注意墨沛中是不是有那金玉之屑。
“有金有玉,这么多年也早掉了!”裱画店的老师傅说:“只有墨最实在,几千年几百年都不变,有时候纸绢黄得不成样子,那墨迹可还是清晰不改。所以墨不必多么贵,只要细致、不掉灰就成了!”
从高中历史课本里,我也确实读到“由甲骨文的朱书、墨书痕迹,可知中麋的墨去磨,就不臭了!”我说。
我把墨盒洗干净,用父亲丧礼后摘下的自帐白布层层包好,交给母亲,她不解地看我。
“把它跟黑金条放在一块儿吧!爷爷留下的墨,爸爸舍不得用;爸爸留下的墨盒,我又何必用呢y国在殷商已经有了笔墨的发明”。算来几千年,那龟甲兽骨上的笔痕,不还是清晰得一如昨天书写的吗?
由于好奇,我特别找到做墨的地方,没想到那竟然如同火场废墟一般,四处都是焦灰。在一间低矮的瓦房里,看见盏盏灯火,于黑暗中跳动,每一个火苗上,都有着一个半圆的钵,收集下面窜升的油烟。另一处破了顶的棚子里;几个工人则在锤打和了胶的烟墨。
我没有看到如父亲所说的珊瑚末、珍珠粉和玉屑,墨对我不再那么神秘,我却对墨多了一分敬佩,觉得它很伟大,伟大得平凡,从最平凡的地方发生,成为最长久的存在。
我也渐渐了解,这么平凡的东西,是人人都可以发现,也可以制造的,譬如画黑蝴蝶,为了表现那不反光的黑翼,史就曾经用白瓷碟,放在烛火上,收集烛烟来当墨用。譬如西方人用的脸汁,常叫印度墨,可知印度人也很早就使用了墨。
既然烧东西会产生墨烟,当然任何懂得用火的民族,也就都可能用那黑灰来作画,写字,那黑灰也就是墨。
可是为什么只有在中国,墨才能被发扬光大,且在那水墨的无边韵趣中,表达出深入的情思?
有一天在研墨时,我顿悟了其中的道理:
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制成墨汁来使用,而是将那烟灰做成墨丸、墨锭、墨条,每次使用,每次研磨,取那砚池中的水,和以墨牛,来耕砚田。
于是“试之砚则苍然有光,映于日则云霞交起”,那每一次墨和水的遭遇,便成为一种风云际会,与濡水蘸墨的毫翰,构成了许多机缘。
他们不像用钢笔蘸浓墨汁,只是单一的表现,而是不断地交融、不断地交织,不断在偶然的飞白、渗漉、晕浸与泼洒间,创造出一种永不重复,永不雷同的结局。
小时候父亲说的神妙故事犹在耳边,那压箱底的黑金条却随着一场大火而成为灰烬的一部分,说实在的,我几乎没能真切地看清楚李廷轩墨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家中曾有祖父留下的好几条传家宝。
传家的李廷轩墨原是不准用的;不用的墨又何必生为墨,它的存在与不存在,也就于我甚至这世界没有太大的关系。不过我喜欢父亲珠粉、玉屑。麋香、珊瑚末的描述,也欣赏祷画店师傅对那珠玉的否定,因为墨之为墨,正如我之为我,本元需那许多精巧的妆扮。而若没了那许多附会夸大的添加,世上又有几人能予宝爱,且从这平凡的漆黑之物中,悟得许多真理?
纸情
从香港寄来三件大邮包,是两个月前订的一百张“蝉衣笺”、一百张“罗纹宣”,50张“玉版宣”和20张“豆腐宣”。一一点过,并在包装的牛皮纸上写下日期和名称,打开柜门,却发现三面架子,早已塞得毫无隙处,甚至有反潮之虞的地上,也堆了数十卷“月宫殿”,正不知如何是好,又听门铃响,邮差笑说忘了一包由台湾寄来的东西,才想起是月前在和平东路买的两百张棉纸。
总忘记自己茂纸如山,甚至连更衣室里,床底下也塞满了各种纸,却还老是四处搜购,只要看那纸行老板一挤眼:“我偷偷收下了几十张文化大革命前的东西,您要不要看看?”便即刻一挥手:“甭看,我全包了!”
碰到学生买错了纸,说是要扔掉,我更不忙不迭他说:“不要扔,拿来给老师练字,或转卖给用得着的同学。问题是,练字用不了多少,差的纸也少有人要,只好愈堆愈高。于是从那干隆纸、金粟笺、发纸、蝴蝶海苔纸、画仙纸、各式宣棉纸,乃至最廉价的机制纸,立身其中,觉得像个纸行,而朋友见了,则呼我千声“纸痴”!
嗜纸而能成瘾,大约总非一日之功,而当天生就对纸有慧眼,于是看纸不过为纸,我看纸,则其间自有许多乾坤。
譬如手工制的长纤维与机制的短纤维纸就不大相同,凡是透光看去。一丝丝纠葛盘旋,如同满天云龙,而且上下左右的韧度相同,必是手工漉成的长纤维纸。至于看不出明显的纤维,上下和左右的韧工又不一样的,必是机器制造的短纤维纸。
这是因为前者用手将泡软的树皮,一条条撕开,锤打、蒸煮、加胶,再以竹竿搅拌,举漉成。当纸浆被捞起时,因为经过手工摇动,所以纤维的分布平均。后者则不但在机器搅拌时,容易打碎纤维,更因为制造时纸浆的流向相同,而缺乏变化。
这许我知识,实际也是一日日累积的。记得有一个行家,曾叫我撕报纸,纵横着撕与直著撕感觉的不同,而使我了解了所谓的“纸浆流向”。
裱画老师傅自然更是审纸的高手,他曾经教我从纸上竹帘的痕迹,一做为重要的鉴定依据。
“你叫黄君壁用港宣或是宋褚,当然成,但如果发现任伯年用的是埔里的台宣,就非假不可了!”他又眯着眼睛,神秘兮兮他说:“以前人会用寺庙里抄写经文的‘写经纸’,以求其古;现在也有人专跑图书馆的善本部门,偷前朝书里的老纸造假,若用那宋纸、宋墨,只题名,加上宋代不与盖章,你说怎么鉴定?”
老师傅不但能裱、精鉴,还会接纸、造纸。他说中国纸最好接,因为是长纤维、质软,所以只要在两张纸的接头处把纤维拉长,就能天衣无缝地接合。
老师傅接纸全不用刀,先将纸边打湿,用他那长甲细细刮薄,再淋上浆水,再把接的纸,对准帘纹地放上,将重叠处照样刮弄一遍,卷起风干后,果然毫无破绽。
至于造纸,有一回看见客人拿了张破了的古画,要求师傅把那破洞,用同一式的纸料补上,却又不准从画边上切纸填补。“既要纸质、颜色相同,能找到一样的老纸,师傅怎么敢接呢?”我心想。
却见老师傅用圆口刀,从画面四处平均地刮了一遍,收集下一团纸毛,调上浆水,压平之后居然造出来一小片,正补上了破洞。
从裱画老师傅那儿,看到的新奇事儿,真是太多了,而我对纸,尤其对中国纸的瘾,大概也就从那时种了根,我尤其记得他说:
“没有这么精良柔韧的纸,画如何能经得再三的装裱?没有长纤维,画又如何能棱成卷轴,历经几百年无数的舒卷而不新?没有这么细的纸质,中国水墨的韵趣又如何发挥?纸是中国人发明,纸的精神、灵魂,也只有在中国获得真正的提升!”
纸居然也有精神、灵魂?我一步步地追索,发现手工造的纸,确实各有各的面目,非但不同批的纸,因为纸浆中胶含量和纤维密度的差异而不同,即使同一张纸,左右也可能有厚薄的区分。
加上中国的“生纸”特别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悬浮物”,所以放置久了的纸,能成为半吸水的“凤矾纸”,有时候放得太近厨房,因为吸了炒菜的油气,画来满篇细小的白点,更造成特殊的效果。
黄君壁老师就最会利用这种效果,有时我在想,我是小纸瘾,他才是真正的老纸瘾。因为不论多么旧、多么皱、甚至染了满处墨痕的垫底纸和生了寅斑的受潮纸,到他手上,都能成为特殊的效果。于是白点成了雨景,潮班成为云树,皱痕成了石纹。
“顺着这些斑点作画,反而能打破旧格式,创出新构图!”黄老师说。
可不是吗?纸被我们从橱柜里请出来,展在案上,轻拂纸面,如同相对促膝的老朋友。它不是被我们役使,我们也不能全听它的,而是在彼此了解体谅、互就互让的气氛下,共同创作一张不朽的作品。
作品之不朽,也靠纸之不朽;纸若朽了,作品也便难存在;而艺术家的不朽,更有赖于作品的不朽。这位朋友在笔朽、墨枯、人亡之后,依然为我们发言,岂不是太伟大了吗?
所以即使是不着一墨的白纸,于我这个纸瘾,也便有许多遐思可以驰骋,正因为它不着一笔,所以可能有无限的生机,如同一个初生的孩子,代表的是无限的希望。相对地,如果不能善加利用,也便毁了它的前途。
于是这纸与每一个用经的人,不也就是一种缘吗?
是何其有幸的纸,能被携人修楔的兰亭,成为王羲之笔下不朽的兰亭集序,落人辩才和尚的手里,再被萧翼偷出来,经过各家的临摹,却又不幸地随唐大宗而长眠?又是何其有幸的纸,能被黄公望画上富春江畔的十里江山,进入收藏家云起楼主之手,临死殉葬投入火里,再千钩一发地被抢救出去,留得残卷,成为故宫的无价典藏?
又是何其有幸的南唐楮树,能经过寒溪的浸润、蔽冰举帘、荡涌熔干,成为那“滑如春水,细如蚕茧”的“澄心堂纸”。
又是哪一位慧心的人,在简犊、缣帛风行的时候,会想到以树皮、麻草这些平凡微贱的材料,捶煮成|人世间第一张纸呢?那初生的纸,会是多么地粗拙而丑陋,它必定有着不整齐的边缘,高低起伏的表面,黄褐且带着灰砂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