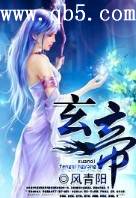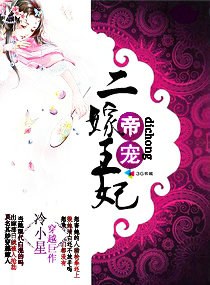���ӵ�-��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ӳ����ڰ�������ʱ������Ҳû�����⣬����������������̫�������֮�У����Ĺ��¡�ĸ���Ĵ�˵�������е�ս��ͼ�������������н���������ȴ��ôҲ��Э����һ�𣬾�����������ͬʱ���IJ�ͬ���
�������������磬�������̲�ס�ˣ���ʫ�Ĺ��Ը��ڵ��������ã��ſ�����Ҫ˵�����ʵ��ȿ����ˣ�����ʦ����������ɣ���
������������ס�ˣ���������һ�������ʵ�˵����װ��Ϳ���ȥ�Dz����Եģ�ֻ�úߺ������˵�����ϳ�������ѧ�����鲻ꡣ�����˵�Ǻܶ࣬������һЩ�ɡ���
�������ǽ��콲����ʫ��������Ķ����ɡ���
���������������������ʫ�����ſ�ͷ��һƪ�����¡���û���ꡣʫ������־�����Զ��顢�����̵¡�����ֹа��ʫ�����д��壬����أ���������������������������ѧʫ������
�������������������ȥ���Ӷ��ܿ��ʵ۵����ɺ����ӽ�����Ҫ�ش�������µ����⣬������ʫ��������ע�⣬�������鰸���ô�ѧʫ����һʱ������������������õġ���
����������ɫ��䣬�����£���ʫ���������ô���������־�����Զ��顭����
���������Ӽ����ô��鰸����̫��Ͳ�ѧʫ��������̫��Ĺ��£���ʦ��������࣬��˵����������
�������Ե�������˽���ɫ��ֻ�����������ſڵ�����̫�̫࣬��Ҳ�ܻ��ң����Ҹ����κ���ʾ�����ڲ�ϯ�Ķ������������Żʵۣ��Ⱦ������Ի�
������̫�桭��̫��Ĺ��¶����ڹ�ʷ֮�У�����������������������ϳ��������Ƽ���λר����ʷ�Ĺ��Ӽ��̫ѧ�IJ�ʿ�����ǡ�����
�������ұ���̫�鷳�ˣ���Ҳ��������ȫ������ʦѡ�����ܽ�������Ĺ��¾��С���
�����ſڵ�һ��̫��Ҵ���ȥ�����Ա��Ƶ���·�ˣ�ֻ����ǿ˵��ȥ����̫�湦�߸�����ب��δ�У��ܽ�������Ĺ���ʵ��̫���ˣ�����������ϳ����롭����
�������Դ���������һ�ᣬ��ɫ��첻��������Խ��Խ���أ�ͻȻһͷ�Ե�����Ȼ���˹�ȥ��
����̫�༱æ��ǰ����������Ӵ��һ������ôҲ�벻���Լ���һ����Ҫ��Ȼ������������صķ�Ӧ��
����������Ц��һ��������������������ѳְ�ɣ������ڻʵ���ǰ������һ����Ҳ��ֵ�ˡ���
��������Ϲ˵����������̽���������ɲ���������Ϊ�Լ��ļ��仰��������������ô������
���������ϴ��ˡ��������š���̫��˵����ʱ��һ��̫������ˣ�����һ�齫����̧��ȥ��
��������Ŀξ���ô�����ˡ�
����������ôͻȻ��̫�����Ȥ�ˣ���������ֻʣ��������ʱ��������������ʡ�
�����������������ͼ��������ĸ������һЩ���£�����������������ν���̫�棬û�뵽��������������ӣ�̫��Ĺ�����ʲô�ɻ��𣿡�
��������Ҽɻ�IJ���̫�棬�ǡ�����֪����˭�����������˲�ϣ����ѧʷ�飬����Ұ�����͡��������������졣
���������ˣ����˼��ۣ�ʲôҲû˵��
�����������ϣ������ӽ�������½��������˵�����������ڻ����Ƕ���ʷ��ʱ���ҽ��Ĺ����㹻���ˣ�������Щ��˵��Ӧ���ܵó����ۣ����������룬�ȱ����������ˣ����������½�����
������������ֻ�̻ʵ����֣����ν�Ҫ������ʱ�������ʣ������ǰ����ʲô�ģ���
��������ǰ�Ҿ���̫�࣬�����ȵ�ʮ���꣬���ۿ���������
����������ǰ�أ���϶����Ǵ�С��������̫��İɣ���
�������ҡҡͷ������Ȼ���ǣ�������Ҳ�Ƕ����ˡ���������������ҵľ�������Ȥ�����ҽ�����۵�ʱ��������˵һЩ�����²�Ҫ��̫����������ҵľ����dz����ò���ʮ�仰����˵�ꡣ��
�������������ţ����Ĺ�ȥ������
����������û�г��֣�����������ʦ����Խ���������У��������ϵ����ݣ�������˵һ���֣�������Ҳû��Ȥ�ٱ����ǽ���ʷ��ÿ����Ƿ�����������ȥ�ػ���̫�������¼���
����������Ѯ���ض�������Ϣ���������Ͻ��ܳ�͢����Ѷ�����ڻ��ǹ����췴�ˣ���ϧʱ�����ţ�������������ͨ��������������ʱȫ��Ͷ���˳�͢��̫���ꡪ�������ƽ�������������˼���ʤ�̣�һ·��������������ƽ������ָ�տɴ���
������������ϲ���ǣ�ϲ���Ǿ˾����´��ҵĸ��������ȶ����ǵ��Ǵ�һ����ʤ�ؾ������þ�Ҫ������Ϊ�ʺ�
��������ѫ���̴���ֻ���˷ܣ����������۷ף�ȫ���ź��Լ�������ս��������ҵ����ʱ�����ܴ������Ƹ����Ӿ��Ǵ����������˽����ս�µĽ�չ��������������һ��Ҳ������Զ����ս����ֻ�ֲ��ᣬר�Ľ̻ʵ����֣����ٻʵ�˼����
�������֮սӰ�쵽�˻ʵ۵�ƽ���������Ľ���ȡ������Ϊѧϰ���������������Ϊ���г�һ��У�Ŀ����Ĵ����
���������Ӵ���û����������ڻʹ����������༫����ѱ����ƥ�����ܿ��������������ǰ����ֻ�Dz��ܳ۳ҡ�
��������Ƚ���ѧ��������������������ǿ�ܽ���ʸ�䵽���Ӹ�����
���������ѧϰ��һ���ô�����������ѫ���̴��ǵĽӴ������ˣ������ܽг������˵����֣�Ҳ�л���۲����ǵı��¡�
�������Ԥ�Եġ������Ӵ��ߡ���û���֣��̴��Ƕ��ܽ�������������������ȴ���ٿ���ʵۡ�
����ѧϰ����ĵ����죬�ʵ��붫�����ֶ���һ��������ݡ���ȭ���뵶����̫����Ȼ���Ļ��д̿ͣ����ϣ���ʵ����е��Ա�������
������ʦ���Ƕ���δ�����������ã��϶�ĸ��ָ�����װ��Ҳ�����˱����������Ϗء�
�������Ǵ�����������ϣ��������ҵ��������������ܹ��ش�������µ����⣺��ô��ύ�㷺�ĺ��ܣ�Ϊʲôֻ��̫�溫��������£�
��ʮ���¡�����
����ϰ�䳡����һ�䳤���ε����ӣ����ܰ����˱����ܣ���ǹ��ꪾ�ȫ�����Ƕ������εع̶��ڼ���������������������ʧ������һƬ��Ҫ��ֲ��������
��������̫��վ�����ţ��������Ŵ��СС�ĺ��ӣ���˵���ǻʵ۱���֮�������һ��Ҳû�õ�����������֪������װ�ľ�����ʲô��
������������ֻ�ж�������������ѫ���̴��������档
�����϶�վ����ԶһЩ������˵����һ�����˶��ɸ���Ϗظ���
���������ڶ�̫����棬�Ϗز��������ؾصع�ݣ�����֮��˵���������书�����̺�����֪����Ҫѧ��һ�֣���
�������������Ͻ�ʦ�����ɡ������������ȵõ������ѣ��ƺ�������������Ϊ��ʦ�������������ǡ���ʦ������һ���֣����������䣬��λҲ�в��죬��ʦ�������
���������������Թ��������õĿ�ͷ��������ӡ���䲻�ã���ʱ����������˵�ĺ�����ʲô�����Ƶġ���
�����Ϗص����ػص��������۾�ͨ����������IJ������֣����ֻ�Ǵ���һЩ���������²��ţ���������һ�㡣��
��������ѡ��ʦ��ͨ�İɡ��������Ӳ��ں�ѧʲô��
�����������ٺ�Ц�˼�������ǰ��������˵˵�㾫ͨʲô����
�����Ϗ�����ͷ����ȭ�������ڹ�����
���������Ǽ������ý�������û�����ù��������������ҿ��˿�������˵��ƾ���������������Ǽ�ʶһ�¡���
������̫���Ȼ����λ��ʦ���������书�����ֿ϶��Dz����ġ��������ӵ���
�����ʵ۵�Ȱ˵��������Ӽ�ּ�������̫��������֮�壬���¾þ���լ���Խ����ϵ������˽���٣������ϵ���ƭ����������������ʦ����Ȼѧ��һ�㣬�۹���еġ���
�����Ϗص�������ѧһ���Ľ������ԣ����ں�������Ⱥ��ף��ܵõ���������ָ�̣����²�ʤ���ҡ���
������ָ�̲���˵���Ҳ������ֵܷ���û������ɣ�����һ��ȭ����������
�����Ϗغ��˵������ط�����������������һ����������������һ������ͻȻ������ǰ����ȭ�����ˣ��ٴ�ǰ������ȭ�����ˣ�Ȼ��ͦ�������ۡ���������������
����������ʲô������������������ȵ�˵��
���������ǡ���ͦ��ġ���������Ҳû�����ŵ���
����������������뿴��ȭ���ȣ���Ǹ��������Ҳ��ᡣ���Ϗص����������������ˡ�
������������Ц�������ٿ�����Ľ�������
�������������ۣ��Ҿ���˼һ�°ɡ���
��������������һ�������ɼǵõ�����̫�����Ϗ������ս������Ρ�
�����Ϗ��ֺ��˼�����ͻȻ�����ڳ���һ�¿�Խ�߰˲��ľ��룬�ұ�һ��һ�������Ǵ̽��Ķ������������ˣ������ͻص�ԭλ������ͦ�������ۡ�������˵������ָ�̡���
��������������Щ�죬��ŭ��˵�������ڶ�����ɣ���
�����Ϗ�ҡҡͷ����������ǰ��˭����Ϸˣ�����µ�ȭ��������������ʵս������·����
����������˵������ڹ�����û����·�ˣ���
��������Ȼ����
�������������ĵ�ƲƲ�죬Ťͷ����̫��ͷĿ�������������Ͻ�ʦ�ı��£�û����ɣ���
����������û�������ӣ�Ц���������ɶ��浶��ǹ��������飬���������⡣��
����������������֪֮�������Ǿͺá��Ͻ�ʦ�������С������ҲС���������������ȥ�м����˽�����������ġ�ʵս�����¡���
����������Ҳ�����Ϗ�ͬ�����������ʵ۵��������ֱ�߳����䣬��һ�ᣬ��������̴Ӷ��н���������ල�����һ�����̣������˺ü��ۣ����������ԣ���û��������
�����������г��������һ���̴ӣ�����λ�DZ�Զ����ォ����ӡ�ĵ�������ʲô���ţ���
�����̴�����ʮ�߰�������꣬���ϻ�����������������ȴ��Ϊ��׳������Ҳ��ߣ�����վ���������һ��ԾԾ���Եľ�ͷ�����������������ơ���
���������Ӻ����ע������̴ӣ���ʱ��ס�������֣�ͬʱҲ�뿴���Ϗ��Dz������汾�¡�
�������������������ƣ�ָ���Ϗ�˵�������˵�ȭͷ�Ƚ�Ӳ����ȥ����һ���ѵ������֪���ʵ۵��书��ʦ���õ�����
��������Ȼ�DZ��µĽ�ʦ�������Ҳ��Ƕ��֡��������ƻ��������û�������ϳ���
������û�£��������棬����Ҳ�뿴��������������ʵۣ������ӵ���ͷ��
�������������ص�����һ�����������ӣ������ߵ��Ϗض��棬����Ļ����С��Ϊ��������һ���������Եü�Ϊ�˷ܣ��ڻʹ��ﵱ�̴��Ǹ����ĵIJ��£���Ҷ�ϣ���������ֿ���
�������Ͻ�ʦ��ͽ̡���������û�а���ڱ�ȭ���֣����ǽ�Ҫ�̳б�Զ���λ���ż����ӣ�û���ɶ�һ����ʦ̫������
�������Ź����������顣���Ϗص���
���������Ƴ������佫���ң���Сϰ�䣬��СȦ�����������������°���һ�����ƣ�����һ�ᣬ���Է�û�н�������˼�����һ��������ǰ����ȭ�ʹ�
�������ٲ�ȭ�����е�һȭ�������鴫�����Ϗر�˵�߶㣬�������Ʊ����岽���ϵľ��롣
�����ٲ�ȭ����ȭ����ȴ��Ϊ�������̹��������Ʋ��������Ͻ���˫ȭ�������磬����������֮�ӣ��Թ۵��̴����м�λ�̲�ס�кã�����ٶ���֮���ּ�æ���졣
����һ����һ���㣬�������˰�Ȧ�����������ͷ��ˣ������������Ͻ�ʦ���������ı����𣿹��ܲ����¿�ѧ��������
�����Ϗ�Ҳ���ù��ˣ��������ѵ������Ź��ӽ��С���
���������ɣ��������ƴ�����𣬰Ͳ��öԷ����С�
�����Ϗؼ�ûֹס�Ų���Ҳû�аڳ��κμ��ƣ�ǰһ�̻��������������һ���Ѿ��嵽�����ƻ������һȭ��Ѹ�ٺ��˵��߲����⣬ͦ�������������˪�����ں�����
���������ƽ������˫��������˫��һ��һ�£�����һ�ñ���紵����С����ͻȻ�³�һ����������һ�����ϣ����Ŷ��ӣ�����ֱ��������
����������³ç�����ֲ�֪���أ����Ź��Ӽ��¡����Ϗص�����ָ�������
����������������Ȼ���Ŷ��ӣ��������ҡ�μ��£�����������û�£��Ͻ�ʦ��ȭ�����ҡ��Ҹʰ��·硣��
�����̴��ǵľ���һ����תΪ���壬�������ط��ʣ�������ʲôȭ�������������˼������������������ĸ����ɵģ���������ʶ���»��������Ҽҵ���ʦ���ڽ����Ϻ���������
������������������̴��DZ��죬����������ͦ��������ȭ������������������ʦ������������
�������Ź��ӿ��������µ�ȭ������һ��һ��֮ȭ�����Ȳ����Ź��ӵİٲ�ȭ������������ǰն�����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