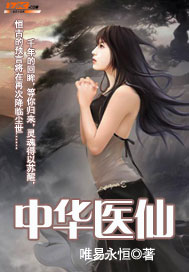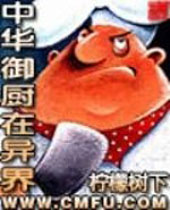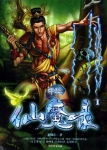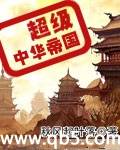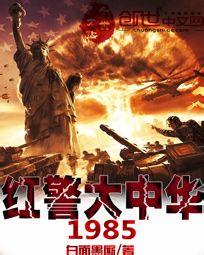Ѫ���л�-��1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еý��ż��ң��Է������갮����Ϊ�����ľ�����������½���ֳ��ٴ�ֱ�������ֳ��ٽ�������Ϊ�������ܶ���������������Ӧ��̨�������̨��������Ϯ����������˼��ҵ�����������̨���������ΰ����������½���ֳ��ٴ�ֱ�����ݻ��Ͻ���ս�ж����ȼ������Ʊ�������̨������¡����չ�����ģ��ɨ�����������������ΰ��ȶ��������Լ���������Ͷ�뵽̨��ս��֮����չ���µĹ��ƣ�Ȼ���������갮����ȴ����һ�����ַ������������Ϊ�Ͻ���ս�Ѿ�ȫ��չ����Ϊ��ռ�������ձ��ʾ��Ѿ������˺ܴ�Ĵ��ۣ���ô����֧���˵�һЩϮ��ɧ�žͰ�;�����أ���ʵ�ʾ������Ͻ���ɨ�����٣�ֻҪ��ֵ���������Ͷ��ս�����ⳡս����ʤ����һ�������ڴ��ձ��۹�����
Ϊ�˸��Ե����棬˫�����ּ���˭Ҳ�����ò���Ȼ������������û��û�˵ij������У���¡�����˶��Լ�������ӡ����ڽ֡�������ȵؼ���ͬʱ��Ϯ��ج����̴�����̨���ܶ�����ʨ�������������¾�Ϯ������ȫը�٣���¡ͨ��̨������Ҫ��ͨ���Ѹ�Ͼ�����¡�۾���ֿⷢ����ը����Ա��������ʧ���أ����˶�ú�����̱�̨��ֿ�����ը�٣����������ָ�����������ա��˲���������ǰҹ��������ӵ��ܱ�������ɱ���ܱ�����ʮ���ˣ��Kռ�I�����ׯ�������ġ��˲���������������������֣�Ϯ�����ܱ���פ������ʮ���ձ��ܱ�ȫ��Ϊ��ʾ��ң�ͬ�գ�ղ���ʲ��������ڽ֣����������ڽ��ϵ�һ���籨��·ά��վ���ܶ���ֱ��ͨѶ�жӵ�����ͨѶ����ɱ��ͬʱ���ж���̨������¡��ĵ籨ͨѶ�ߣ���һЩʱ������ɡ������Ϯ���˹���������Թ�����ɱ�����������ľ�����ʮ���ˣ��ٻ�������ǧ���
������������һ�����ѩƬ������ľ���籨������ƽ����������һ������ը�ף�ʹ��̨���ܶ���ɽ�ʼ͡��������갮�����Լ�½���ֳ��ٴ�ֱ�������ֳ��ٽ������ɵ��վ���̨�ĸ߲��Ա�ܵ����ޱ�ǿ�ҵ�����һ��ͷ��Ŀѣ֮����ɽ�ʼ�����������֧�Ǿ���ս����ͼ��Ȼ��֪������Σ��÷������Ѿ������ˣ�һ�ж��Ѿ�������ء�
��������ѻȸ��������ֱ���������갮����Ҳû���������۵����£����е��˶���Լ��ͬ�İ�Ŀ��Ͷ������ɽ�ʼͣ������صȴ����ܶ���̨�����˾����������ľ�����
�˿̵���ɽ�ʼ�ֻ���������д��������ݡ����ѡ���Լ���Ϊ̨��ĵ�һ���ܶ������м����˶������κ�ϣ������Ȼ���⼸���������������Ͻ��ж�����۽������ܴ��ۣ��������Ѿ�ռ���̨������Ҳ��������˴���©������������ʡ����Ե۹�ѽ����Ȼ�����Ͻ���ȡ�õ�ս����ȷʵ�������в��ʣ�����Ŀǰ�������������������̨�����еľ��ӣ���Ȼû��������ռ�����ĵֿ�����һ�ٵ�ƽ����˵ʨ���������Ͼ�����¡�۾���ֿⱻը���Ѿ�ʹ�ûʾ������Ͻ���ս������Ϊ�̣��ٴ���ȥҲֻ��������ȡ������ˡ���ɽ�ʼͰ���̾��һ�����������Σ���Ը����������
̧��ͷɨ����һ��������ˣ���ɽ�ʼͳ���˵������̨�������Ǵ��ձ��ʾ�����̨��ĸ����������ȶ��Ե۹�δ����̨�������������Ҫ��Ŀǰ��̨�����صı���ʮ�ֽ��ţ�����Ӧ��֧���˴���˷���ɧ�ź�Ϯ���������������в�����ձ��ʾ����������ա��ҽ��飬��ʱֹͣ�����ϵ���ս�����Ӹ�����ʱ��������������ı����������䲿����ر�̨֤�������ΰ����ȶ�����
��������һ���Ĭ�����˶�������ɽ�ʼ��ⷬ������˼����ʵ������ζ�Ŵ˴��Ͻ��ж����ٴ���������ɨ�����ӳ��أ�����̨��֮��������ؽ����¶Ͼ���û�������ʵ�ҩ�IJ������ڶ�����Ҳֻ�ܴ������ˡ�֮����û��ֱ�������ֻ�����Dz���̫ɨ���״����ܾ������ͷ������갮�����Ⱦ�����������Ӷ��ѡ�
10��6�գ��վ���̨����������ɨ������ȫ������̨�����ء�10��10�գ����״����ܾ������ʽ���ʦ�ż���·���в���Ȼ��������ڡ���̶��ȵس��ˡ��Դˣ��վ���������ĵڶ��������ж�����ʧ�ܸ��ա�
����ʮ���¡�����ʿ����ϧ
��������һ�����������������߳��˴��ա���ĿԶ����ֻ���ڲ���������ĺɫ֮�У����ڻƽ�ɽ���ϻ�β�뵺�����е���˳�ھ����Ѿ���ϡ�ɼ���
��˳��λ���ɶ��뵺���϶ˣ����ҹ���������Ȼ���ۣ�ս�Ե�λʮ����Ҫ��1602�꣬����������������ˮ����1714�꣬�峯�ٴ�����ˮʦӪ��1880�꣬����¾�����죬��������˳��Ӫ���������أ���֮���ر����Ż���
����ԯ�š�����ʻ������˳�ڣ��˿̴����еij˿ʹ�ӿ���˼װ�֮�ϣ���������������Ʈ�������������������ۡ���˳�������ϻ�β�뵺���죬��Ȼ�ط�Ϊ�������ģ������Ļ�����Ҫ���ڶ��ġ�������ƶ��ۣ����ϱ������Լ������������ӣ��øۿ�����һ�����أ�ֻ��������һ���ţ��Ա�������롣�����ڷ�ƽ�˾������ܵĵ̰�ȫ�ɴ�ʯ���ɣ�ƽ����ʵ���ɱ����ϣ���ģ������˳���룬�����õĹ�¯��������������ˮ��¯������ˮ��������ľ������ͭ������������������������Ƴ���������е���ϵIJֿ��Լ�����ʽ�Ĵ�����ͷһ���ſ����������ϡ�Ȼ��ֻҪϸϸ�۲죬һ���ޱ������ĸо������Ȼ���������������������Զ��һ����������Ϊ���Ƶĺ������أ����ȴֻʣ��һ���ռ��ӡ����롢��������ͷ��δ����ֻҪ���ܹ���ж�Ķ�������Ϥ��Ϊ�վ����ߣ�ֻ���ǹ�����Ĵ����š������ؼܡ���ˮ�����Ȼ�����ʾ�������յĺ�ΰ��Ի͡�
ӵ���ڷ������ӵ���Ⱥ�У��������Լ����������������߳��˴���ͷ�������ҷ��ڼ�ͷ�����幪��ѯ�ʵ�����ү�������Dz���������˳�Ҹ���ջЪһ�ޣ��������ٸ������ݣ���
����̧ͷ���˿���ɫ����ͷ���������˰���µĴ��ˣ�Ҳ�úú���Ϣһ���ˡ����쵽Ҳ������ȥ���ݣ�����������˳����Χתת����
�������Ͷ�����˵�Ż�����Ȼһ�����ʵ������ڶ������𣺡��Բ��𣬸��������������������𣿡�
����һ㶣��Լ��Ÿյ���˳����ô�ͻ����������Լ����˴α����ô��Լ���û��֪�����ѽ��̧����ȥ��ֻ��һ������ͦ�Ρ����ݿ��ʡ���ͨʿ�Ӵ�磬����ֹȴ�쳣���ų�����������������������Լ���Ҿ��ѯ��
�������е��ɻ�����һ���ֵ���������������ͨ�ż�ֱ���������ǡ�����
����������¶���˷������ĵIJ���Ц��һ���������������뻪�������ܹ��ü����������������������Ұ�����
����ν���˵���������Ӱ�������������������������ǹ��ˣ��˿�զһ֪����ǰ���ǫ������������˾����������¡���������������ô��ر������´뻪��Ҳ���ɵ�����һ��������¶���˲���֮ɫ��
��������������Ҫ˵���ڴ���������������緶Χ�ڣ��뻪Ҳ�ǵ�֮�������ȵ�����ɶ���ս���ݡ����䷨��ǿ�衷�������ô������Լ����¾��ɺ�Ԯ̨�����ش��վ���ÿһ�ζ������������ޱȵ��������������ֳ�Ϊ�����������г���Ƶ����ߵ������֡���������ƾ���뻪�������־��Ѿ��������е��˶����Ծ��ظ߿���һ�ۣ�������һ����˪Ѫ���ĥ�£��������������ʷ����˼���ı仯����ʹ��������վ�������������Ҳ������һ����������Ķ������ʡ�
��������������Ӧ���뻪�ٴι���������ʩ��һ�������쳣�Ͽҵ�˵��������������һ·�۳��Ͷ٣��뻪��Ϊ�����źó�����ס��֮��������������������³ç֮����Ҫ���֣�����
��������������������������һ�о����ͷ뽫���ˣ���������Ȼ��Щ����������������м�ڰ���Ȩ��ȴ���Dz�ͨ����֮�ˡ���˵�뻪��һ�ε�������Ϊ�Լ���ǰ�����ֳ�����ǫ��ƽ�͡�������飬��ʹ�������Է뻪ʮ�־��кøС����£���ֻ������ԥ��һ�£���ˬ��ص�ͷӦ����������
��������ũ�ң����IJ��ų���16�꼴����ţ����Ƴ�ȴ����˳����ֱ��1894����41��ʱ���ŵ���״Ԫ������֮ǰ�����ڵ������ͳ���ⳤ���Ļ�ţ�����1882�곯����������б��ֳ����ķǷ��Ÿɣ��Լ��º����⡶�����ƺ����ߡ��������綫�����ԡ�������ʱ�渴���ߡ������£�ʹ֮һʱ������ȵ��ȫ������һ���Ķ�����Ȩ��һʱ���س�������������Ļ��Ȼ�����ز��С��ɱ�������֮ͽ��������ȴһһ���Ծܾ���
1894�꣬��������״Ԫ֮���������ս�ս����֮ʱ���ǻ�����֮�У������Զ�ʱ�ֵ�����۲���˵ĵ�ʶ����ð���Ծ���;����Σ�գ����鵯������Ҫ�������£��䵨�����ķ��ٴ�Ӯ�������˵Ľ��ڳ��ޡ�1895�꣬�������ڸ���ȥ���������ϼ���ͨ���ơ��ڻؼ������ڼ䣬���ڼ���ս�ܵĴ̼����Թ���ǰ;����ã�Լ�ɥ���ı�����ʹ�������������ܻ�֮������Ҳ����������;�Ϲ��ҳ�����ֻԸ��һֻ����Ұ�Եġ��������ķ����ⰿ�衣���������������Ѳ�Ը���ܹٳ���������ȴҲ�����ľʹ������ּ�Ȫ�£��Լ���һ����ѧ����ҲҪ����һ��һ��������֮�������������������ľ��£�����ӭ���˷뻪�����������������ܶ�����һ�ܷ뻪����������ͨ��������ǰ���ô��ر�����ְ��
�뻪��������������������������������Ȼ���ո��¶����IJ��ٳ��ˣ����˴������Լ�����Ψһ���˸е����������ϣ���ķ뻪���Լ���ǰ���Ǹ������Dz��ǻ�Ҫ������֣����������Ҳֻ��Ϊ�뻪���ڴ�����������֮�ʣ���ճ�����һԱ������������Ȼ��Ҳ�����¾����ɶ��ļ�����ʤ��ܲ��ѣ�����û�жԷ뻪�ر���Թ�ע�������ڽ���������������䷨��ǿ�衷�Լ��ô��ر���������ȴ�������е��˼�������裬�뻪��һЩ�뷨�������Լ���ı���ϣ����һ�������۵�ʮ����ӱ�ͷ�����ʡ��
�������뻪���������е���������Ļ�����������Щ�����¾�ǧ���������ɺ�Ԯ̨��չ�ֳ�����Ȼ������������Ķ�����������һ�����о������֮�ţ�����Ϊ��Ϊ��֮�ĵġ���֮Ӣ�ܡ����Լ������ú�ȥ�δӣ��������ǣ��������ھ����ȵ��ô�����������Ȼ���پ����Լ�����ȥ����ֻ��������û�뵽���Լ�������˳�ھͱ��뻪֪̽�����٣�һ�½���ԭ���ļƻ��Ͱ���ȫ�����ҡ�
�������������Ž��뵽��˳���У���������סΪ��ǰ�ľ����ˡ���ʱ���Ѿ��롰��˳����ɱ������һ�꣬����˳ͨ��ȴ����һƬ��ԫ�ϱڡ���Ŀ����������������������ȣ��쳣���壬���վ��ڻ�����ĺۼ��ȱȽ��ǣ�̮���ķ��ݣ������IJݵķ��棬������ôҲ����������DZ�����������Ϊ������������֮һ����˳�ڡ�
����ˮһ���̾ŵ㣬׳�մ˵�ʵ���ա���̨�����绢�ۣ����´�����ٲ�������ݳ��о���������ҹ��������߷�ͷ��Զ�����������ӭ���s��������Ħͼһࢣ����������ղ��ҡ�νɽ�ɺ�������ŵ��о�������������������һ�����������Ȼһ̾�����˿��ٶ��ƹ��ȣ������ܣ��ֹ��ȣ������ס�����˳�������з��ű��л���������д������˳�ڵ�ʢ˥�����衣�������л���ʱ����һѩǰ�ܣ��������ѽ����
�������ԣ������������Եķ뻪�����ϵ�����Ҳ��ٿȻһ��������Ĭ��һС������������ޱȳ��ص�Ӧ��������ʵ�����˳����ò�������¾��ս�����ʱ����Ѿ��������࣬�������������������Ա��з����������������������˳����ɱ����ʱ����˳ʬ����ɽ��Ѫ���ɺӣ������ǻ��Ѫ�����������棬��ʹ���춼Ϊ֮���ᣬ����Ϊ֮�������˳���������Թ��ˣ��˳ܲ�ѩ�����������л�����
��������ס�ˣ��ӷ뻪�쳣��ʹ�Ļ������У����о��ó�����һ������ȷȷʵʵ���Էθ����뻪�ǿ����л������Ը�������ǿ�ң��������Լ����ĺ�Ҳ���Ծ���������������������Ļ��ﵴ��������ij����ȡ���
��ҹ��������壬����է�����ɪ��粻ͣ��ҡҷ����֦����֦ͷ�ǿ�ʼ��Ƶ���ҶһƬƬ���䡣����һƬ��һƬ������з���Ʈ��Ļ�Ҷ��������������ͷ������һ˿�Թ����˼���������������Ҳֻ���������ţ��ܿ�����˼�����ٴλص��˸ղ���뻪���Ƿ����������Լ��е��˷ܵi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