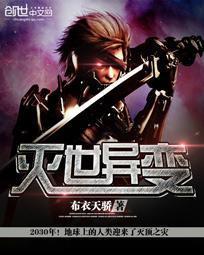清山变-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能是席间多喝了几杯水酒,郑祖琛花白发根的额头满是汗水淋漓,在曾国藩看来一阵心疼:“而与其等到皇上在此事上为臣下为难,不如我自己上一道表章,就此致仕。也落得个全身而退。”
曾国藩一皱眉,心中虽不以为然,却也知道,他说得并非无理,出了这样一大件事,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是说不过去的:“那么,老前辈的本章,准备什么时候上?”
“这且不急,总要把此事安顿下来之后再说。”他转头望着曾国藩,继续说道:“倒是涤生兄你,我们虽同是在朝为官,却彼此从未得见,这一次有缘相会,又是同时办理这开国第一件大案,老夫有几句话……”
“啊,是,请老前辈赐教。”
“就如你刚才所说,便是有皇上恩宠,为人臣子者,却也当谨饬自守,万万不可做恃宠而骄之事,否则,不但恩宠必减,便是身家性命,也难以保全。涤生兄饱读诗书,不要说纵观青史,列列在前,便是本朝的年大将军,前车之鉴,不可不慎啊!”
“是!晚生记下了。”曾国藩真是心存感激,郑祖琛和自己说这样的话,便真的是拿自己当做近人。要知道,这样的说话传到皇帝耳朵中,一个大不敬的罪名是怎么也跑不掉的!当下很郑重的点点头:”还请梦白公教诲!“
“还有一事:托梦之说,老夫心中大不以为然,虽然此事在桂省有了确证,也难以打消老夫心中疑窦。”郑祖琛慢吞吞的捋着短髯:“皇上纵是天纵之资,也绝无可能知晓万里之外的桂省金田县之事!是而老夫心中实在存疑。”
其时已是六月中旬,广西地处西南,巡抚衙门的后花园中,明朗的月光下树影婆娑,偶有几只蛙鸣之声,更是增添几分惬意,而主客之间的话题却全无半分轻松之氛围,反倒于这景致格格不入,只听郑祖琛继续说道:“这且不去说他,涤生兄,皇上新君登基,自然要有一番作为,从陈孚恩之事可以看到,朝中那些只知磕头,琐屑龌龊的大佬,怕是很快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了。朝中很快就会有一番新气象,到时候,涤生兄,可就是你大展宏图之机啊!”
曾国藩恭恭敬敬的站起来,一躬到底:“谨受教!”
“说不上什么受教了。”郑祖琛很谦虚的摇摇头,他说:“不过是有些老马识途的阅历,能祝涤生兄一展冀足,便于愿足矣。”
曾国藩自然更要客气几句:“不敢当,老前辈的话,涤生越发的不敢当了!”
郑祖琛笑着摇摇头,似乎不以为然,却没有纠缠下去,而是换了个话题:“涤生,你对时局如何看待?”
“文风不振,大为可虑啊。”彼此都是读书人,又是一朝为官,说起这样的话题自然有着相同的观点:“文运关乎国运,我真是搞不明白,何以会弄成今天这样萎靡琐屑,寻章摘句,不务实的文风!”
“还不是曹文正?”郑祖琛一来是今天晚上有了酒,二来和曾国藩在这数月相处之中,也真的是对他很高看了几眼,当下也不吝一敞心扉:“当然,也不能只怪曹文正一个人。”
“您认为还能怪谁?”
郑祖琛昏黄的眼睛在灯下很是奇怪的瞟了他一眼,似乎很惊讶他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只不过身为人臣,决不能臧否先皇,只得低头不语。
他当然知道‘还能怪谁’!曹振镛中下之才,死后居然得谥一个‘正’字,怕是除了道光皇帝和曹振镛的家人,无人不认为是不合理的!只是事涉先皇,干系重大,从来没有人敢于谈及而已。至于曹振镛的后辈,便是今日军机首辅的穆彰阿,和曾国藩有师弟之谊,又有相携之恩,便更加不可谈了。
曾国藩也是下意识的一问,也猜到了老前辈沉默的原因,心中有些愧疚,当下只得改变话题:“老前辈于地方多年,可有以教我?”
“老夫在广西任上多年,据我看来,现今最大的问题就是侈然自大,全不知外务。道光三年以前,银子流入外洋,每年不过数百万两;三年至十一年,已增至一千七八百万,而现今,每年漏银已超两千万之数,可知鸦片输入亦在逐年增加。朝廷立新例,置重典,原也无可厚非,只是奸商蠹吏,滔滔皆是,阳奉阴违,如之奈何?”
“若以前辈之见呢?”
“老夫倒是赞同某些通达之士的主张。闭国不可,徒法不行,倒不如寓禁于征,课以重税,且以货易货,不准以银购买。至于吸食者课刑,也要分清楚轻重缓急,专重官员,士子,兵丁,渐次于庶民,庶乎有济。”
曾国藩猛的一拍扶手,大声说道:“梦白公所言发人深省,若是能够上表皇上,朝廷也真能够顺应而行,怕用不到二十年,不,用不到十年光景,我大清就能够再现汉武雄风了!”
郑祖琛摇摇满是花白发根的头颅,把话题又扯了回来:“涤生啊,虽然现在文风不振,但是讲实学的却也很多,这也是盱衡时局,堪以自慰的一个好现象。我大清现在虽然是内忧外患方兴未艾,但是总还不至于危及社稷。”
“以国藩看来,这便是国家养士之报了。”曾国藩点点头,说道:“佛家讲生老病死,也通乎古今兴衰存亡之理。便如同前明。武宗童沂无知,宸濠窥窃神器,幸有王阳明出现,方转危为安。这便是前数代养士之报。梦白公以为今后纵有忧患,还不致危及社稷,想来也是因为本朝仁泽甚厚之故吧?”
郑祖琛简直要为曾国藩的说话击节叫好了。遗憾是身边无酒,否则的话,对着一个能够说到一处的同僚,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怕都不能形容,这大约就是淳于髡所说的‘饮可八斗’的最高境界了吧?
************
老家人有田的一声呼喊让曾国藩从回忆中清醒过来:“老爷,我们到省了呢!”
第49节 万千之喜
新君登基,曾国藩以一篇《奏议大礼疏》得皇上青眼有加,简在帝侧,朝夕相对。这一次是以钦差身份赴桂省查案,差事办得漂漂亮亮,又奉旨回乡探亲,也是朝中很少有的恩遇。天下人都知道,曾国藩这一次探亲结束返回北京受皇帝重用是指日可待之事——这时候不趁机打好关系更待何时?
于是,自从他进入湘省地界,便有沿途各地府县长官前来迎送,一次次的庸酬之事也不必一一细表。终于,在六月二十九日的时候,一乘小轿穿过湘潭县城,顺着官道直奔荷花塘曾氏祖宅而来。
早就有守候在官道上的家人注意到了小轿的出现,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男子和同伴低语了几句,迎着队伍走了过来:“敢问,可是来自广西的礼部右侍郎……”
轿中的曾国藩听见的外面的声音,赶忙跺了下脚,轿夫停稳,后者不等人撩开轿帘,就自己钻了出来:“澄侯?”
“啊!”被他称为澄侯的男人正是二弟曾国潢,兄弟两个倒有十来年的时间没有见过了。曾国潢上前一步,突然想起对方虽然是自己的兄长,更加是国家的命官,便又站住了,脸上很是难堪的一笑:“大兄!”
曾国藩可顾不得什么官员仪体,抢上几步拉过弟弟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二弟,你还好吗?”
“我很好。大兄,我很好。”
看着二弟表情很有点尴尬和疏远,曾国藩心中好不是滋味。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在京中为官,算是朝廷的人。自然的,在家乡这边,也就由二弟担负起了在父母膝前尽孝的重责。想到这里,曾国藩忽然双手抱拳,深施一礼:“大兄!您这是何意?”
“二弟,这些年来,为兄人在京中,全仗二弟代我在二老膝前尽孝,为兄我,这里多谢了!”
“大兄,切莫如此,切莫……如此!”曾国潢眼圈一红,声音中有一点哽咽:“快点,大兄,快点上轿,爹娘都在倚门而盼呢!”
“啊!”曾国藩这才想起来,赶忙追问了一句:“二弟,爹娘的身体可还康健?”
“康健,康健得很,只是听说大兄这一次奉旨办差可以原籍探亲,阿娘高兴的一夜没睡,这几天没有什么精神。”曾国潢第二次催促:“大兄,快点上轿吧。”
曾国藩有心和弟弟一路走去,又恨不得尽快赶回家中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父母兄弟,只得低头钻进轿中。这边,曾国潢赶忙打发下人先期快步返家,告诉老爷和夫人,多年未见的长子回来了!而自己,则跟在轿子的旁边,向荷叶塘而去。
路上无话,距离荷叶塘白杨坪还有一点距离的时候,轿子停了下来,曾国藩和弟弟并肩而行,远远的看见祖宅的门口站着一大群人,为首的二老,正是老父曾麟书与母亲江氏夫人。
曾国藩顾不得旁的,尽可能的加快脚步,冲到父母跟前,撩起衣服的下摆,重重地的跪了下去,再说话时,已经带上了哭腔:“不孝儿国藩,给父亲母亲请安!”
曾麟书和妻子看着这个最有出息的儿子跪在脚下,老夫妻的眼圈同时都红了起来:“起来,宽一,起来。”老夫人叫着儿子的乳名,在他的背上轻轻地拍打了几下:“让阿娘看看。”
“是!”曾国藩听话的爬起身,微微蹲下一点身体,任由母亲的手在自己头顶,脸上划过:“唔,我的宽一也老了。”
“阿娘。”看着父亲母亲已经白发满头,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怜惜和思念,已经年届不惑的男人的泪水夺眶而出!身体再一次跪了下去:“阿爹,阿娘,孩儿不孝……”
“说什么不孝的话?你是朝廷的人,忠于皇上便是天下第一大孝!若是整天绕在父母膝前,却不能为国家建功,那才是不孝呢!”江氏夫人重重的在儿子头上拍了一下:“这是连我这目不识丁的无知之人都知道的道理,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是!阿娘教训的是,是孩儿糊涂了。”
“好了,孩子好难回来一次,何苦见面就训斥儿子?”一直含泪望着这曾家骄傲的老父亲这时候终于插话了:“天气太热,还不让孩子进屋?”
曾国藩顺势起身,搀扶着母亲,由曾国潢搀扶着父亲,一家人走入高高的挂起了红灯笼的曾氏祖宅。
在内堂换过衣服出来,在祖宅的正厅里二老端坐,曾国藩再一次拜倒,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爹、娘,孩子回来了!”
“起来,起来说话。”这一会儿,经过刚才在门口的激动,彼此都冷静了很多。曾麟书示意儿子站起来入座,满脸带笑的看着他:“这一次从听到你可以顺路回来探亲的圣旨那一天起,你阿娘日夜期盼,就盼着你能够早一天回到家中。”
“是啊,听说大兄这一次办差途中能够回乡探亲,阿娘可高兴得不得了呢!”坐在一边的四弟曾国荃大声接口:“还是二嫂连夜起来相劝,阿娘才肯睡下的呢!”
曾国藩难得的开心一笑,抬头望向母亲:“阿娘不必为儿子牵挂,还是保重身体为重。”
“没什么,没什么的。”老夫人掩饰不住的笑意溢于言表:“家媳还好吗?孙儿孙女还好吗?”
“是!母亲,他们都……”他的话只说到这里,门口突然传来一声高声呼喝:“有旨到!”
曾国藩一愣,中断和家人的叙话,迎了出去。外面一乘八人抬的蓝呢子大轿稳稳当当的停下,一个年级在五十岁左右,翅绫辉煌,身着二品锦鸡补服官服的老者手托黄卷正在下人的引领下步入正厅,正是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有旨意,着曾国藩接旨!”
“是!”曾麟书也站了起来,命人排摆香案,又把骆秉章迎入大厅落座,这一边曾国藩闪入后堂,在听差的伺候下换上官服,朝珠补褂穿戴整齐的走出,在香案前跪倒,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臣,曾国藩接旨。”
骆秉章面南而立,展开手中黄卷:“……曾国藩于桂省督捕邪教匪逆之事,厥劳甚伟,功勋在在,甚慰朕心!曾国藩着改调户部左侍郎,在军机处学习行走,位列周祖培之下。”
“又:两湖、江南一地乃我大清人文荟萃,天下英才齐集之所。丘壑之间必有大才隐没,着曾国藩于旨到之日,细细查访,待回京之后报与朕知。万使朕野无遗贤之志通达为盼,钦此!”
“臣曾国藩,领旨,谢恩!”
骆秉章收起黄卷,等他站起双手递过,笑眯眯的一拱手:“恭喜涤生兄啊,这一次入军机行走,将来入阁拜相,指日可待矣!”
“多谢骆大人善颂善祷。只恐国藩绠短汲深,菲材何堪当此重任?不过是在几位中堂坐前以供趋走而已。”
第50节 夜不能寐
骆秉章到访传旨,自然也就打断了曾国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