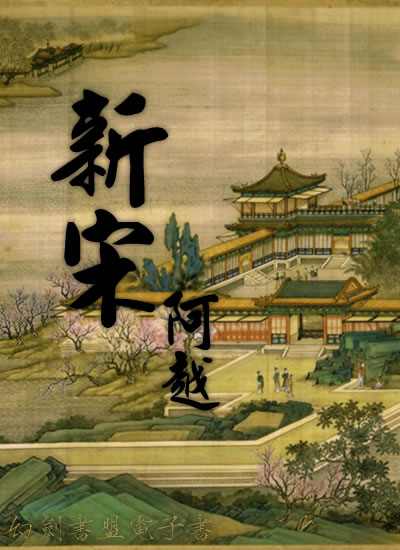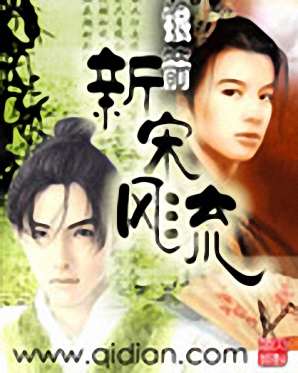����-��4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Ÿ����µ����ġ���ʵ�ϵ�Ȼ��������������֪����������dz�Ǯ�����ˡ����ű�����������̸����ʵ�롰��ʵ���������Զ���γ���Ա���������䣬нٺ�������ź���Ա�Dz���Ҫ���Һ��ڣ���Ҫ�е�����Ľ���Ӧ�꣬Ӧ�������������������ϵ�ʱ�������Ũ�ܶ��Ա����ʱ������������ķ��֣�����֮��Ҳ����Ҫ�������壬�����ͳ�Ǯ���ڼ��彨����֣��˰�ѧУ������ʹ���и���Ա����Ϊ��������Ҳ���벻����������������֣��ոս���Ϊ�м����δ�õģ���Ȼ��֮�����Ѳ���ͬ�ն������ʵҲ���ǿ��������꾩��һ������լԺ���ѡ�������꣬������Խ����Ҳ��Խ�Ȳ��ҿ˿۾��ã��ֲ���˽�Ի��ף���û��������ʲô���ѣ���Ҫ�������������ܼã���Ȼ��������þ��ģ���Ǯ����ȴ��ע��������̫�ĵġ������ȴ�������������ʱ���������֪��������ϣ���Ȼ��ɳ���ˡ������������Ϊ��ֱ������Ϊ��Ϊ��������ˬ���������Ⱥ�������ս����������˼������һ���ıڹ���լԺ��������������Ů���������ֶ�ӡ�һ��ֶŮ���˸�С��Ҫ�����⣬Ҳ����ö����졣��ת�ξ����٣������в����ѵ�ԭ�������Ȼ����ٵĻ�����٣���������ٺ»����ͨ����Ҫ�ź�Щ�������ҵľ�������С�����ⷬ���ᣬ������ʵ��һ���ش��������ƽ���ھ�ʦ�����ѣ���ᶼ���ԶԶ�ģ���Ҳ����¶�档�������Dz�ͷ��������Ȼ֪��û���̲��ı����Ĺ�Ա����·�ϻ���ʲô���ľ�������֮������־������������ܷ��β�����û�κ��£���ֻ�ö�ƴ���գ���������O·���밲�ҷѡ���Ҳ����ȥ��ʯԽ���ƿ����ع���Щ�ˣ���������ڿ��⸮�������м䣬�����е������ģ���������Ȼ����ù���ڼ����ã����Ͼ����СС���Ǹ���٣���Щ���۲���Ҳ��������������������ô������һ�˼����ļ���Ĵգ���Ӳ�����Ǵ��������Ǯ��
�����������֮������������������£�ÿ�����ȥ��������˾��î�⣬�����������꾩�����й䣬ÿ�����ڲ�ݺȲ�������ֱ����һ�죬���ڳ��������Žָ���������һ����ģ���ġ���¥�����
�����ڴ�֮ǰ�������䲢��֪������¥�������������ʮ�����ʱ���Ѿ�������ˮ̶ͼ��ݣ���Ϊ�꾩���������������Ĺ���ͼ��ݡ�
������ɣ�����һ���Ĵ�֮�£���ʹ��ս�����ϵ�����£��γ���͢�ڹ��������ϵĿ�֧��Ҳ�����������ġ�����Ȼ�����Ӵ�ľ��ѿ�֧��������ֵһ����Ͼ�Ҳ���ڽ�������������ʮ���꣬Ӣ�����ŵ�ŷ���������������ʶ���ʡ��ĸ�������ٸ�Ӧ��Ҫȫ�����ʶ���˿ڵı��ʡ���ŷ����ȥ��֮��ɣ�������ñ�̳���������־��ɣ����ڡ�������˾���У�����֮��Ϊ������Ȼ֮��������������ж����������Щ�����������ѧ��ϵ�С������ķ��롣��Щ�Ĵ�����ʵ����������ʮ�������͢���ǹɷ��Լ���ս��������������Ϣ��������������ӭ����ƽ������֮������������ս������������ѹ��֮�£������õ�һ�������������ո��������뺣�����������·�����ݵ�ʶ��������ͯ��ѧ�ʡ�
��������Ľ����Ȼ�������ֹۡ�Ҫ֪��������һ��ʱ���У�ʮ���������ڣ���ǿ����ʶ�ֵ�������ײ��С���������ٷ�֮ʮ����д�ֵĸ��ͣ���������һ�˰�һ��ʵʩ�����������ʵ�ʾ�ѧ�ʾ�ֻ�п����İٷ�֮һ���ģ������һǧ������ʵ�����Խ���Ϊ����֮���ĸ������ε����������������ô�ҵ�����Ҳ�㹻��⡣
����ʶ���ʷ��棬�꾩����ߵģ�ȴҲ�����չ����ɣ�����Ǻ��ݡ�������ɶ�����ijЩ����������ֻ�п����İٷ�֮һ��ȫ��ƽ��ʶ����Լ�ٷ�֮��ʮ������Խע��������Ϊ���й��Ŵ�ʶ���������Ϊ�γ�֮���ɣ�����ĩ����Ϊ���ɡ�С˵��ȡ�ϱ���֮���ݡ����ڻ���������ν���ţ���һЦ���ӡ�С˵���ԣ����ص��档Ω�Ŵ�����ʶ����Զ�����������Բ����ԡ�����ʱ��֮�ձ���19������Ļĩʱ�ڣ�����ײ����Ӵ�����ģ�Ů�Ӵ���ɣ���ʿ�ײ�ٷ�֮�١�ͬ����1920�꣬�ձ���ͯ��ѧ�ʴ�ų����ϣ�Ī˹��ȴ������ɡ���������ͯ��ѧ�ʣ��ԡ���ѧУگ���䲼�Ժ��Ǵ��к�ת�����꾩����ɣ���������Ŭ������֮�������ӽ��£���ѧ�ʾ��ߴ������塣�����˳Ծ����ǣ���ͯ��ѧ����ߵij���ȴ�Ǻ��ݡ���������ҵ�ķ�����ϵ�ѧ��Ũ���⣬Ҳ��Ϊ�����ּ���ѧУ�Լ�����ѧ�õĴ��ڣ�ʹ�����ѧ�ʾ�Ȼ�ﵽ���˵��߳ɡ�������ֻ�Ǽ������ķ�������������ȫ����Χ�ڣ�ƽ����ѧ������ijɡ�
�������ֻ������ã�������������Ȼ��Ϊ�����������ڲ����Ǹ������ѿ���ƽ�����ֺ���ģ��Ǹ�Ϊ�ѿ��ĵ������������ݲ��졣��������꾩���⣬������ʶ���ʻ��Ǿ�ѧ�ʣ��Ϸ���ԶԶ���ڱ����������˸�����ʶ������͵�һ���ײ㣬��ٵ�ʶ���ʶ�ֻ�п�����һ�ɣ�����ȫ��ƽ��ˮһ�룡�����������Ӫ����ξ�µĸ����������������桱�����ݡ�
����������������£��������ò���ȡһЩ��ʩ����Ӧ��������������Ӵ�Թ���ͼ��ݵ�Ͷ�룬���ڽ���ѧ����ѵ����������Ƚ����ȵȴ�ʩ����������Ӧ�������IJ�����ȷ��һ�μ����ת�䣬������ʮ����ǰ�����������˵�������Ҫʶ�����������������ڣ�������Ӫ�Ľڼ��ǣ�����ѧϰ�����뼸�Ρ�
�������������Щ��������ȫ��֪�飬��Ժ������¶���ĥ���뿼�������У���ȷ��ʶ�ֵ��������������������Щ��������Ӱ������������Щ������һֱ�ڴ��̣������Ǿ���ս����ʲôĥ�����Σ��������������������Щ�������������Ծ�������Լ��İ���������������Ͼʱ��Ҫ�����ϰ�ߡ����ͻȻ�������ģ������¥��������е�ϲ�����⣬�Ӵ�ÿ�����м���ʱ����Ҫ��ĥ�����
�����������Ӳ���������ؽ赽��һ������ѧԺ����ġ�ı����˵���������ȷ�Ƿdz������棬�ⲿ�����˵ľ����������ڴ����ܵ��˲����������ӣ�����ѧԺ����������鼮����������Ϣ�ģ���Ϣ�ģ�ָ���Dz�˹�ģ�����Ĵ�ʳ�ģ�ָ���ǰ������ġ�������ʳ�İ汾ת�룬ֱ������ʮ����Ϊֹ�������ķ�Χ��Ҳ��Ҫ���ڴ��εĸ���ѧԺ�����ѧ�����Ķ���Ϊ������Ҫ�ܵ�ѧ���벩��ѧ�ҵĻ�ӭ����ʱ�ĸ���ѧ��������������֮���������е���ר��ij��֮ѧ�ߴ��ڣ�����ӡˢ֮������һ��Ҳֻ�Ǽ��ٲᣬֻ�м�������Ʒ�Ż���ܻ�ӭ��ӡ������ǧ�ᡪ�����ⲿ��ı����˵������һ��������սʷ��������ϣ��ս��ʷ����������Ȼ�������ܵ���Щѧ�ߵĻ�ӭ���õ�ʯԽ�����������ѧԺ�����뾭¥������������������Ŀ�ģ���ϣ���ܸ���У���̲ģ����Ͼ�У�����ٸ������������÷���һ�䡰����Ҳ��д���飿���㽫�������鶪������Ͱ������Ҳ�ķ���������ʽ�����Ѫ����������������飬���Էֱ������ʮ�����ҵ��ճ���ֻ����õIJ������ר�ŵIJ��������ſ��������������겻�����յ�̩��������������¥������ղ��ⲿ��ı����˵���Ѿ���һ�����ʷ�������¼�����Ǹ����һ�α����ġ�
������������Ϊ���������Ӳ������ؿ����κ��ˡ���������̩�����˵���Ʒ����Ҳ���ſ����۽����̬����Ϊ�˼Ҽ�Ȼд�ó��飬�DZ��ܱ��Լ�������ϴ�Ҫǿ�ϼ��֣����п�ѧ֮������˵�Ҳ���˸߲��ҵ�����������úö��������ϸո��߳�����¥���㱻ӭ��������һ���˽�ס������λ�������������ォ������
���������һ�£��������˰��Σ�ȴ�������ϲ��ô��ˡ��������Ծ�������˼����æ��ȭ��Ǹ��һ���ʵ�����ˡ��ʧ��֪������γƺ�����
�������˲��Ű���������꾩�ٻ�Ц������������ð���Ŷԡ��ォ��ԭ���㲻�ϵ��ҡ�������ʱ�ң�ԭ���������ϡ�����������ʱ����������������һ�档��
������������Ż�Ȼ��Ц������ԭ����ˡ�������ô�����꾩����
������ʱ��Ц��������͢�ո���������±�ټ�Ǩ��������ء��ⷬ����DZ�Ķ��飬������������ɹ���ҫ�档��
����������֪�������ټұ�Ǩ��������������ס�ģ������ıض���һʱ֮��ǿ���������ԣ�ֻ�»��Ǵ���Ҳδ��֪����ʱ���Ĺ����뿪�����ߣ���Ϊ�Թ��߳��⣬��ͨ�����г��˲�������ȻͶ�����У������γ������⣬���൱һ������־�������������������������Щ����������������䣬��ҵ����䡣���˾�Ȼ�д�����׳־����Ҫ���꾩����������������Ҳ�������塣�����������ֵ������Ǹ��������صĴ��ɷ�
���������������ˡ�����ʱ����æǫ��������ȴ�Ǽ����ˡ���Щ���ľ��ˣ������ǵ�����ˣ����꾩������ٶ������ܵ����ӣ����ͷһ��������˳Ͽҵع���������������������ϣ��������κ�����֮�⡣�����˿�������������飬�е�н���Ц�������벻������ԭ������˫ȫ����
�������������Dz�֪���ٴ������ø��ָ���������˵��������˫ȫ�������������ˣ����ѵ���һ������ʱ�����ijϿң��������е��ݵ�ζ�����������һЦ��������ʱ�����ﱧ�ŵ��飬������һ������Ȼ���ǡ�������˾����
��������ʵ�Dz��ƽ��ʵġ���ʱ��û���һ���Ц����������ɣ���ӵ���ô����
���������ǡ�����ʱ����Ϊ������Ҳ�����Ȿ�飬Խ����������������ͷ��һ�������ɣɽ��������Ҳ����˵��͢Ҫ����ɣɽ���������Ϊ������ֱ����ʥ�˻�ר���������̳���Ѱ��λ�������飬����˵ʥ�˿��˺����dz���������������ˣ�����������ʵ�顭����
������ʺ���Dz���̣��ڷ��䵽������ɣ���̵�����������������Ҳ�����˵�ˡ�����Ȼ������������ʺ����͢�����һ����Ȼ�İ�ʾ����ɣ���̶��˵��鼮���꾩�κ�һ����궼������ȫ���õ�����Щ���̶�������ô�������������������и������ƽ�ϣ���ȻҲ��������ɣ����һ���ġ���ʱ������ʱ�����²�����˵������ɣ�������õ�������羴�����Ȳ�����˼����������£���ֻ�����ĵ��ڲ�������澲���������š�
�����꾩����¥��֡���ʱ��ʱ����������ʮ����İ�����Ѯ��������������һ����Լ�˼������ѣ������¥���žơ���Ȼ�ֱ������⸱ξ�����γ�������ʿ����һ���ź���⸱ξ�����Ǹ�����Ʒ����٣���ʹ�¹��ƹ涨��û����ʵ�ʵIJ�Dz��нٺ�㼸��Ҫ���һ�룬��ֻҪ�����ݳ�������꾩���ж��գ���Ȼ�������⡣���ο�����ʹ�������䡰������֮����ҵ�Ů����Ҳ���DZ������Ͷ���ϰ�ߣ��Ӽ����Ů���˵�ʹ���Ů�������һЩ�Ӵ�����������ְ�������������������á��������ļ�ͥ��ֻҪ���Ҳ�������Ķ������Ƕϲ���������ġ�ֻ�����������������ģ��������ƺ���һ��������������ϲ������Ȼ�տ�ʼ������ʱ���о��Ǻþ�û�й��������밲������ʱ��һ���������û���ɵķ�������������ʱ������ǰ���йص���Ϣ��������ܴ�������
���������ֿ�����˵�ˣ�С������Ľ�ݽ����������絽��ʦ�ˡ�����ʱ��һ������һ���Ȳ�������˵���������Դ�����¥������ʶ��û���ռ䣬���ѳ��ֵ��ܡ�
������������������ƽ���ˡ���һ�ԵĿ��⸮Ѳ���´���һ����žƣ�һ��Ц�����´����Ǹ���׳���������ӣ����ź�ɫ����������ӣ��������DZ����á��������ݣ����������Ա�ĬĬ�ԾƵ����ܣ�ȴ���ְ����֣�����ʮ�ֵ�������䴩�Ŵ�磬�������´��еĸ��࣬���е���Я���ϵ���˼����������ȴ֪�����˼�����һ�����´����ǿͻ�������������ֲ��ϵü����������ܼ�ȴ�ǵ��ص��������壬Ҳ������ʮ������顣ֻ�����ij�����ò�Ŀ������γ��ڲ����ĵĹ����ϣ���Ȼ�������ƴ���һЩ�ŷ磬������������ò�е�Ӱ�����ݵ��ˣ��ȿ����Ͼ��ӣ�����ı�������ԡ����⡱����Ҳ�����ܵ����ӣ�ֻ�ñ�������ѧ�䡣
����������ԭ��������ԭ���ϣ�ʯԽ��μ����Ϯ���˽�ӦļΪʯԽ˧�����ױ�������������ݾ��飬����˧˾��ȫ�����μ�������֮ս����������ĩ�ڣ�ƽ���ʶ���֮�䣬������Ҳ�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