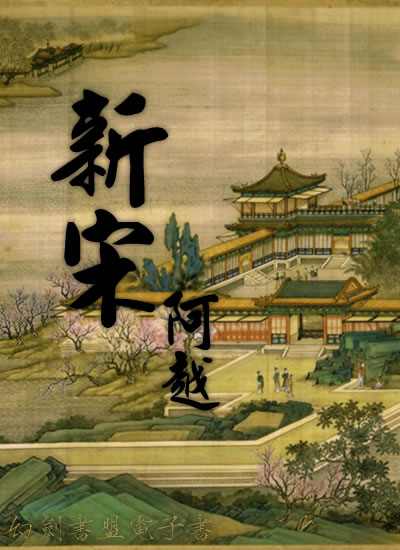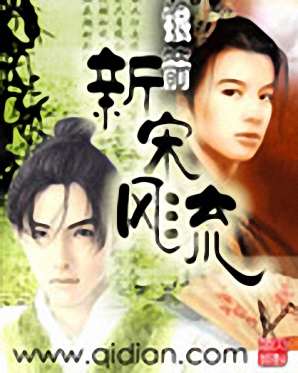新宋-第26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被她称为“桑郎”的男子,却只是神不守舍地唔了一声。若有认识的人见着他的样子,必然大吃一惊,原来他竟然是白水潭学院的山长桑充国。叫他“桑郎”的人,自然是他的夫人王昉无疑。
王昉似乎有点恼怒,嗔道:“桑郎?”
“嗯?”桑充国猛地一惊,这才回过神来,道:“我方才想事情去了。”
“在想什么?”
桑充国口中说出来的话,让王昉大吃一惊。“我在想,这次无论胜与不胜,其实于大宋都不是好事。真正有好处的,可能只有子明而已。”
“若能大胜,怎么于大宋不是好事?这是我爹爹梦寐以求的事情。若是我大哥未死,纵然他与石越有隙,心里也会高兴。”王昉不解中带着几分嗔怪。
桑充国皱了皱眉,他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端正了一下身子,沉声说道:“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朝廷——天子与百官,按照经书所说,天子是奉行上天的旨意,来治理天下的,而百官,则是协助天子牧守万民的。而天意,其实便是民意。唯有民意能直达上天……”
“是啊?这有何不对么?”王昉疑惑地眨着眼睛,习惯性地托腮问道。
“而子明却曾经说过,天子不是受命于天,而是受命于民。两位程先生与岳父大人也说,天下非天子之私产,天下是祖宗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这自是正理。”王昉笑道:“本朝立国以来,士大夫莫不奉行。纵是天子亦不敢以天下为私产。这些道理,其实不待石子明来说明。石子明不过是集前贤之大成而已。”她说的却是事实,宋朝本是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最浓厚的时代,唯后人无知,将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等同于所谓“封建专制”的加强,将一个明明是中国历史上宰相与外朝之权最重的时代,硬生生地说成是皇权加强的时代。
却听桑充国问道:“既是如此,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朝廷才是一个好朝廷呢?无论天子是受命于天还是受命于民,归根结底,天子都应当顺应民意。那么,是不是说唯有顺应民意的朝廷,才是好的朝廷呢?”
“那是自然。但是庶民有无知之时。”王昉沉吟了一下,说道:“所以,应当如圣人所言,施行仁政的朝廷才是好的朝廷。”此时二人早已忘记身处的环境,更是将说书人与众听客抛置脑后,全心全意地讨论起来。
桑充国怔了一下,笑问道:“那娘子以为,何为仁政?”
“大抵轻徭薄赋,简刑宽政,可称仁政。”
“我以为不然。”
“啊?”王昉听到夫君这样的回答,几乎是惊呆了。不可思议地望着桑充国,却见桑充国的眼中,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我反复翻阅石子明的着述,又与二程先生、邵先生几经讨论,方才得出这样的结论——”桑充国虽然压低着声音,却掩饰不住情绪的激动,“所谓的仁政,应当是一个好的朝廷应负的责任。一个好的朝廷,其责任,不止于轻徭薄赋,简刑宽政。后人评价诸葛孔明说,为政之要,在于宽猛相济,一律简刑宽政,并非好事。至于轻徭薄赋,自古皆被人所称赞,但是我却以为,重要的并不是是否轻徭薄赋,而是朝廷征收的税收,用到什么地方?!”
王昉出神地听着。
桑充国略有几分得意,道:“此事我曾与岳父大人写信请教,岳父大人亦以为然。”
王昉点点头,她自然可以想见,自己的父亲并不会反对这样的观点。实际上,王安石一向便持有这样的观点,只不过没有明确的陈述出来罢了。
“百姓交税服役,供养天子及百官,此为理所当然。然则,这交上去的税,所服的役,却必须所用得当。否则,是使天下奉一人,而非使一人治天下。凡天下财赋,出自百姓,亦当用于百姓,方为天下之大道所在。一国之内,有天子,有百官,有军队,此皆坐食俸禄者。百姓之所以供养天子、百官、军队,是为天子与百官能牧守天下,使天下无盗贼;军队能够抵制外侮,使边疆无烽火。然后方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以此观之,则朝廷之责,是能使百姓安居乐业。换言之,则可说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之政事,方是仁政;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之政事,皆是恶政。何为仁政?由此可知。仁政者,非止轻徭薄赋,简刑宽政。但凡训练军队、兴修水利、赈济灾民、鼓励生产、办学校、建药局,凡民之所急者,民之所需者,皆为仁政。而最要紧处,则是仁政并非是朝廷之施舍,而应当是朝廷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若其不为,便是失职。”
桑充国的观点,表面上看来平平无奇,但是细一思之,却是发聋振瞆。
王昉忍不住喃喃说道:“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她委实是震惊了,开始桑充国反对以简单清静少为思想作为“仁政”的标准,这一点身为王安石的女儿,她并不觉得如何新鲜,但是当桑充国说出原来“仁政”竟然是朝廷必须要做的事情之时,她却是震惊了!
原来百姓们完全可以不必为朝廷的“仁政”而感恩戴德,那其实只不过是朝廷的职责所在而已!
“两位程先生如何说?”
“大程先生与小程先生皆以为是。”桑充国的语气中,显得非常的自信。他的观点,是连石越也不曾提及的。他并不知道,甚至连石越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因为石越是带着“救世主”的心态去进行他的着叙,哪怕石越本人身上有再多的平等意识,再诚惶诚恐,但是他在心态上,却不可避免的居高临下了——于是他虽然在书中告诉士大夫们,治理国家应当如何如何,但是却表现得循循善诱,他不敢大胆地指责统治者——这是你们应当做的!他只是告诉他们,上古的圣王是这样做的,然后暗示他们,这样做就符合圣人的标准,会有好的结果,在历史得到好的评价。
这是石越的局限。不能说石越不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是出于谨慎也好,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也好,总之,最初喊出这一声“这是你们理所应当要做的事情!”的人,是桑充国。所以,他的确有理由感到骄傲的。
不过桑充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熙宁三年说出这些话,与在熙宁十一年说出这些话,还是很不相同的。在石越的着作经过八年的传播之后,他喊出这些话来,才显得那么理所当然。
王昉凝视桑充国一会,心中也为他感到骄傲。同时却又一点不满,她在心里微微嗔怪为何桑充国之前没有和她讨论这些事情。显然,桑充国有这样的想法,已经很久了。她忽又想起桑充国最先所说的话,不由奇道:“那方才桑郎说,无论胜与不胜,其实于大宋都不是好事。有好处的只有石子明。与此事又有何相干?打败西夏,使边疆无烽火,不正是桑郎所说的‘朝廷的职责’么?”
“可我现在却认为,这并非是当今的急务。”沉吟了许久,桑充国方说道:“打一场大战,败了不必说它,便是胜了,也是累得无数的百姓转运于道,不得安宁。而花费的钱粮,更是不可胜计——若肯将这些钱财用来办小学校,便是让天下的童子都读书亦不是难事。朝廷养着成千上万的冗兵冗官有钱,打仗有钱,唯独要来建小学校时,却立刻没钱,只是骗得老百姓出钱义学!”桑充国提及此事,不由愤愤不平。
“肉食者鄙,古来如此。不能很快见利之事,朝中也难以通过。”
“除此以外,去岁灾民,以十万计,皆在等待朝廷赈济。去年有几名学生分赴各路统计,发现各州弃婴,有增无减,而慈幼局却往往力有不逮,数以百计的婴儿因此夭亡。各地又有许多村夫愚妇,有病不治,反信巫术,若朝廷能多开医药局,岂非能多活许多人?朝廷官员,若误判一死刑,其罪不小,可这些人死去,难道便不是朝廷之过,为何却可以熟视无睹?军队虽是国家所必需,抵御敌寇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观子明所为,却似有开疆拓土之志。此次若能擒着秉常,一举灭了西夏,倒也罢了。现在听各处传闻,只怕秉常有惊无险。朝中诸公闻此大捷,必有人蛊惑圣听,盼着今年一举灭夏。大兵一兴,成败未知,而劳动百姓,耗空国帑,却是不可避免……此于国家,是喜是患?此于百姓,是福是祸?”
王昉一时默然。从小她就读过许多征战别离的诗歌,自是知道普通百姓而言,并不乐见轻开战端。但是收复西夏故地,却是她父兄的理想之一,她自幼秉承庭训,耳濡目染,岂能不受影响?故此一时之间,竟是不知道谁对谁错。若说桑充国对,似乎又嫌迂腐;若说他不对,但那百姓的困苦,却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桑充国所说之话,一句也难批驳得。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桑充国低声长叹道:“子明作的好词。只恐自己却忘记了……大败西夏,他自然是声名日盛,炙手可热,但是奈百姓何?如今只愿趁着这次大捷,息兵数年,使国家百姓,皆稍得休息。”
“只恐难以如意。”
二人说到此处,再无谈兴,不约而同都将目光移向那些还在兴高采烈听李秀才说书的茶客。桑充国见那些人脸上一个个都洋溢着兴奋之色,猛然间又想到,这些人似乎是乐见军队开疆拓土的,这些人的心意,应当也是民意,那么,究竟应当先考虑哪个民意呢?为什么某些人的民意,就可以重过另一些人的民意呢?想到此处,桑充国只觉得原本清晰的脑中如同一团乱麻,纠缠不清,竟是完全呆住了。
桑充国不知道,他没有猜中石越的情况,也没能猜中石越的想法,但是却猜中了朝中诸臣的心态。
慈寿殿。
太皇太后曹氏的居所,这一天显得十分的热闹。殿外虽然依旧银装素裹,殿中却是炉火通明。曹太后微微斜靠在一张椅子上,含笑望着殿中众人:自高太后以降,向皇后、朱妃、王妃,后宫所有封号在“妃”以上,以及生有子女的嫔妃,全部到齐了,皇帝也自然亲临。除此之外,昌王赵颢,嘉王赵頵与他们的王妃、王子、县主,也被恩诏入慈寿殿请安。
此时由皇帝赵顼与高太后、向皇后陪侍曹太后左右,余人依序而坐,将慈寿殿坐得满满的,众人尽皆笑容满面,不时低声私语欢笑,俨然是一副四代同堂共享天伦的景象。
坐得一会儿,赵顼看见赵颢含笑与赵頵交首接耳,赵頵频频点头,不由笑问道:“二弟与四弟却在说甚事?”
赵颢含笑不语,赵頵红了一会儿脸,又看了赵颢一眼,方说道:“臣弟与二哥方才在说,今年这般景象,实是欢喜,只可惜却少了两个人……”他说到此处,抬眼看赵顼,却见赵顼原本满面笑容的脸,已是如蒙上乌云一般黑了下来,心中打了个突,竟是不敢再说。但他这话声音甚大,满殿皆闻,原本欢声笑语的慈寿殿,在一瞬间,便已安静得连根针落地都听得见。连小孩子都吓得不敢出声。
赵颢见赵頵不敢再说,他知道自己这个四弟,一向醉心于医学与仙术、文学,素来不闻外务,对大哥赵颢是既敬且惧,这时被吓得不敢说话,倒也并不意外。当下缓缓起身,接过赵頵的话,从容说道:“此事原是臣弟听说狄咏战死环州,可怜十一娘孤儿寡母在长安,因想向太皇太后、太后、皇兄、皇后求个情,复了十一娘的封号,把她接到京师,也好有个照应。”他说到此处,动了真情,眼睛竟是红了,又低声道:“十一娘与十九娘,都是与臣弟一起长大的,骨肉相连,如今她们触犯天威,本是不该,唯盼太皇太后、太后、皇兄、皇后恩泽……”说罢,捋起衣袂,扑通跪了下来。
他这么着一跪,赵頵原是个本分老实之人,想起从小到大的情谊,也是站不住了,紧跟着跪了下来。二王一跪,两个王妃自也不敢再站,拉着身边的孩子,也一并跪了。
赵顼的脸上阴晴不定。
他此时并不知道狄咏是怎么死的,整个宋朝,都还没有人知道狄咏是怎么死的。大战过后,石越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环州城中活着的人口,仁多澣虽然履约没有杀他们,但是却全部掳入西夏。赵顼已经诏令石越,无论如何要将这些人赎回来——实际上,石越早就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进展。
不过,无论狄咏是怎样死的,他战死是事实。赵顼对狄咏的怒气,随着他的战死,早已烟消云散。清河恢复封号,其实只是迟早的事情。但是,虽然赵顼早已决定要恢复清河的封号,可是他心中却希望这件事情,是由他亲自提出来的,而不应当是其他人,更不应当是赵颢!但赵颢偏偏就提出来了。虽然他假意让赵頵先说,以显示自己并不是想借为清河求情之名,对博取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