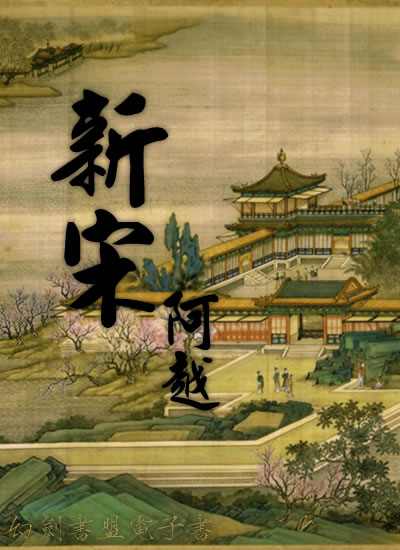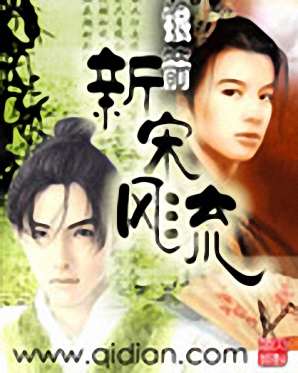新宋-第19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官家把四件东西看了一眼,没有说话,又让人送回去了。后来,官家对李宪说,这几件物什,石越也买得起,不过搜罗起来却要费点心思。李宪说,以清河郡主之炙手可热,石越费点心思,也是人之常情,他李宪也曾经送过几样礼物,虽然比石越的要差一点,但是花的钱却是差不多。官家说,你李宪是内臣,他石越是外臣,不可相提并论。”
曹太后不易觉察的皱了一下眉头,问道:“李宪服侍过三朝皇帝,连他也替石越开脱?”
“这都是老奴从别处听来的。不敢欺瞒娘娘,老奴等做内臣的,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外官的礼物。石越每年冬至与端阳的礼物,便是他远在杭州之时,也是从来不曾少过的。虽然礼物都不重,不过是一点特产之类,但是内臣中,都感念他这么一点心意。”
曹太后瞥了他一眼,道:“张严,你也收过石越的礼物?”
“老奴的确收过。熙宁宰臣之中,不送礼的只有文彦博、唐介、王安石、司马光几个人。其实这也是惯例,连韩琦和富弼,在仁宗的时候,听说也送过的。不过老奴却没有资格收罢了。”张严自从仁宗朝宫中之乱起,就跟在曹氏身边,自然知道面前的太皇太后,是不可欺瞒之辈。
“唔。”曹太后沉吟了一下,问道:“那你为何不替石越说话?”
张严笑道:“外臣们送礼,是前朝的书看多了,图个平安无事。却不知本朝祖宗家法,远胜于前朝。老奴收礼,只是贪了这个便宜,也是怕不收礼反惹人嫉恨之意。并非是收了礼就要替他们讲话的。娘娘一向知道老奴,却是再没有那个胆子,敢去议论朝政,品评大臣。”
曹太后点了点头,道:“你跟了我几十年,不要在老了的时候,把名声毁了,还把身家性命也搭上。不过若由此看来,结交内臣亲贵,倒也不止石越一人。只不过这一层上面,石越终是差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一筹,也不及文彦博。”
“内臣们见了文相公,腿都有点打颤,谁敢受他的礼?其实便是相公们的礼物,也没有人敢当真全受了,必是礼尚往来。不是都知、押班,也不会有份。内臣们也怕两府的相公,若真的犯了事,被一剑斩了,到时候只落了个白死。”
“你还算是个明白人。”曹太后躺下身子,道:“昌王的‘病’,好了没有?”
“还没好呢。”
“有人去‘探病’么?”
“倒是没听到有什么动静。不过昌王府这么大,纵有个人进去,别人也未必知道了。”
“若没有别人去探病,过两天他病还不好,你就带我的旨意去探探病。”曹太后冷冰冰地说道,缓缓闭上眼睛,道:“我困乏了……”
“是。”张严却并没有告退,直直站立着,没有动。
曹太后半晌没听到动静,略觉奇怪,闭了眼睛问道:“张严,还有什么事么?”
“是有一件事情。”张严的语气略带迟疑,“只是老奴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说便是。”
“有人看见,有人看见柔嘉县主,在今日六更左右,去了尚书省……”张严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道,饶是如此,声音还是有点发颤。
“你说什么?”曹太后霍的睁开了眼睛,严厉的目光逼视着张严,道:“你再说一遍。”
“有人看见柔嘉县主,在今日六更左右,去了尚书省……”
“她去那里做什么?尚书省谁当值?”曹太后的语气越来越严厉。
“不知道县主去那里做什么,尚书省昨晚是石越当值……”
“胆大包天!”曹太后气得身子直发抖,好半晌才说道:“柔嘉是怎么进宫的?”
“她昨晚陪皇后下棋,宿在皇后宫中。一大早,皇后不见了她身影,就差人去找,结果有人说……”
“这事有多少人知道?”
“皇后已经让知情的人全部缄口。算上奴才,不过四五个人。”虽然知道太皇太后不至于杀自己灭口,但是说起这种宫闱之事,张严还是不禁打了个寒战。
“她在尚书省呆了多久?”
“不到十分钟。很快就出来了。后来就出了宫。”
“去了哪里?”
“不知道。”
“此事关系到皇家的体统,不可外传。”曹太后毕竟是见过各种世面的人物,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但是从她微微抖动的手臂,可以知道她的震怒并没有平息。
“老奴知道。且这件事,当是柔嘉县主一时好玩。”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不可外传。”曹太后严厉的望了张严一眼。
张严哆嗦了一下,道:“奴才明白。”
“你去把邺国公叫来。”
“是。”张严不敢再在慈寿殿多停,立时躬着身子,退了出去。
当天晚上。邺国公府后门。
柔嘉牵着白马,哼着小曲,轻轻叩了几下后门的门环。如往常一样,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但是柔嘉却怔在了门口,因为站在面前的,不是柔嘉的丫环,而是一脸怒容的邺国公赵宗汉。
“爹爹。”柔嘉眼珠儿一转,灿然笑着,张开双臂,扑向赵宗汉。
赵宗汉万万料不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来这一手,又是恼怒,又是怜爱,心中顿时一软,几乎就要硬不下心去责罚了。但是慈寿殿太皇太后的严辞切责,却让赵宗汉心中一凛,勉强硬起心肠来,一把拉开柔嘉,板着脸说道:“你随我来。”说罢转身向自己的书房走去。
柔嘉吐了吐舌头,像小猫似的紧紧跟在赵宗汉的身后,一只手还紧紧拉住赵宗汉的衣襟。
到了书房,赵宗汉吩咐一声,把所有的下人全部打发出去,只余下他与柔嘉二人。这才看了柔嘉一眼,道:“十九娘,你跪下。”声音虽然不大,却有着从所未有的严厉与冷淡。
柔嘉此时早已发觉情势不对,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因笑嘻嘻的跪下,道:“爹爹,不可打得太重,会很痛的。”
赵宗汉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本来就最没有威严的一个人,竟是被柔嘉弄得无可奈何。好半晌才又硬起心肠来,冷冷道:“你最近都在胡闹什么?”
“女儿何曾胡闹?不过是去陪十一娘和圣人下下棋,有时候也去蜀国公主那里玩玩。”柔嘉对付自己的父亲,早就驾轻就熟。
“是么?”赵宗汉冷笑了一声,道:“你就没去过尚书省下棋?”
“什么尚书省?”柔嘉心中暗叫糟糕,却揣着明白装糊涂,一脸天真地问道。
赵宗汉见她神色,若非知道太皇太后素来英明,几乎要被她骗过,以为她是被人冤枉了。他从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竟然已经无法无天到了这种地步,须知尚书省那个地方,没有诏令,连他也不敢随便去。他女儿倒好,六更时分居然大摇大摆去了尚书省。完全是把皇家的种种忌讳,朝廷的各种礼法都不放在眼里。想到自己在慈寿殿被太皇太后骂了个狗血淋头,又惧又怕,又惭又愧,赵宗汉不由怒气上涌,厉声喝道:“你还要抵赖么?连太皇太后都知道了。”
柔嘉眼见父亲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早已知道此事难以抵赖了。但是却不料竟然惊动了太皇太后,不由大吃一惊,急道:“女儿只是去玩玩。”一面偷觑赵宗汉的脸色,一面低声问道:“不会连累别人吧?”
她不说这话还好,此话一出,却是把赵宗汉的火气全部激了出来。赵宗汉涨红了脸,粗着脖子瞪着柔嘉,冷笑道:“是啊,现在还担心会不会连累‘别人’呢!我的宝贝女儿真了不起,柔嘉县主,你就敢去尚书省玩?你怎么不去明堂玩?你怎么不去太庙玩?!”
柔嘉见父亲如此模样,缩了缩脖子,不敢再作声。
“赵云鸾,你听好了。太皇太后旨意,从今日起,无诏不准你进宫,不准你离开邺国公府一步。我已经让人收拾了一间院子,你就去那里闭门思过,每天陪陪你母亲。”赵宗汉一口气说完,又道:“从明日起,你每日抄一百页的班昭《女诫》和长孙皇后《女则》,抄不完,就不要吃饭。”
柔嘉几曾见过自己父亲如此声色俱厉的对自己,眼睛一红,扁起嘴来,赌气道:“不让出门就不让出门。什么《女诫》《女则》,饿死我也不抄。”
“你……”赵宗汉不料柔嘉还敢顶嘴,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举起手来,作势欲打,可看着眼前这个明艳照人,天真可爱的女儿,泪汪汪地望着自己,却是实在下不了手。半晌,才软绵绵把手放下来,叹了口气,几乎是哀求地说道:“十九娘,你是皇家的女子,比不得平常百姓。你总不能忍心因自己一人之不端,把全家几百口人都连累了吧?这次太皇太后没有收回你县主的封号,已经是格外开恩。若有下次,只怕……”
柔嘉县主被邺国公赵宗汉“严加管束”之后的第三天。
石越府邸。
“陆佃在《新义报》呆不长久了。”潘照临一面看报纸,一面淡淡的评论道。
“潘先生何出此言?”陈良奇道,拿起一份《新义报》,念了起来:“当使天下咸知,诛异族,开疆域之功,大宋不吝厚赏,此王韶为枢使,薛奕拜侯爵也;至于镇压同族,平定叛乱,虽有功不可厚赏也。盖国内之叛乱,是朝廷之羞耻,社稷之非福,用兵平乱,不得已而为之。此事于朝廷不足为庆,于官员不足为赏……”
“这么大胆的评论,他也敢说。又是和吕惠卿唱反调……”潘照临笑道。陆佃自从王安石罢相后,虽然因为政事微妙的平衡,一直是《新义报》的主编,主管朝廷的喉舌,但其立场,却已经较为中立。既不倾向吕惠卿,也不倾向石越。但是支持变法,依然是《新义报》的主要倾向。
陈良叹道:“新化县叛乱朝廷知道不过四天,《汴京新闻》和《西京评论》却在昨天不约而同报道此事。实在是厉害。《新义报》居然敢大张旗鼓的讨论政事堂正在讨论地问题,陆佃写这则评论,究竟是什么意思?迎合司马光,和吕惠卿破脸?他不过是个小小的主编……”
“清流而已。”潘照临略带讽刺地说道,“眼下管不了他陆佃如何,屋漏偏逢连夜雨。早不来晚不来,初三,新化县叛乱;初四,岳州军屯侵占民田,百姓联名告状;初五,卢阳县军屯数十名士兵胁持军屯长哗变。虽都是些小事,但连在一起发生,就显得军屯政策弊端甚多了。现在我们只要等着有人拿这些事情来做文章便是。”顿了一会,潘照临又道:“新化县叛乱的事情本不足为惧,无论他们怎么样报道,远在湖南路穷乡僻壤的事情,对于汴京士林与汴京百姓来说,都只是遥不可及的谈资而已。朝廷也不可能因为这一点点小事而放弃利益甚大的军屯计划。只不过现在地问题,是时机非常的不凑巧。”
“是啊,现在汴京的上空,风云密布。”
“本来公子并不是风暴的中心……”
二人正在交谈着对时局的看法,门房进来禀道:“潘先生、陈先生,门外有个道士求见。”
“道士?”潘照临与陈良顾视一眼,见二人眼中都写满了疑惑。潘照临笑道:“问问他是找谁的,若不是找人,便让他离开。”
“他说是王昌先生派人前来,拜见参政。若参政不在,便要见见潘先生。”
“王昌?”潘照临心中一凛,望着陈良,见陈良点了点头,潘照临站起身来,说道:“你去告诉他,参政不在,不便在府上相迎。我今天晚上,在陈州酒楼相候。”
晚上。陈州酒楼。
很少有人知道,陈州酒楼从熙宁九年腊月开始,实际上已经是唐家的产业。在这里单独的院子中密会一些不方便在正式场合相见的人,潘照临认为是比较安全的。他不相信何畏之,同样也不相信何家楼。
“无量寿佛。”在李道士的佛号之中,潘照临开始打量眼前之人。很快,他的目光中露出惊讶之色。
“是你?”
“不错,是我。”李道士微微笑道。
“你投入了昌王门下?”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不能不报。”
“昌王非可为之人。”
“我岂不知。昌王虽然礼贤下士,但资质有限。彼若为君,不过中庸之主。或者是又一个仁宗。”
潘照临冷笑道:“就怕是又一个真宗。”
李道士沉默良久,道:“昌王似非怯懦之人。”
“其材华又岂能与今上相比?”潘照临冷笑道:“你既知我在石府,还想要游说公子投入昌王一边?”
“一个平庸的君主,可能更容易发挥臣子的才华。此诸葛亮之于刘禅是也。”
“你知道我家公子之志向?”
“不知道。我云游四方,少问政事。”
“可你偏偏却涉足了这个漩涡。”潘照临指了指面前的椅子,道:“请坐。”
“事有非常而已。”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