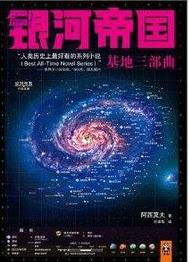���ºӵ���ϵ�С���ӺǬ-��9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ݸ�����������˵����������һ��������
���������⻰˵����ʵ�飬��ʱ�˿̣����Ŵ�������������������������ˣ���������֮�飬�������⣬��Ů���������˼�顣������������������ݸ��õ����գ���������������̽���һ�Ρ����õ����������ϵ����˶�֪����ȷʵ�ڹ�һλ��������������������ˡ�̫����������һ�գ����ڵڶ����ùٽ��͵�ʡ��ȥ�ˡ�������˵�ٽλ��ͣ���û�ɵ������ͷ��ԭ��������һ�α��ɽ����Ӵ�����������ɽ��˭֪��ʡ��һ������������û�м��������ʡ��Ѳ������˾��ѧ̨�����������ʵ�����ѣ�������������ѵ����䡣��֪�����б䣬���ַ������ݣ���������������̽������Σ����������ȷʵ�����ڸ��õĻ�����α�������ӿ��غ��ϣ��²����֡�
������������������֣���������ɤ�Žе�������Ҷ��ڶ��������˷Ը���æ��ȥӦ��������������������æ����һ�ԡ�֣���ѡ��ۡ���һ�ڴ���������ֽú����˵���������������������������һ���������ѴӴ����ݵ����˽����������һҾ˵����������ij���������֮�����ˣ���ɣ���
������������������ˣ���֣���������Ц����������ӵ���ү�����ţ���ү�Ѿ������볷������ϲ���������վͿɳ����ˣ���
����������������ʵ��������ϣ�ֻ��Ц�����������뵽�����֮���Ҫ����������Цһ�����������ſ���������������˵�����������Ǹ����������Ѿ�û���ˡ��������壬���������Ҽ����Ӷ��ء���������һ������ң�Ҳ�����ھͻ������Ǹ������Ĵ���ѽ����
�����������Dz�һ�����������Ц�������Ҷ�����ʲô�����㱳���Ǹ�������ȴ���Է��ģ���������������������ã�����·��ʧΪ�����������治֪��Ϊ��Ҫ̰���������ǵ�С��С�ݣ�Ҳ�������֮�����治�С���
�����������������⻰����֪���ı���һ�ᣬæ��ת������ȴ��������ֵ�������ҹ�������飬��ѧ�ʣ��������ƣ�������һ����������������һ˵���ƺ���ү�����ﻹ��ֻ��˵��������ѣ��ǾͲ��ض�̸�ˡ���˵�꣬��վ��������
�������������������ȻҪ�������ߡ���������һ�����������Ӧ����֣���Ѽ�������ָ߰��ذ�����ͷ��Ц��Цվ���������һ��������˵�����������������ʵ��֣ij���⡣������ȥ�������ֵ���һ�ν������������������𡪡��������ϴ�Ӧ�����������Ɑ�ƣ���
��������������������֮�У�����������룬�ⲻ��һ�����̵����Խ��ܵ���������ӹ�������һ����������ȥ������˵��������ǰͷ���¡���ͷ���£�����������ϡ�����������¿ɿ���˽����һ�ʹ���Ҳ�ա���
���������������ҿ��Ǹ�С�ˡ����ӿ��ۣ�С�˲����ۡ�������㵱���ס������վ��������������Ļ���Ҫ֪������һ�仰��ɶ�һ�ž��尡����֣���Ѻ�Ȼ����������Цһ������������һ���������Ŷ����ȣ����������ˡ�
��������������˵��ô�죿����ij�ڴˡ����������˵�����ͻȻ����ɤ��������������ʹ���ɿ���������ʹ���ң���Ȼ�����Լ��Ѿ���������ϼ���ĵ��������������ţ�һ�ַ����α���һ�ֶ�����ָ��֣���ѣ����ǵ�Ѫ�죬ֻ��һ����Ҳ˵��������
������������ҩ����֣���ѵ���ع�����Ц����������������ô����飡�ѵ�ֻ�д������Ƿ�ڵ���ð취��������㶼��֪������ҩ��Ȼֻ�м����Ч��������ֻҪ�����Ҿ����ˣ���������Ҫ����һ���˷�������Ҳ���ո������Ϊ�˱������ڹ�����ʱ�����������ʩС�ƣ����е�������Ǹ����Ǹ����
���������ʸ��������ش���������һ��ŭ����һ������������������档����һ����������ս��ɱ�����������Ǵ�û�м���֣��������ײкݶ����ʸ�������ת�����������ٿ���Ļ�Ҿ硣
�������������ˣ���֣���Ѷ�ݺݽе���
���������������䣬һλ����Ӧ�����룬ͦ���������ף��ʵ����������кβ��ţ���
����������������˭����֣���������������ԣ�æת���ʵ���
��������������������
��������������ү������һ��Ӧ�����롣
������������һ�ߴ���������һ��ͦ��ֱȡ����������֪����������ˣ��Ѿ�����ѡ�
����������һ�±����⧣�������û����������������˽������飬���Լ��������������һ���������ǹ���ñ�õ�һ�ɺ����ܲ������У���÷��죬�������������˳��һ��ֻ�����顱��һ��������ıţ���������Ҳ����÷��飬�����������ӭ����Ͻ��������������ˡ�һ��֮�䣬�����Ľ���ƽ���������æ������һ�ͣ�����һ�ɺ�����˽���ɨȥ��ֻ�ۡ��͡���һ�������ϵ��·��ѱ�����һ�顣
��������������ʱ��ŭ�����һ�����������ǹ�����ס֣���˺���������������������С������˵����������ȥ�����˴��һ�ţ�֣����һ��ʼ�ŵû겻���壬��ʱ���Ǹ����ӣ����ſ��������Ժ�ӣ�����ɤ�Ŵ�У���ǰ���ŷ��ˣ��ظ���������������һ����������ǧ������
��������������������Χ����ɱ��������������������Ĩ�����г��ֺݶ����ۼ����������࣬��������ʩչ����һ����������Ӵ���Ծ��������һ��Ƴ������Ҳ�˵�Ժ����ĸ����δ�Χס��ɱ������ʹ�����������������²��ã��ԵýŲ����ȡ�����������һ���������������ߣ���˵��һ�����֣���ö����ͬʱ���֣�Χ���������ĸ����ѱ��̵�������������ɱ���Ⱥ����죬�Ծ�����֧�֣��������ﺰ�У���Ϊ����ҲҪ�˳�������������˶�������ʱ��һ����˫����ס���ܣ���һ�����ӷ����������ݶ���������˦�����ڣ������������������������������е�����ʦ����������������Ҳ���ߣ���˵�꣬��ɲ��ܷ�Խ�ݣ��ߵ���Ӱ���١���ʱ�������£����ҳ�һ���ࡣ
��������Ժ������˰�����Χס���������������������Цһ����˫���ڿ�һԾ�����������Ȧ�ӣ��ص����������������ͷ�ԣ������û����������ҽУ���������Ѫ���ܵ���ͷ�Ӵ�������˳�����ԭ����������ͷɱ�˿�������ѵ��������ۡ������˾���һ�����������ʱ��ȴ�����䡱��һ���������ĺ�ǽ�Ѿ���̮��������ѧ���������Ծ����ǽ���ӳ��˻�����
������������·�ºã���֣����������������Ҫ�������ǣ����������䣬����һ��Ůǽ��������������һ�ƣ����Ƶ��ˡ�ԭ��������������ר����ǽ������
�����������������������ֶ������һ���˵Ĺ���������Ůǽ��ȱ�ڴ���ಡ���һ�����˹�ȥ����Ӱ��ֻ��������������һ�£����˷�������һ��ߺ������˵���ǰ��ʱ����������һ̯Ѫ�������������Ѳ�֪ȥ���ˡ�
������������֪��������һ�������ȫ�Ǵ���������֣�����Ⱥ��亹һ�����������ܻ��ش�е���
����������������վ��������Ŀ�����һ��߬ס֣���ѵ��ֱۣ���̫��͵������Ĵã�������Ҳ����һ�����ϵĺ�������˵���������˰ɣ��ҽ������̾��ߡ���֣����Ҳ���߰ɣ���
�����������������Χ���ڸ������ߵȺ�������Σ�ֻ������䡱�����죬����������ǽ�����������˼䣬ȴ������ͷ���������������䵹�ˣ����ã������ű�û����Ϣ�����۰Ͱ����˰��գ����������˳�����ϣ�˼��һ����������ض������˼����С����ص����Ҳ����������ټ���˫��һ����һƨ�����ڵ��ϣ���һƲ�������ء��ش��������һ�߿ޣ�һ������Թ�����ù�ѽ������Ǹ���������ʲô�ã���ɵ��ã�����Ҳ���˼ҡ�
����������ʲô����ѣ�������������ǰ���Ȼ������һ�䡣�����������ģ��͵ر���һ������һ������ͷ��ʱ���Ǹ�׳�꺺�ӣ��ڵ���Ҳ�Ʋ�����˵���Ŀ������һ��µ������������үү������ޣ�����ƨ�£���·���죬�˸���ߣ������ĵ�����
��������������������˭���DZ���Ұ����ԶԶ�ִ���һ���ʻ���
���������������˱�����ʱ�������ĶԹ��ƴ�ӵ��һ����װŮ�ӣ���ͷ����һ����װ���Ӱ��ű����ಽ�����ظ��š�����Ů�������Ϲ�Ŀ����ꡣ�������ݸ��ոն�ס�¡�����һͦ����˵����������ʲô�ˣ��ܵ�������Ұ����Ұ����������æ�������������ӣ����ëͷС�ӷ��ſ���˵ʲô����ѡ���
�����������������˲���һ������ǰһ����˫��ҡ�ŷ�㶵������ļ�ͷ���������������е㷢�������ú��ӣ������ң������������ˣ���
��������������˭�������������һ�������������������ʵ���
����������������⺢��һ���·�˺��ϡ�ã���Ƥ��¶����ͷ��������һ����һƬ����ü���۵ģ�ȴ��һ������������������ꡱһ��Ц�ˣ�ת���������������Ц�Żص������ǣ�����˵�úã���̤����Ь���ٴ�������ȫ���ѹ������������´�ض�������������������ѵı��ã���Ѱ�������꣬�ܵò�����Ϣ�����ú��ӣ����֪���������䣬���߹ùã���ô����
������������һ�۲�գ�ض��ſ�������۾�������������һ�����������Ű�����Ŀ�⡣���ã�����������ͷ��������Ĩ������������������㣬����ʲô���ӣ��ҹùú������������˼Ҹ��������ա�
������������Ҫ�ޣ�Ҫ�뷨�ӡ��������긧ο���������ʲô�������ţ�������ù��ϴ�ȥ������������˵�ţ������Ȱ�س����������˺Ӱ���ȥ��
��73�¡�������ҹ���������ʹ������������ˣ�����
������������˼�����������������һ��������ѴӶ�ԫ���ӳ����ã����涫���ϱ������ֿӿ����ݣ���·���У����ӱ�ۏ��������©��֮�㣬�̻���ɥ��֮Ȯ�����������ݳǣ�ֱ���������ϵ��������ŷ�������ѣ�������ӣ����˲�������һ�Դ�é�ڸ��ŵ�ˮ����ЪϢ��
���������������ˣ�������Ұ���ǵĺ���һ��������Ѳ���ʶ���Լ����ȳ����ˡ��������Ƕ����ѽ��ĸ��죬�������һ���������ű�������ľ�İ��ӣ���Ц�������룺����������������µİ�ͷ���ǻ������䣡��
����������������������һ��������Ѷ�Ȼһ����æ�������Ӳ鿴��ȴ˵����������
����������ûʲô������������������֪�ĸ�����������һ������
���������������ϸ��ʱ���ǹ���ֻ��������ɫ�ף�������������һ��������æ������һֻ�֣���������д�������������Ҫ��ô����
��������������˱������أ�ֻ��������������һ·ʧѪ���࣬��ʱ����ͷ�Σ���ء����ǡ�é�Զ�����ת����ǿЦ�������ڼ����ϣ�����Ҫ���ġ���������ˣ��˲����������룬������Ҫ��������¿ۣ�����ȴʧ���е���
�����������𣡡�
�������������˫�ִ����һ������ͻȻ��ʶ�����Լ��������ŵģ��Ѳ��ǡ��������������ߡ������͵ܡ������dz�˼���Σ�����Ѳ�ȻһЦ����������������д�������ҷǵ�ѧ���壬����»��Ů�ӣ���Իɩ��Ԯ֮���֣�ȨҲ��������ĬĬ����ƺ��ѻ�˯��ȥ�������С�ĵؽ��Ѫ��ճʪ���½�˺���Լ����ӵ��½������������ϡ���Ȼ������ָ������һ��Ӳ�ϸ�����Լ�����ʱ�������ǿ鼦Ѫ�����⣬��������һ�����ںޡ�������ãȻ����꣬����ʲô��ζȫ�С��ֶ�Ȼ��������һ·������Ѫ��������Ҳ����������ЪϢ�ˣ�
���������������������������ѵ����ð���ĸ��ĺ�����˪���ڻ�Ұ������һֱ���˰��ʱ��������Զ�������������������һ�ţ��������˻�����Ѫ������������ת�ơ���
���������ۼ�ǰͷ��һƬ�ڳ����Ĵ�ׯ�ӣ�����ѱ�������һ��һ��Ų�˹�ȥ��ȴ��ׯ������С���ƵĶ������q�q�ش����ţ��߽��˿���ȴ��һ����ͤ�������������ǰ������������һ������ôת�������������ˣ�����ʥ�˹ʾӱض����ˣ��Ծ���ο��ת�������˿����࣬�������Ƕ���һ������������Ǻã�����ת�������������ˣ���ʵ��Σ�գ��㸩���������Ѱ���˼����½�����˵�������𡰸���ͨ�١�����ר��Ѱ��ƶ���˼ҡ��е�Ժ����ڼ�ª�������Բ������е�����������̫�࣬����Ҫ�Ķ������ˡ�ֱ����������⣬��������������Ѳ��ڿ���������Ѱ��һ���е��˼ҡ�
�����������Ժ��ֳܴɶ�����ȴһ�ɶ���ɻ��é�ݷ���ԺǰһƬ�ճ���ɨ�øɸ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