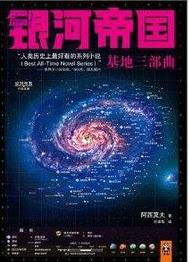���ºӵ���ϵ�С���ӺǬ-��7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Ƚ�����������ȥ�ú���ҵ���ӹ����ˣ���������Ϻ����������º���ˮ��ֱ��Ѳ����β���ʵ���ࣿ�������ɣ���˵�ű�������E�����������E��������ȥ�α���������������£������Ϲ�ί�˴����ƺ�
����������Ȼ���и�����������ǰ�����������������ү��Ȼ֪�����ǹ̰������Ǹ��ù٣����������������ǰ��ա������������ĺùٺܲ�����ѽ����
����������������Ǩ���������Ц������������һ���ù����̰�����Σ���
����������һ���ʵ�������������Ǹ����Ƶ����긾Ů����û���������һ���Ȼƾƣ���˫������������˵��������������������ү��һ���ů��ů�����ӣ��������������ɣ�������һ��������Ĩһ��������������þƣ���
��������������ү˵�ƺã������ǹ̰��˵����棡���Ǹ��˽ӹ����벢�����£�Ц�ǺǴ���˵����������ү����˵Ҫ��ίһ���ù����̰����Ҳ�ã������Ե�̫�����ˡ��β�ί�Ǹ��ùٵ�����ȥ��������̫ү����������������ٲ����٣��ǻ���������үһ�仰����
�����������ã��ã���ֵ���һ����ʷ�����������˵����ϷŹ⣬���������㣡���Eʳ��Ʒٺ���ӵ�̨�Σ������ι̰�����ô�����ް׳���һ��ƣ���Ҫ������������
����������̲�϶�ʱ���������߽У�������ʥ������
��������ԭ���ؾ�������ֻ�����Ƴ�һ�죬���������������ڹ̰��������E���鷿�����������Щ���겻�������鷿��һ������£�һ���������Ҫ�˲�����ȴ�ֲ��ԣ�������ϳ�����������˼�ҳ���ַ��¡�
����������Ȼ������κ��ͤ����˵��������ͤ���㵽�Ƹ�ǰ������κ��ͤ����ЩĪ���������˳�ӵ����˹�����
�����������������ơ�������������κ��ͤ������̾��������һ�����ʴ��£�����ȴ�˵ش����㣡��
��������κ��ͤ��Ȼ�е�һ�ɼ������ȡ�������������Ѫ��Ѫ�Ķ����ӵ��ﹰ����Ҳ���ס����ɫ�����Ǻ��ˣ�æ���µ��������購������ū�ŵĹ�ʧ����
������������Ҫ���������ί�������������һ���ɣ���
����������������ū����ô�����ί������κ��ͤ��æ˵������������Ļ���������ð��������ū����Ϊ������������˵�����˵�ţ�����������������������
�����������������㣬�������Ǽ�����ū�����ޡ�������Ц���������ᶼ�����ˣ���˵��ί������
����������ū����IJ���ί������κ��ͤ����ߵͷ��������˵������ū�������Ӻ�������иг���ˣ���˼����Ϳ��Ҳ�ѱ���һ��
������������˵����ʵ��������������κ��ͤ������������ȷ��ί����ĵط������ѵ��㲻��������Щ���Ӵ��㱡��һ�������
��������κ��ͤŪ�����⻰����˼�����û���һ����æ������ū�Ų���������£����Ӳ���������ū�š�������������˻ػ�Ц���������Ǹ����˻����ͻ��ˣ��⼸����������������ģ���κ��ͤæ������ū��������Σ���������¶���Ǿ�������˵���Ӳ�����Զū��֮���������У�ū����Ӧ�����Ծ̣���������������Թ��֮�ģ���
�����������������ܺã�������̾�����������վ���֪�����⡪����������ͼ�����鲻ͬ����������һ�£������������ǻ��ף���ʱ������ֻҪ������֣����ܲ������������ӣ�����ž��䲻����ֻ������һ��ͬ��ʿ�ĵ��ˡ�����ʲô����Ľ�ģ���˵�����������һ��κ��ͤ��������˼��˵�����������ǣ���ʵԶ�����������ء��㼸����ּҪ����ѧ�ģ���δ�ʡ�������ʱ�����Ҫ���⽮�������ǻ�������һ�仰����������ѧ�����ӣ���������Σ����ղ�����ʵ˵����������
��������κ��ͤ�����ˣ��̻�ؿ���һ�ۿ�����ȴ���������˰��֡���������������Ѳ����������ʲô�õط���������Ҳǿ���˶��٣�������ȥ�������ǿ��ǹ����ҵĵ��̣��ѵ���Ҳ�����ȥۏ��ˮô����
��������������ʥѵ������ū��é���ٿ�������
�����������ﻮ���������ò������������ߡ���Ҫ�Ե������������
����������������һ����ο��˵���������У�����������κ��ͤ����˵�÷����������������������ĵ��£�����������Ĵ��Դ����Ľ����ֵܺ�������ͨ���ݣ�����������֮��������һֱ�㷲����������������鵷��������ȴ��û��ʵ�ݣ������У���Ҳ����óȻ�����鷭������������������ġ�
��������κ��ͤ�������룺��������һ���ư���ֵ����
��������κ��ͤ���ڳ�˼Ĭ�룬�������E������ͨ��˵����Ǭ��������������������κ��ͤ��֪�����ض���Ҫ�³ʱ���
��58�¡�����������Դ�������̫�帳ʫӽѩ��������
��������͵�ͨ������ﹲ���������ۣ�һ������ͼ���ܴ��ĵ��������ӣ���ϸ����˸������뾩�Ժ���ɲ���ں������ذ��Ʒ��������˾ʱ��ּ������һ�����ڳ�����ûƻ�����˵������Ѳ�����������ܲ���ʮ�����������ٵİ��ӣ�ĩ�����౨����ѵ�����������δ���������տ���������һ�ߣ�������һ����ʱ������һ����ԭ����������ѵ��ױ����ӣ�������������ǰд�ģ������������϶���������С�������ﲻ��һ���˷ܡ��������������ҵ�������꣬�������ּ�ʮ����Ϥ��
�������������Ĵ��ζ��������ֱ������ĵģ���Ȧ�����պ죬�������Ҫһ˿���ѵ�ϸ�����֪�������е��ּ�����������ǰ�����о�Υ�ط�֮�С����ſ��ţ����鲻�Խ���С������������
������������Ϊ�ķ���������������ΪҪ�����ܶ������Ծ��������ܾ۲ƣ������Ա��¡����ϲ��ˣ����°嵴����������������ʵ����Ȼ��ƽ�����²��ɣ����²�Ϊ�����Ƕ����У��������в���֮��������������ʥ�����������ϡ���һ��֮����һ��֮�ޣ��Ҳ������ڱ��£��������ɢ�ˣ�����������ѧɽ������ʿ��֮�ģ��Ƽ���Ȼ�������ľ��⣬�����˲ţ����������ã�Ϊ������ҵ���߷��ౡ֮������Υʥ�գ�ʱ������Դ˹�����棬����Զ�ʣ��ܲ�DZȻ����
���������ٿ��±ߣ����м���С�֣�
����������������а�������ɣ��������ҥ���ƣ�ɿ�����ģ�־�ڲ��⡣�˼���Ϊ��Ᵽ�δ��ʦ���Σ��ڴ��స������Ϊ��������֮�Ծ������鰵�ã�һ�ĵ������������Զ��ӡ�
������������Ѷ����ּ�
���������������ţ���ˮ���鲻�Խ������˳������Լ�����λ��ʦ�������������ϡ�������֮�ߣ�������������֮Զ��������������������Ƽ��Լ�ʧ̬������æ�������ˣ�ת�������E��������ʦҥ�����࣬��������ھ��ܣ�������Щʲôû�У���
�����������еġ������E��һ˼����������Ƕ���Щ����̸֮�����ѳ����Ͻ�������
�������������������������Ը���
�������������������Eæ����������С����ҥ������
�����������ſڶ����������ɴ�ɢ������˫����������ʱ����һ���ꡪ��Ȱ������ơ�
�����������E˵�ţ�͵�ۿ��˿������������Ϻ��ޱ��飬������ֵ�������������������
����������ʿ��������������ľˮ�����顣ʵ���������Ի�����������Ѫ��ˮ��
�����������Eһ�߱�������һ�߽���˼����������̧ͷ�ʵ��������㿴������Щͯҥ��ζ�����ָ��ʲô�������Eæ����ߵͷ��������ʵ��ѧªʶdz����һ�����ⲻ�����ڶ�����Щ��˼��δ��ֱ�¡�
��������������ˣ����������ʲô�ɰ���������һЦ����������ʲô��ֻ��˵����
�����������ǡ�����ڶ���ͯҥ����ָ�����𡣡�
������������ô�����أ���
��������������ʿ�������������������E���͵������������ߡ�����Ҳ���ѡ�����������д����һ���ɡ��֣��������������㣬�ϳ�һ����ƽ���֡���ľˮ�����飬�������ϡ�ľ������ˮ�������������룬�����ڡ��𡯣�����������֮������ָ���������������������ǡ��������ǿյģ�����˵��ʵ�����ӡ�������һ���������֣��ճ��ˡ�ƽ�����������֡�����������Ԫ�䣬����ȸ��Ω��Ϊ�����������������ǡ�ƽ�������ɱ�����������⡮Ѫ��ˮ�����ǡ�ɱ������˼����˵��ߵͷ�������ⲻ���dz������ܶϣ�δ���ܴ���ҥ�����⡱
������������˵�öԣ�����������һ�����ѡ�����ʵ��Ĵ�˵����������ͯҥָ��ȷ�������𣬵����������볯͢������̣������췴֮�������Dz���֮ͽ�������ɿ���������Ͻ�������������
����������������Ļ��������E���ݴ��������������û���ˣ�������������в��ܾ�֪�������ط���ʢ��һ�֡������ɡ��̣�����ʮ�ֹ��ؿ��ɣ�ȴδ����Ƿ���ҥ���йء���
�����������������˵���ˡ��������ƺ���Щ���⣬վ�����������˸���Ƿ���������ѳ��ˣ����E���Թ��ˣ��������賿���̻ؾ�����κ��ͤ����������Ϲ������̣�һ�й��ž㲻��졣��
�������������賿��ģ������������ݻؾ������E����Υּ��ֻ���ź����˵ȹ��ͳ��DZ����Ļ�����������Ϊ�����������������У�������˷�װ��ͷ��һ���ں��ȶ�̨�ڣ����Ž�ɫ����������Ƥ�ۣ�����һ��ʯ������̽�ӡ�κ��ͤ����������������һ��һ�����Ÿ�ͷ��������������ӵ�����룬����Ϲ���Ҳ��ȫ���ӳ����������������Ӫ��ǰ����ӵ���ƺƵ�����̤�ż�Ӳ�����Ķ�����ӭ�������ĺ��磬˳�������ذ������ٵ�ֱ��������
�������������������ϣ���ɫƽ�����Դ���ο�����ܼ����������������ߵ�������ô�����ң����ǣ����Ծ������ò���֮��������������ʦ����ѵ��ţ�һ������������������и���һ��̤ʵ֮�С���˼���ã����������ϻ�����κ��ͤ˵�������������£����������ޣ�һ�ǵ�����������������������һ�£������ж��ٴ��������������ǵ�����Ϲ���������Ӫ����פͨ�ݣ����E������گ��������ּ���������꽫�����������Ե���������Ϊ���ؾ�ʦ�Ż�����
���������������£���һ����κ��ͤ������ģ�̫�͵���̮��������گ��������������������˼�������Ų��죬˵�ǿ�����������ȻҪ���һ�£��ڶ���ȴ���ˣ��Ϲ������������������Լ�����Ӫ�ܹ�Ҳֻ��֪�����գ������ͣ�ΪʲôҪ�ؼ���Σ����E�ǿ����ڶ�����Ը��������ģ�Ϊʲôһҹ֮����ֱ��ˣ�����Ƭ�̣�κ��ͤ���Ŵ����������ּ����
�����������㲻Ҫѧ���ٵ��ͻ���������Ц��������Ϊ���ͷ����˵�������ʸ������ٵ��ؾ�����Ҫ������ū����ʲô�ã�ͨ������ط�������ӣ��Ϲ�һ��ĩ����֮����������ּפ�����Ҳ�Ŭ�����ϡ���������
��������κ��ͤ��Ȼ������н�֮�Զ�����
�����������������E��Ҳ�Ǵ�ͬС�졣�����������°ͣ��۾����������Զ��������˵��������������Ҫ���죬������Ҫ������һ�¡����E�����Ĺ����˸���������̫�ϣ�Ҳ����̫�¡���
�������������ꡪ���⣿��
�������������E��������ϸ�����������ھ������������������ǡ�෴��ɣ����䳤������̡������������������ƺ�������ƺ����͵Ĺ⣬���ò���˵�������õ�̫�Ϳ�ϧ�˲��϶����õ�̫�ߡ�����Ȼ������Щ���ڣ�һЦ��ס�ˡ�
��������κ��ͤ���ӵ�Ƴ��һ�ۿ��������������������ҳϵò��������ˣ���ʱ������ʱ���µĸо����Dz��ϵ���������ͷ�������ÿ�����һ̶������ˮ����ɽɫ�������������������������ȥ���ֻ������ɲ⡣����Ȼ�����������������ӣ���װDZ�����Լ������������ֱ꣬�����ݰ�����������¶�����ࡣ�Dz����Լ������������������أ����������������Ŀ����ȥ�ˣ�æ�ִ���һͷ�룬�ںӵ������E�����Լ�������Ʒ���츦������ˮ��������������Ϊ�������E�����ֳ��������������ƣ�ʹ�����������ˡ�ʥ�⡱��κ��ͤ��ӭ�洵�������Ϯ�ô���һ�����䣬��ͦ��ͦ���ӣ�����һ�������ֱ��˻�ȥ��ֻ����ʲôҲû��һ��Ŀ��ǰ����
������������ʿ�����Dz�Ӧ�ƽϳ�����˵ġ����·����ڻش�κ��ͤ�����ʣ�������Ȼ�����̾Ϣ��һ����������Ϊ�����ģ�Ҳ�����������ij��ӡ������������ڲ�֪�����ˣ�������ͷ��ѧ�����࣬Ҳ������Ч������ɽ������������Ӧ�Եľ��˱��������������˵û�����Ĺ��͡�ǰͷ�����θ�������Ŷ�ת�����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