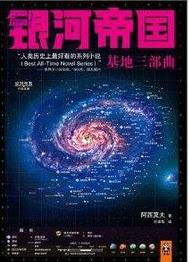二月河帝王系列·康雍乾-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金标“刷”地抽出腰刀,恶狠狠地道:“那就休怪小人无礼——”正说间,穆子煦已抄至身后。他做贼出身,脚步奇轻,刘金标竟毫无知觉——便觉膀子电击般一麻,已被穆子煦摘脱了臼。穆子煦一手反拧住他的手臂,另一手将匕首在他脖子前来回比试着:“还敢无礼么?”郝老四、犟驴子抢前一步,推开架何桂柱的人,一把将店老板拉了过来,却不知魏东亭要这人做什么,也不松绑。
刘金标被解除了武装,嘴却依旧很硬,梗着脖子叫道:“你有种就杀了老子!”
犟驴子气火了,大声道:“老子杀的人还少了,就再添你一个王八蛋也没得关系——”上前一把揪住刘金标前胸,笑道,“天儿热,让你祛祛火气!”夺过穆子煦手中匕首就要往他胸膛上扎。
“兄弟!”魏东亭已夺得何桂柱,无心把事情弄大,忙止住道,“别弄脏了你的手!”
刘金标见他不敢杀人,索性放泼:“你是哪个庙的神,比班大人还大?!”
犟驴子怒极,将匕首朝腰里一插,二指如锥,直插进刘金标右眼里,活生生地把个眼珠子抠了出来。“不给你点颜色,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那刘金标像猪似地嚎叫了一声,挣了一下,被穆子煦在后紧紧拤住,哪里动得!跟来的人见这五官不正的矮个子生性如此残忍,一个个吓得闭目摇头,噤若寒蝉。犟驴子把眼珠子扔给郝老四说:“接着,下酒最好!”又问道,“刘金标,这只眼也送兄弟吧?”刘金标痛得浑身直颤,一句话也说不上,只是闭着血肉模糊的眼睛一个劲地摇头。
魏东亭“哼”地一声说道:“今儿给你点教训,好教你知道,北京城还轮不到姓班的!”将头一摆,押着何桂柱便扬长而去。
第15章 史龙彪翻悔皈清室 班学士解疑鳌公府()
魏东亭一行急走了半个时辰方才站住,下马来给何桂柱松了绑,笑着给他掏出了嘴里的抹桌布道:“老板,这一次擦干净了嘴,十年不用漱口”
何桂柱长长透了一口气,跺脚埋怨道:“好魏爷,你闷死我了,怎么不早点给我掏出来?”魏东亭道:“你一嗓子唤出我名字来,岂不大大麻烦!”说毕哈哈大笑。
穆子煦惊讶地问道:“大哥,这是——?”魏东亭道:“这就是悦朋店老板,姓何名桂柱,本想吃他的东道来着,不料今夜竟吃我的了!走吧,都到我那去,咱们吃个痛快!”
返回虎坊桥魏东亭宅上,已是四更时分。史龙彪和明珠两个因各怀心事,在床上翻来覆去正睡不着。老门子上了年纪熬不过困,坐在堂屋角春凳上睡着。家下仆人给魏东亭开门进来,也不惊动人,一干人悄没声儿穿过客厅来到了后院,明珠、史龙彪早已起身迎了出来。魏东亭便吩咐穆子煦:“这几位兄弟住东厢房,咱们这边来,今夜睡不成了。大家吃酒耍吧!”当下便引着他们进了西屋。
明珠见魏东亭身着崭新的三品武官服色,在灯下耀得眼亮,钦羡地道:“哥哥一夜便连升三级,小弟合当祝贺。”众人这才瞧见魏东亭今夜装束端的鲜亮——红珊瑚顶大帽子,补褂下金线宫制江牙海水,石青袍子后面悬着镂金嵌玉的一柄长剑,浑身上下一崭新,煞是英武。
魏东亭给大家瞧得不好意思,双手解下宝剑说道:“这是圣上亲赐小弟的,不敢独享,诸位也开开眼。”犟驴子性急,上前便要拔出观赏。魏东亭却庄重地将剑举过头顶,然后放在桌上,退后一步,又躬身一揖。众人见他如此恭谨,不禁肃然。
明珠上前捧起宝剑端详,便抽了出来,方出鞘便觉寒气逼人,晃一晃,照得满屋亮闪闪的。明珠失惊道:“此乃太祖身佩之剑,如何有缘到哥哥手中?此乃非常之恩遇也!”魏东亭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将文华殿康熙封赠的情形详细告诉了大家,说到最后已是泪光晶莹:“圣上今以此剑赐我,正是要我建勋立功。圣上以国士待我,我即以国士报之,魏东亭纵碎尸万段,也要报答此知遇之恩!”
“一将功成万骨枯,”史龙彪叹了口气,弦外有音地道,“你们求功名的人,心思究竟和百姓不一样。”
大家正沉浸在一种虔诚、肃谨、感恩的心情中,听得此言不禁愕然。魏东亭想,这倒是试探史龙彪的极好机会,遂笑道:“老伯,您瞧着我是见利忘义之辈么?”
史龙彪心情极其复杂,打火点烟抽了一口,半晌叹道:“倒不能这样说。满洲人入关二十多年了,老百姓日子一点儿也不见好。你这里讲大丈夫遭际不凡,可京西人市上头插草标卖儿鬻女的有多少!真可叹哪!”
“老伯说的是实情,”魏东亭心情沉重地说道,“但谁使他们抛井离乡落到这般下场呢?皇上今年还不足十五岁!”
史龙彪没有出声。魏东亭心知这话已经点到穴位,接着道:“从顺治四年圈地,到康熙这几年又圈又换,天下苍生冻饿而死的不知有多少,老伯您不说我也知道。去年我随皇上到木兰围猎,一路上收了几十具饿殍尸体,皇上难过得掉泪,命人收葬,说:‘这都是朕失政所致’”他瞥了一眼史龙彪,接着道,“我们还看见一父一女,那孩子饿得面色青白,头上插着草标,见我们走近,以为是买主,又惊又怕,浑身抖着扑到老人怀里,嘶哑着声儿哭‘爹呀,别卖我,我会织草席、会烧饭,我讨饭、当童养媳都行你呀你不心疼我啦!’一边哭一边抓打老人皇上当即拿了二十两银子赏了他们,眼睛看都不敢看他们这能说皇上不恤民,心地不仁么?”
听到此处,史龙彪也不禁动容,旋又勉强问道:“一边下诏禁止圈地换地,一边朝臣又在大圈大换,这算个什么意思?”
“对,是这样的。”魏东亭道,“这便是今夜皇上召我的真旨。皇上说归说,臣子仍照老样做,天下哪能太平?”
魏东亭瞧准了史龙彪外刚内柔的秉性,一点也不客气地痛下针砭:“老伯任侠仗义,纵横江湖几十载,号称铁罗汉,是顶尖儿的好汉了,恕小侄冒犯,不知老伯到底曾救过几万人?”
这一语下得很重,众人正担心史龙彪受不了,魏东亭却提高了嗓门:“这不是杀几个贪官的事,也不是复辟明室的事。现皇上决意更新政治,复苏民生,而内有权臣,外有藩镇竭力阻挠,皇位都坐不稳,性命也无保障——”说至此,魏东亭忽向史龙彪一揖拜倒,扬声问道,“即以小侄如今的处境看,敢问老伯当何以处之?是助皇上?还是鳌拜?吴三桂?或是别人?”
史龙彪早又愧又窘,忙双手挽起魏东亭:“贤侄不必说了。我枉自活了五十年,并不明理!”红着脸坐下叹道,“实不相瞒,我与鉴梅进京寻你,原为做一番复明的事业,如今人事俱非,鉴梅现在鳌府做了丫头,与我也常常见面只是”
“哦!”明珠忽然失口叫道,“我明白了,老伯原是为南明永历入京来的——”
“禁声!”魏东亭低声喝止,“哪有这话,永历早死了!”
“明珠说的不假,你也不必掩饰。”史龙彪苦笑道,“说难听点,算他一个坐探。今夜听了你一番理论,我才明白,永历比起康熙,连条蚯蚓也不如!”
“咱们不说这些了。”魏东亭道,“老伯英风盖世,如遇明主,一生事业正长呢!”
穆子煦、郝老四、犟驴子和史龙彪几个聚在灯下赏剑,明珠心里仍激动不已,端起一杯酒,头一扬饮了下去,在厅内踱了几步,口中微吟道:
风云会龙泉,有剑何灿然!
断得天河水,甘霖洒人间。
魏东亭不禁笑道:“兄弟好大志气!”
明珠已有醉意,大笑道:“若论兄弟才资,虽不及兄,也算说得过去的了,只是空怀报国之心罢了。时乎,命乎!”他已有狂态,眼中流出泪来。史龙彪、穆子煦、郝老四受到这种情绪感染,黯然不语;犟驴子只知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却不理会这些,自顾饮酒大嚼。
“何必作司马牛之叹!”魏东亭上前轻按明珠肩头笑道,“好兄弟,英雄造时势,事在人为嘛!”众人忽觉他语中有异,一齐转脸瞧他,魏东亭目光闪闪,微笑不语。明珠怔怔地问:“什么时势?”
“诸位,”魏东亭收起笑容,神色庄重地说道,“可愿意跟着我魏东亭取功名么?”
穆子煦笑道:“奔京里来为的就是投靠大哥,有什么不肯呢?”
“既如此,那好!”魏东亭道,“皇上命我遴选少年有为之士,伴驾习武以备非常之变,今日在座诸位若肯同心办好这差,还怕将来没有立功名的机会?”
穆子煦等三人顿时大喜道:“我们跟着大哥做就是了!”史龙彪也道:“只要用得上,我也能出一把力。”只明珠嗫嚅道:“哥哥手无缚鸡之力,怎生应付得下来呢?”
“你的差使更好!”魏东亭道,“陪皇上在伍先生跟前读书,我来弄这武的。”明珠顿时喜形于色道:“将来兄有寸进,总不忘兄弟提携之情!”
“老板,”见何桂柱坐在墙角不言语,魏东亭笑道,“你在想啥子?”
何桂柱闷闷道:“夹尾巴狗,有什么想头?”
魏东亭笑道:“你好大口气,孔夫子也做过丧家之犬!我为老板备资,你与史大伯在西便门外白云观附近重新开张做生意如何?只是事事得听史大伯和我的调度,自然也还你一个正果!”
“白云观?”史龙彪讶然问道,“那里叫李自成烧成破野庵子了,在那开店,除了庙会有什么生意好做?”
魏东亭笑道:“咱们只做大生意,小生意当个幌子就成!”
一番铺排,众人个个眉开眼笑。何桂柱道:“席已残了,我店后头地下还埋着几坛二十年老陈酿,可惜了的,不然大伙今夜都有口福了。”魏东亭笑道:“你以为只有你有好酒?请诸位尝尝我后院埋的老酒吧!”老门子已被大家吵醒,进来侍候。魏东亭吩咐道,“老爹,你带老四他们挖两坛出来,东西屋各一坛!”
刘金标被人架着回了班府,此时班布尔善方送走泰必图,见他血淋淋地回来,吓得酒也醒了一半,忙问:“是怎么了?”
听几个亲兵七嘴八舌地诉说完巡防衙门无理劫人的事,他倒犯了踌躇。巡防衙门正是他近日极力拉拢结纳的,怎会如此不肯给面子?见刘金标一副惨相,又不好责备,便索性送了个顺水人情:“这也难怪你们,金标受了伤,先到后头养着,等寻着那小子,我给你们出气。”
他一夜也没睡好,尽在床上翻烧饼,平时最宠爱的四姨太扒着耳朵劝道:“鳌中堂的事儿,你操那么多心,值吗?”他心绪烦乱地说:“妇道人家这种事儿少问!”
没想到这事这样不顺手。他原想拿到何桂柱,审明后再与鳌拜商议办法。不料出师不利,下午截住那个臭进士,被一个莫名其妙的糟老头子搅坏了,晚上去擒何桂柱,偏又被巡防衙门的人抢走,算晦气到家。
抄苏克萨哈家,意外弄出伍次友的策卷,循名按址找到了悦朋店。班布尔善不相信,一个举子能有这么大的胆,竟在顺天府贡院中大书“论圈地乱国”!没有硬后台,他敢!再说,苏克萨哈搅了进来,越发说明事情不简单。所以,几天来并没有动手拿伍次友,只派坐探扮作酒客观察动静,将悦朋店监视起来。不久便发现魏东亭也是那里常客。他心中暗喜:看来大鱼就要咬钩了。谁知几天之内,不但魏东亭不来了,连伍次友也杳若黄鹤,这就蹊跷得很了。他有他自己的棋,自觉比鳌拜高明得多!事无巨细,但与棋局有关,那就非弄明白不可。无奈之间才决定捉拿明珠、何桂柱,想捞起一根线来。可接连出了这两件事,使他觉得似乎还有别人在同他下棋,而且一步步都是先下手,这未免使他暗自心惊。
其实,听了刘金标的遭遇,他心里并不相信是巡防衙门劫了人,那年轻侍卫像是魏东亭,只猜不透这伙巡夜哨兵都是什么人——真是扑朔迷离呀——但既无把柄在手,又怎能奈何了这位皇上宠信的近卫?
一夜辗转,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班布尔善翻身起来便吩咐:“备轿,到巡防衙门!”
行至中途,班布尔善反复思忖,还是不去为好,事情传开了,弄得人人皆知,立时就会谣言四起,于当前景况实在没有好处。于是轻咳一声吩咐道:“回轿去鳌府!”
鳌拜因夜间多吃了酒,仍在沉睡。门吏因班布尔善是常客,也不禀告鳌拜,直接引他至后院鳌拜书房鹤寿堂中,安排他坐了吃茶,说道:“大人宽坐,容奴才禀告中堂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