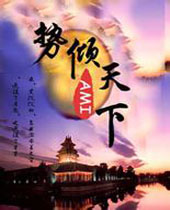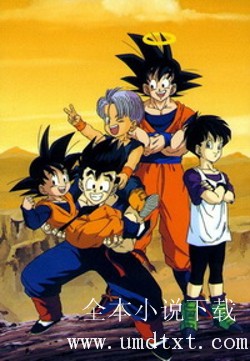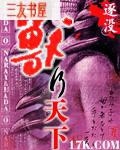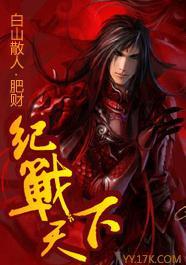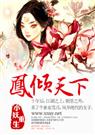天下豪商-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九十五章 墨娘子(求收藏,求推荐)
(全本小说网,HTTPS://。)
朐山县,榷场港。(全本小说网,https://。)
通海巷位于朐山县外的榷场港口旁边,不远便是浩瀚的海州湾,海面上商船渔船往来如织,不时有满载货物的高大帆船进出,热闹非凡。通海巷内却绿柳成荫,一片宁静。
通海巷东段,几乎挨着海滩,一座新修葺过的酒楼内,悠扬的丝竹曼歌,正从一间可以看见海对岸云台山景色的包间中传出。
包间内,几名穿着白色大袖衫襦的女伎拿着竹箫、胡琴和七弦琴在合奏一曲。
一位穿着不知道是波斯还是天竺式样的红裙,戴着头巾面纱的歌伎曼声唱道:“月华收,云淡霜天曙。西征客、此时情苦。翠娥执手送临歧,轧轧开朱户。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
一叶兰舟,便恁急桨凌波去。贪行色、岂知离绪,万般方寸,但饮恨,脉脉同谁语。更回道、重城不见,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
歌伎唱的是柳永的《采莲令。月华收》,歌声起伏,婉转缠绵,有着说不尽的柔情蜜意。让听曲的武好古和潘巧莲都忍不住一遍又一遍望着对方,仿佛在用目光告诉自己的挚爱:我们是不会分开的,永远都不!
一曲唱罢,那歌伎站起身,冲着包间里面听曲的客人们盈盈一福,然后取下了面纱头巾,露出了一张充满了异国风情的面孔。
这是一名胡姬,她的眼眸是黑色的,鼻梁挺直,皮肤白哲,五官精致,弯曲的眉毛又黑又浓。看这长相并不是日耳曼、斯拉夫种的,多半是波斯或是地中海沿岸的人种。
这胡姬虽然是个绝色的美人儿,但是年纪却有些大了,至少有二十六七岁,放在后世没什么,可是在萝莉当道的北宋青楼行中,这年纪的歌伎却也不多见。
她的脸上没有笑容,双眸中也流露出了哀伤,不知道是因为被自己所唱的词曲感染了,还是真的想到了什么伤心的往事?
不等武好古等人发问,将众人带来这座名为听涛阁的酒楼吃饭听曲的纪忆便眉飞色舞地说道:“怎么样?还听得入耳吧?”
这胡姬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歌喉却无可挑剔,唱得也是柳永柳三变的名词,而且还唱出了情侣依依惜别的那种意境,实在令人心潮起伏。
米友仁摇着扇子笑道:“忆之兄,如果我没猜错,这胡姬定不是听涛阁养的,而是你姑苏纪家的家伎吧?”
“何以见得?”纪忆笑着问。
“如此姿色,如此歌喉的胡姬,便是在开封府都不多见,何况是在海州?
况且,这般年纪的歌伎不是升了老鸨,便是从了良,还在献唱的,也就只有富贵人家养得家伎了。”
纪忆连连点头,笑着说:“果然没有能瞒过你米元晖的,她便是我家的家伎。
墨娘子,过来陪武员外、米衙内、潘衙内和尹衙内喝杯酒吧。”
“喏。”
胡姬应了一声,第一个就到武好古跟前。武好古是有佳人相伴的,虽然为了行走方便,潘巧莲换上了男装,可是她那等妩媚姿容,就是穿上男装,也瞒不了谁。那胡姬自然也能看出来,于是也没有撩拨武好古,只是从一旁伺候的女使那里取过酒壶,给武好古酒杯斟满。尔后便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又拿起酒杯,遥遥一敬,用甜甜腻腻的吴音说:“奴奴敬武员外。”
武好古举起酒杯,并没有喝,而是好奇地问:“墨娘子,你是何方人士?”
“奴是明州人士。”
明州就是宁波。
宁波人?武好古心说:你骗我,我见过宁波人的,没你这样的。
“在下问的是墨娘子的祖籍是哪里?”武好古又问了一句。
“奴的祖籍是广南东路广州番禹县。”
广东人?看着还是不像啊,中东人还差不多……
纪忆知这时笑着插话道:“大郎,在广州是有不少白番后裔的,他们的祖先最早从南朝时便到来了,至今有数百年了,其中一些白番后裔已经不知祖籍何方,也忘记了乡音,完全入了华夏。
这位墨娘子的母亲,便是从广州来的,当时已经怀有身孕,在明州生下了墨娘子。约莫十七八年前墨娘子又辗转到了我家,成了家伎,一直到今日。”
“原是如此。”武好古点了点头。心里很有点同情这个墨娘子了,虽然她是个番女,但是姿容、身段、歌喉,恐怕都不在李师师之下。
可是却一辈子不红,最后入了商人家做家伎,而这家伎又做了十七八年,从父亲伺候到儿子,连个妾都没混上去。
看来这世上不如意之人,也是十常八九啊。
不行,那么好的人体模特儿可不能让一直在纪忆家里面耽误下去,得寻个机会把她要来做个人体模特,将来也好在中国,不,是世界美术史上留名……
武好古刚想开口向纪忆索要墨娘子,才忽然想起潘巧莲就跟自己身边呢!
虽说这年头男人纳妾再正常不过了(武好古可不是要纳妾),可是潘巧莲……武好古心虚地看了眼潘巧莲,见她正笑靥如花地看着自己,哪里还敢提这茬?
墨娘子这时敬完了酒,便莲步轻移出了包间,武好古望了眼她的背影,才依依不舍地将目光收回,眼角的余光,却扫到了那个高丽棒子尹奉,忽然发现他的一双小三角眼睛,也正直勾勾看着墨娘子的背影,还咽了下口水,仿佛想把人家一口吞了似也。
不过就墨娘子的身板,要真送给了尹奉这个柴禾般的高丽衙内,还不三下两下就把他吸干了?
高丽衙内这时也把目光收了回来,正好发现武好古笑吟吟看自己,颇有些尴尬,忙笑着转移话题道:“听说武员外是开封府第一的画师?”
武好古笑了笑,刚要谦虚几句,他的好徒弟米友仁却替他吹嘘开了:“家师乃是宋画第一人,这可是李龙眠,王晋卿和家父共同评定而出的。”
“米衙内,”尹奉居然很了解宋朝书画名家的,这时突然插话问,“另尊可是米襄阳?”
“正是,”米友仁道,“家父正是米元章。”
尹奉不敢相信,又看了看纪忆,纪大官人点点头,笑道:“没想到吧,米襄阳的衙内竟然拜了这位武崇道武员外为师。”
说着话,纪忆又笑着问武好古道:“崇道兄,在下也是个爱画之人,不知可否求得一纸墨宝?”
“好啊。”武好古一笑,马上应了下来,他拒绝谁也不会拒绝纪忆,纪家超级有钱,姑苏纪半城啊!
“不知忆之兄想要怎样的画?”武好古问。
“美人图样,”纪忆说,“照着真人来画。”
“像这幅吗?”武好古一伸手,他的好学生米友仁便递上一个画卷,武好古拿个画卷后就给了纪忆。
纪忆展开一看,原来是一幅《毗沙门天图》,图上的“毗沙门天”,纪忆却是认得的。
“画得是智深大师?”
武好古点点头,“这是元晖摹的,便送你了。”
在从涟水到海州的途中,武好古便开始教米友仁临摹自己的几幅新作了,其中便有《毗沙门天图》。从官船上下来的时候,武好古就叫米友仁拿了一幅《毗沙门天图》的摹本,准备要送给纪忆的。
武好古又说:“待吾返回开封,便为忆之兄作画如何?”
“好,便一言为定了。”
第九十六章 佛法和子宫(求收藏,求推荐)
(全本小说网,HTTPS://。)
西门堂在海州的分号,开在榷场外面的榷场港临海长街上,占了一所三进三出的院子。(全本小说网,https://。)门前的青石路面上有被车轮轧出的两道深深的车辙,显然经常有车辆运载着货物从这里进出。
就在武好古、潘巧莲、郭京、刘无忌、林冲等人往临海长街而来的时候。西门青和他的祖父也在张熙载的陪同下刚刚抵达,爷孙两个从一辆马车上下来,海州西门堂的掌柜就亲自迎出来了。
“大伯您怎么来了?这一路的劳顿,您老的身子骨还好吧?”
海州西门堂的掌柜也是西门家的人,单名一个咨,名叫西门梓,是西门青的族叔。
顺便说一下,西门青所在的阳谷西门家是个“半义门”,也就是介于义门和普通宗族之间的存在。
和坚持不分家,搞家族公有制的义门不一样,半义门是分家的,下面的每一房,每一家,都有各自的产业。不过在分家的同时,半义门下也存在大量的公产,主要是学田和族田——一般来说,将商业资产做为族中公产是很难经营的,而田产则相对容易经营,只要收租就行,因而义门/半义门的族中公产通常是农田。
而半义门拥有的学田、族田,则主要用来支付族中子弟的教育费用和赡养族中孤寡老人的。
具体到阳谷西门家,则是以阳谷和彭城的农田为本,同时经营药铺和宋辽走私的半义门。阳谷和彭城的农田皆是族中公产,各地的西门堂,则是各房的私产。
海州这边的西门堂虽然和彭城的西门堂挂同一块招牌,但并不是西门青的产业,而是属于西门梓这一房的。
另外,西门一族既然是半义门,自然也要在科举仕途上有所争取。
若是没有几官身倚靠,如西门家这样的富家,便是官人吏员们眼中的肥肉了。
不过西门家走的不是文科举的路子,而是专攻武举,因为有祖上传下来的骑射底子,西门家族祖上可是出了不少武进士。不过从西门青的爷爷西门鹤那一代开始,由于宋朝武举日益注重笔试,使得西门家吃了大亏,已经有几十年没出武进士了。
这家道,也显得有些中落了……不过西门族中还有许多能打善杀的狠人,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弱者!
而且,各地西门堂都是医馆药铺,要是换人来做,还有没有病家上门就不好说了。所以西门家虽然没有官身庇护,但也还可以维持局面。
“还好,还好,趁着还能走动,便四下走走。”西门鹤一边说,一边在西门庆的搀扶下进入堂内,然后又穿堂而过,到了后院。
一入后院,西门鹤马上就问:“马家的老二到了?”
“到了,昨日便到了。”
“没引起旁人注意吧?”
“没有,没有,”西门梓笑道,“这几日有个高丽国的使团正好到达,海州官府都忙着招待高丽国贵客。”
“哼,甚底贵客?”搀着西门鹤的西门青冷冷道,“不过是契丹人的狗奴才。”
“联丽制辽嘛,”西门鹤道,“这说明朝中的相公还没忘记恢复燕云。”
三个人说话的时候,已经进了西门堂后院的一间堂屋。堂屋内也有两人在说话,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商人打扮。其中一个生得高大,蓄了一部络腮胡子,仿佛是个武将。另一人则短小精悍,皮肤很黑,五官倒是端正,说话的时候一对眼珠子总是在转,显得非常精明。
看见西门鹤、西门青和西门梓三人进来,正在说话的二人也连忙起身,冲着西门老头便行了一礼。
“晚辈马植,见过西门世伯。”
“晚辈花满山,见过西门大爹爹。”
西门鹤摆摆手,“不必拜了,都坐,都坐下说话。”
说着话,老头子便在一张玫瑰椅子上坐下,又叫西门青、西门梓也坐下。
“对了,马二郎,你家燕山先生怎么说?要不要把那个姓武的诳去辽国?”
“二叔叫我来看看,若真有信上说的那么好,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不就是一画画的么?”西门鹤有点儿不以为然。
马植却一脸正色地摇摇头,道:“世伯有所不知,契丹人这些年来日益沉迷佛法,不能自拔。国家财富,都用来建寺斋僧,国族(契丹人)壮士,不是在家吃斋,便是入寺为僧。契丹一族不过二百万众,僧尼却有三十多万,全都坐食供养而不事生产。
长此以往,契丹将无可战之兵,无可饷之银,一旦祸起草原林海,便会有倾覆之灾了。
而我燕云汉人,则日益兴旺,族人繁衍至数百万,渤海之族,也尽皆汉化。如今的大辽,我汉人才是第一大族!
若契丹人继续沉迷佛法之中,不出三四十年,就算辽国不亡,契丹国族也将被我汉家所替代了。”
原来契丹人就要被印度的佛教和汉人的子宫打败了!
二百万人口,有三十多万僧尼,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口繁殖。而且没有出家的契丹人,也大多沉迷佛法,念经念得糊涂了,再也没有祖先的悍勇善战了。
相比之下,燕云汉人倒是在辽国的“乡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