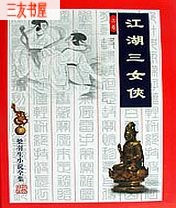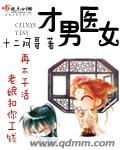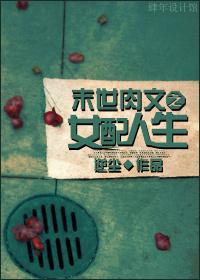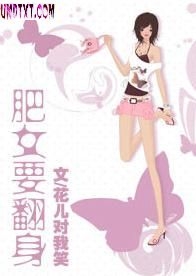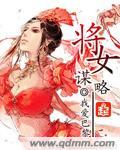庶嫡女-第1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且为人很周全,让跟他说话或者共事的人都很舒服,不会让人心生反感。他知道母亲的性格快人快语,连父皇那样的性子有时候都镇不住,这么柔和赵群说不定还被他母亲欺负呢?想到这里他还有些想笑。
自从他办成了这件事情回京之后,声望大增,太子选妃一事再次提上日程。他却并不放在心上,大丈夫何患无妻,只要妻子不是那等蠢货就成,他则利用和初哥儿的关系从他那里拿了不少他母亲做的东西,而且也因为他对初哥儿好,母亲主动给自己做了一对手套。
前世母亲也爱跟自己做东西,什么手套、衣服,他根本就穿不完,这一世却已经是奢侈了。
他没想到父皇竟然生了退位的心思,他有些不可置信,却又想通了,其实父皇原本就不恋栈这个皇位,只是他身为太子如果不成为皇上,想必下场很惨。有的人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跟自己献起了殷勤,他厌恶这样的人,实在是太过于趋炎附势。
云氏其实在秀女中很平常,家世不算顶尖、人也不算特别聪明,但胜在听话,他想要个这个的皇后能镇住就成了。尉氏秀美可人、傅氏善解人意,后宫还有不少对他献殷勤的女子,但他自觉身为君王就不要感情用事,否则前朝后宫都处理不当。
既然他成了天子,就要平衡好这些关系,不能因爱而宠,女子还是要看其生育子女以及品行。似尉氏虽然生了大皇子,但其人封了丽妃后就飘了起来,还无礼于皇后,这样的人肯定要治治。
他一向都是这样,从来不会觉得不对。
信王府的世子妃是他替初哥儿选的,因为梅氏是南直隶人,娘家不在附近也不太重视她,嫁入婆家自然一心为婆家着想。之后信王府的几个孩子都是他替他们选的,他知道她娘三十六岁的生日过的很快乐,儿媳妇们纷纷为她庆生。
他也想去,可是却不能。
有一瞬间,他回想起袁氏那个女人,那是怀着怎么一颗恶毒的心的人,那样的人根本就不配为母亲。
好在那个袁氏他已经解决了。
现在他站在养心殿里,烛火已经烧了一大半了,他按下手中的折子,这一世他过的很孤独,却更加明确了自己来此间的宿命,不仅仅是见到前世的母亲今世活的这么快乐幸福,而是继续把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
至少这一世,没有康王继位,也不需要太多的拨乱反正。
“万岁爷,夜深了,您看要不要歇下了?”
“睡了吧。”
第二日起来他又要开始早朝,他似乎天生就是做皇帝的样子,从来不会感觉累。他看到信郡王赵群上了折子要把二儿子派到苦寒之地,很是意外,同时也觉得在意料之中,信郡王府的儿子多,可只有初哥儿一位能袭爵,其他的人想要出头很难。
而赵群又不想自己的儿子靠着余荫去做事,因为仅凭父辈的余荫,自己没有本事,日后不过是沦为闲散宗室罢了。能够吃常人吃不起的苦,熬的下来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了。
他批了,看到赵群过来谢恩。
“仲哥儿是个实诚人,日后必会本分做事的,信王还请放心。”
赵群笑道:“蒙皇上圣恩,也是想让这黄口小儿出去长长见识。”
他开玩笑道:“仲哥儿去那么远,你和王妃不会想他吗?”
却见赵群正色道:“自古忠孝哪能两全,我们做爹娘的,只盼着孩子好,在不在身边的又有什么要紧的。若他过的不好,强留在我们身边,也不一定会孝顺。”
原来如此,赵佑宁夸了一句:“信王妃果真是女中豪杰。”
听别人夸他的妻子,尤其是皇上夸耀,赵群一幅与有荣焉的样子,“他跟了臣这么多年也没让她享福,她这个人豁达的很,还让我多谢谢您,说您不仅对我们世子那么关照,对府上也照顾。”
赵佑宁微笑:“应当的。”
他真的是应当的,如同赵群所说,只要他过的好,就是不在娘身边又如何?更何况上辈子他已经得到他的娘全身心的爱护了,这就够了。gd1806102
第167章 第一百六十六章 陶心湄番外(一)
(全本小说网,HTTPS://。)
蒲州县陶家湾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陶家湾方圆五十里有一座气派的大宅子,青砖绿瓦; 窗明几净,陶家湾的人都十分羡慕,若是能住上那样的屋子; 就是一死也得偿所愿了。
陶家出过大人物; 陶家的老爷子官至国子监祭酒,正正经经的京官; 三年前却带着一家老小回到这里推翻了小茅草房; 建了这座大宅子。有人说是陶老爷犯了事被赶回来了,有人说陶老爷年纪大了告老还乡;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不过人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陶家的仆从、田地都是本地的员外郎所望其项背的。陶老爷一共有俩子,长子陶大爷娶的是侯府的姑娘; 次子是回来蒲州娶的; 是本地乡绅家的姑娘。不过陶老爷的长媳命不好,从京城回到蒲州的途中动了胎气,孩子早产了。
现在陶大爷没有娶妻; 独自抚养这位小姑娘。
“湄儿,天快黑了; 进来吧。”
听到自家爹爹的叫声,陶心湄放下手中的几根草; 跟着丫头跑回家去。家里仆人并不多; 她有一个婆子和一个丫头伺候着; 在陶家湾她是名副其实的大小姐,就是二房的婶子生了个儿子也比不得她。
“爹爹,湄儿回来了,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陶大爷此时还很年轻,他今年满打满算也才二十五岁,因为父亲的关系回乡避难,陶家在蒲州县有个小铺子,每隔三个月陶大爷便去城里结账,今次也是。他手里拿了个糖人递给她:“喏,湄儿,你要的糖人。”
陶心湄高兴的转圈儿,“爹爹太好啦。”
看着这么高兴的女儿,陶大爷满身的疲倦都不翼而飞了。他跟妻子虽然是婚后才认识,可妻子的容貌才情跟他十分契合,更何况,若不是为了这个家,妻子也不会早死。所以妻子虽然没了,可他对这个唯一的女儿十分宠爱奉若珍宝。
女儿集他和妻子所长,才三岁的年纪,就已经出落成这个样子,以后也不知道会如何?
陶大爷正值盛年,虽然对妻子感情很深,可他是嫡长子,家里不可能让他一直这样作为一个鳏夫活下去。很快陶老夫人就寻了一位在家守孝错过了花信之期的姑娘刘氏,刘氏是位秀才的姑娘,读书识字,还生的婀娜袅袅,对陶心湄也视如己出,陶大爷十分放心。
只是,再怎么视如己出陶心湄也不是刘氏的亲生女儿,尤其是刘氏也生了女儿之后,陶大爷对长女又疼宠一些,盖因她生而丧母身世堪怜。况且陶心湄的母亲虽然过世了,可留下来不少嫁妆,陶大爷有心想为女儿留着,可财帛动人心,随着陶家每况愈下,他也没办法守着一大笔嫁妆不用,要家里人吃苦受累。
恰好这时侯府的人来了,他们说侯府的老太太慈悲,老太爷怜惜外孙女生而丧母,想接孩子去侯府。此时陶大爷内心是不想送女儿去的,别人家里再好,总是寄人篱下,可女儿却一定要走。
他不解:“湄儿,跟爹爹在家不是很好吗?”
却见女儿道:“你连我娘给我的嫁妆都用到心妍母女身上,你根本就对我不好?”
他语塞了,他是擅自用了妻子的嫁妆,但是是给全家人用的,可他在蒲州新开的铺子有了起色,过了一年半载的挣了银子,自然还是会给女儿作为陪嫁。
他想解释,哪里知道女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定要跟着侯府的管家走,他去留,却见那管家道:“陶姑爷,表小姐都跟我说了,你宠爱后面的妻子,根本就对她不好。”
“张管家,我……”
那管家一幅明白的表情劝他:“陶姑爷,表小姐这样的貌美,在这乡野之地又怎么会有机会出头?我们侯爷说了,家里开了闺学,表小姐进了闺学,日后我们老太太再帮着寻摸一桩体面的亲事,岂不是两下便宜?”
这确实触动到了他的心事,女儿生的太好看了,陶家湾哪里又有配得上她的人?
他亲自找到女儿,陶心湄看到她的爹爹,不像小时候那样依恋,反而觉得父亲是想断了她的好前程,她一个没娘的孩子,若自己不为自己打算着些,日后怎么办?刘氏对她是面上好,更何况刘氏不过一个穷秀才的女儿,现在穿得起绸缎,还不是用的她娘的嫁妆钱。
她冷着脸对她爹道:“不管如何,女儿肯定是要去侯府的。爹爹日后不必为了女儿挂心。”
却没想到她爹同意了,“湄儿,你既然那么想去,爹爹也不会阻拦你。只是别人说的一入侯门深似海啊,你的亲外祖母早就过世了,爹爹也没多的东西给你,这两百两银票你带着,进了府之后也好打点一番。”
也许在侯府两百两并不算什么,可在还八岁的陶心湄眼中两百两无疑是一笔巨款,她仔细的放在贴身的荷包里,坐在宽阔舒适的马车里,望着早已被甩在脑后的陶家湾,她怎么还有些心疼。也许是想起父亲最后一个表情,想起小时候父亲对她的百般疼爱,可她终究还是要为自己打算……
从蒲州到京里,并不算近,她就近观察着侯府派过来的人,仅仅一个伺候的嬷嬷就浑身绫罗绸缎,未语先笑行礼请安,说不出的气派。她既忐忑又多了几分期待,难怪她从小就觉得自己和陶家湾的那些人不一样,甚至跟同是乡绅家的姑娘也并不一样,原来她骨子里更像她娘更多一些,她娘是侯门女,她也是。
这一路乘船、坐马车,折腾了快两个月才到京城。这也是她头一次到京城来,京城实在是太气派了,就那城墙都比一般地界儿的高。她战战兢兢的下了马车,由下人们扶着从角门进去,换了轿子,又再换了轿子,她觉得自己仿若皮影戏里面的人,本人提着走。
不过,这也足以说明侯府很大,她们在陶家湾的屋子谁不羡慕,可看到侯府,她才知道陶家湾的那房子放在侯府也不过是下人住的屋子,甚至比下人住的屋子还要差。
“表姑娘,请下轿。”
她咬着牙,丝毫不想露怯,昂首阔步的跟着丫头去见侯府的老太太,也就是她的外祖母还有舅妈们。老太太倒是慈眉善目的,赏了她一幅头面让她戴着玩儿,舅妈们都各有表示,就是表姐妹们都差不多跟她年龄相仿,她真是觉得太好了,人人都这么和气,人人都这么好。
第二日又从外边来了一位汪家表妹,说起来她和这位汪表妹的关系更亲近呢?因为她的亲外祖母和汪表妹的亲外祖母是亲姐妹,她比汪表妹过的还好一点,至少她爹爹还在,而汪表妹则是父母双亡,基于这个,她也要多照应汪表妹几分。
侯府的人对她很好,像院子就单独跟她分了一个大的,衣裳首饰的样子都是她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她很是欣喜。
过了几日,她再去请安的时候,却又跟第一天所见的时候不大一样了。大家似乎有意无意的总是把焦点放在大表姐身上,跟看不到她一样,还有那位在大表姐身边站着的六表妹玉琪。就是老太太也一口一个心肝儿的叫大表姐,她站在一旁觉得有些失落,看到身旁站着的更加懵懂的汪淑儿,她又叹了一口气,如果这丫头能够大一点还可以跟她一起商量。
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她兴冲冲的问她的乳母:“妈妈,今年除夕我要跟淑儿表妹坐在一处吗?侯府里都吃什么呀?是在老太太的院子里吗?”
她一连串问了许多问题,却没见她的乳母回答,她又问侯府派过来伺候她的丫头。那丫头支支吾吾道:“表姑娘就在院子里吃便是。”
“什么?你搞错了吧。大过年的怎么会让我们冷锅冷灶的吃饭呢?”陶心湄不信,而且老太太人也和蔼,她肯定不会让自己一个人过年的。
往年在陶家湾,家里过年都是热热闹闹的,爹爹会跟她买好几身新衣服,孩子们抓着花生瓜子装一满荷包,再趁机向大人讨要红包,即便是最抠门的二婶在那天都会笑眯眯的给红包给她。
这个时候的她并不知道这些,还在请安的时候跟老太太说了出来,恰好老太爷也在那里,老太太看向老太爷,“您看如何?”
老太爷沉吟一声,“孩子们来了咱们家,就是一家人了,再者二丫头和三丫头都是没福气的,好容易留了这俩个孩子,让她们跟我们一处吃吧。”
陶心湄偷偷的看了一眼老太太,只觉得老太太不是很高兴,但仍然是笑着安排好她们。
她对于自己说动了老太爷和老太太有些自得,于是去了汪表妹那里告诉她和她的嬷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