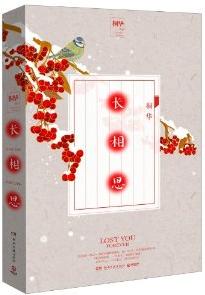长相思,在长安冒牌王妃在长安-第6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李易之,你是不是没吃饭?用点力啊……”
“还不够高?”李谏又用力推了几把,手有点酸,“你这是要上天了啊。”
“不够,我还要!”
“不行了,我软了……”
刚刚过来准备请示是否布膳的冬生远远看到这一幕,心想,这西北风大概比珍馐美馔更有滋味吧,于是默默退下了。
第76章 这种痛,从骨头深处一丝……
十二月就这么过去了; 眨眼除夕将至,长安城即将迎来新的一年。
太子被罚禁足东宫一个月,这段日子他乖巧得很,果然足步不出东宫; 天天抄经替皇帝祈福; 又每日命人替他到甘露宫向皇帝问安; 将经书呈给皇帝。除夕这一天; 皇帝终于发话; 免去太子的禁足令。
“玉郎,全靠你想了抄经祈福这个法子,父皇果然心软了。”李珩兴奋地道:“你瞧; 我到底是嫡长子; 只要我不忤逆,顺着他的意; 他多少念着父子之情。”
杜玉书却道:“殿下可不能得意忘形,皇上这么做,只是因为今晚是除夕; 他虽免了你的禁足令,却没传你到兴庆宫,可见心里还是对你不满。更何况,此番宁王平定东突厥有功,皇帝对他赞赏有嘉,比起宁王的止戈兴仁; 殿下的经书又算得上什么?”
今晚是除夕,李氏一族的皇亲国戚及京中从三品以上大员,皆齐聚兴庆宫,参加今晚的宫宴。今年东宫诞下小龙孙; 今晚的宫宴比往年更盛大热闹。皇帝解除了他的禁足令,却没邀他参加宫宴,这还是自太子被册立以来,第一次缺席除夕的宫宴。
李珩听了这话,脸色讪讪的,哼了一声,“宁王那丑八怪趁我禁足,使劲做妖。罢罢罢,不去就不去,除夕的宫宴年年都有,也不差这一年。我这就传膳,咱们就在邀月阁设酒席,一边吃一边赏月,可不比兴庆宫强多了。”
杜玉书说不必,“太子妃仍在坐月子,她为了诞下小龙孙吃了不少苦,今晚既是除夕,本就该一家团圆,你过去看看她,陪她一道用膳吧。”
李珩本不愿意,经不住杜玉书一再劝导,说皇帝若是知道他善待太子妃,一定更感宽心,“初七的祭祖大典,或许他会允许你出席了。”
每年正月初七,皇帝都会前往李氏宗祠祭拜祖先,所有李氏一族的子孙皆会参与,是天家最隆重的祭祀大典。除夕的宫宴不参与就罢了,若是连祭拜祖先的庆典他都不能出席,那他这个太子就实在太难看了。更何况,早在两个月前,李珩就开始着手筹办此事,若是最终皇帝不允许他出席,会更让人猜测他的地位不稳。
李珩思及此,不情不愿地答应了,“那我过去看看她,玉郎你先用点参汤,等我回来,我们再到邀月阁……玉郎,你怎么了?”
杜玉书的眉尖忽然紧紧拧着,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将手捂在膝盖上。
李珩大吃一惊,“玉郎,可是你的腿又疼了?”
杜玉书痛苦地点了点头。
李珩急道:“怎会如此?你明明已经很久没发作过?”可随即一想到杜夫人刚刚出殡没几天,李珩就明白过来了,定是他心里难过,忧思过甚所致,“玉郎,你且忍一忍,我马上命人煎药,之前的龙须还有剩的。”
他正待喊人,杜玉书却说不,“龙须不能再吃了,海长老说过,我是从娘胎中带出的大寒之躯,服用龙须等同于饮鸩止渴,每次发作,只会愈加痛苦。”
李珩大惊失色,“那可如何是好?”
杜玉书痛苦地摇了摇头,“只能忍。”
眼看细密的汗珠自杜玉书额上滑落,李珩越来越着急,“那个海长老如今在哪?我马上命人将他抓来替你诊治。”
“不必。他来了也没用……”
这种痛,从骨头深处一丝丝往外抽,源源不断地,不让人有喘息的机会,杜玉书两手捂着膝盖,用力咬紧牙关,痛苦地蜷缩在矮床上,巴不得将一双膝盖剜掉。
太子在一旁干着急,若是可以,他宁愿痛的是自己。他跪坐在矮床边,抱着杜玉书,好减轻他的痛苦,却发觉他浑身冰冷,身上冒的全是冷汗,“玉郎,你怎么样?是不是冷?”
“冷……好冷……好痛……”
杜玉书的牙关在咯咯打颤,脸色苍白得像白凌,太子大声喊来人,往书房四角的青铜兽都加了碳,书房里很快便暖如春日,可惜杜玉书并没有好受些,摘胆剜心似的,汗水逐渐湿透他身上的衣物,最终昏迷在太子的怀里。
东宫的另一边,太子妃端坐在食案前,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脸上平静得像一樽瓷器。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名小内侍进来禀报,西苑的兰舟公子腿疾发作,太子不过来了,请太子妃自己用膳。
太子妃平静无波地嗯了一身,拿起玉箸夹了块蜜渍山药送入嘴里。
兴庆宫那边的宴乐声不时传过来,一旁伺候的孙嬷嬷看着行单只影默默进食的太子妃,在心里轻叹一声,将窗户关紧。
“难克化的您别吃太多,一会还要用药。”孙嬷嬷见她胃口不错,高兴之余又有点担心,但转念一想,难得她今晚胃口好,多吃点又如何,又道:“难得您吃得香,要不今晚就不吃那药了,少吃一次,我想着也不妨事吧。”
太子妃却道:“不,药必须得吃。我这两日胃口好了,精神也足了,全靠这药。”
“是呢,早先的药,您喝了十多天也不见有起色,连床都下不了,可愁死我了。这几日换了方子,奴婢眼见您是有了胃口,能下地了,脸色也比之前好了些,看来这方子的药是用对了。”
太子妃边吃边问,“陈御医替我换方子了?我记得之前的药并不是这个味道,明儿他再来时,你替我谢谢他。”
提到这事,孙嬷嬷觉得有些奇怪,“我昨儿也问了陈御医,开始时他支支吾吾的,我见他神色有异,便故意问多了几句,他经不住问,坦言这方子并非出自他的手,是受人所托。又让您尽管安心用这方子,他看得出这方子是出自高人之手。”
太子妃不由愣住了,“他是受人所托?受何人所托?”
孙嬷嬷摇头,“他不肯说,我给他塞了银子他也不说,只说那人吩咐过,不想让您知道此事。”
“这么奇怪?”太子妃眉心蹙起,皇后来看过她两次,但也只是做做样子问了几句,宁王妃倒是热心,隔天就来,虚寒问暖的,但以她的性子,若真帮了自己,还不嚷得阖宫皆知?她多半是来看自己什么时候熬不住的,“那张方子还在吗?”
孙嬷嬷做事仔细,很快便将那张方子找了出来,这种笺子,并非宫里常用的笺子,太子妃道:“你去医署,向拣药的药童悄悄打听一下,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
孙嬷嬷应了,半个时辰后回来,神色略带兴奋,“还是您聪明,真的问到了。也是巧,今晚守值的药童认得这笺子,说是前一阵乾祥宫太妃娘娘宫里的人,曾拿过同样的笺子去取药,他认得这上面的字,与那笺子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我又打听了一下,说是太妃娘娘之前晕眩症发作得利害,靖王找了个隐世名医替她诊治,最近太妃娘娘的精神比之前好多了。”
太子妃听了,失神地看着那张笺子,许久才道:“知道了。”
与东宫的萧条冷清相反,今晚兴庆宫灯火辉煌,喜庆的宴乐不绝于耳。
皇帝今晚特别高兴,先是东宫替他添了小龙孙,再是之前一直兴风作浪的东突厥,与肃州裴家军抗衡了数月后,终于安分了,竟学着西突厥,也把嫡子送到长安为质以表决心。
说起来,东突厥这次肯向圣朝低头,全靠宁王的大力斡旋。东突厥之所以抢掠边境,实因最近几年天灾不断,物资严重匮乏,唯有四处抢掠。宁王派出使者到东突厥,提出在两国边境划出一片区域,设立互市。在此区域内,两国百姓自由交易,两国设互市监,掌交易之事,监督税收。
互市可解决东突厥物资匮乏的难题,东突厥可汗十分赞赏,当即同意了,并许下永不犯境的诺言。不用一兵一卒就平定了战事,宁王可谓是立下了大功劳。
东突厥世子名叫阿布勒紫狐,二十五六的年纪,生得魁梧健壮,一双鹰目灼灼有神,看人时双目带笑,但眼里总有掩饰不住的欲望。
他对长安的繁荣富庶赞不绝口,更对宴席上献舞的舞姬倾心不已,但提到带兵打仗,言辞里却对圣朝将领多有轻视之意,“裴家军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我们东突厥近几年天灾不断,死了不少人,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若是早几年……不是我吹嘘,拿下肃州不过是一个月的事情。”
他说着哈哈大笑,又朝坐他对面的阿史那玥宁喊话,“玥宁,我说得对不对,咱们两部交手多次,东突厥的实力你最清楚不过了。”
他的中原话比阿史那玥宁说得好,玥宁不意他会这么问自己,耸了耸肩,“不好说,反正我们是打不过裴家军的,但你们部落又打不过我们部落,到底谁强谁弱,我也说不上来。”
原本阿布勒紫狐的话有点冒犯,让在坐的人皆有点不愉快,但玥宁的话又让众人笑了出声。
第77章 巾帼不让眉毛……
阿布勒紫狐的脸色有点难看; “你说的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啊我忘了,你在长安呆得太久了,早被这花花世界磨平了你的棱角; 你们西突厥的人大概也早习惯了这种安逸日子。在我们部落; 无论男女老少; 人人皆可上马打仗; 即便是孩子和女子; 丝毫不输男子,就算面对裴家军,他们也丝毫不惧。”
面对紫狐的嘲讽; 玥宁心里不快; 但又不知如何反驳,他们西突厥和东突厥不同; 因曾联过姻,西突厥多仰仗圣朝的庇护,在圣朝的余荫下求存; 紫狐的话并不算胡扯。
还好靖王开口了,“人人皆可上马打仗?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在我们圣朝,除了边寨重镇,从来没有让妇孺上马打仗的先例,历来只有男子冲锋陷阵保家卫国,哪有让妻儿上阵厮杀的道理?当然; 裴家除外,裴家满门忠烈,便是女子也是女中豪杰。”
一时席上众人纷纷附和。
紫狐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言下之意; 他们东突厥的男子几乎死光了,这才迫不得已让妇孺上战场。他语带不屑地道:“裴家的女子如何我没领教过,但裴家的男子……不过而而,花花架子罢了。”话出了口,他也知道以自己现在的身份,这么说实在不恭,于是又道:“不过如今既然我已坐在这儿,再说这些话就是不自量力了,方才多有得罪,皇上请恕罪。”
皇上原本有点不高兴,但见他主动认错,也不好说什么。
宁王见气氛有点僵,忙打圆场,毕竟两国互市的建议是他提出来的,紫狐也是在他的斡旋下来长安为质的,若是闹僵了,他也失了脸面,于是哈哈笑道:“如今两国互市,化干戈为玉帛,无论于圣朝、东西突厥两部都是好事,又何必非要争个高低。”又打趣道:“紫狐世子,方才我九皇叔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实在是你方才抚了他的逆鳞,他才出口驳你。”
紫狐奇道:“哦?此话何解?”
“世子有所不知,我九皇叔的王妃,正是裴家的女儿。”
紫狐恍然,他虽桀骜,但性情却是豪爽,当即朝李谏举杯道:“原来如此,方才是在下不敬,我愿自罚一壶,向殿下和王妃赔罪。”
他说喝就喝,倒吊着酒壶往嘴里灌,那香醇的烈酒,于他来说喝水似的,引来阵阵喝彩声。众人继续说说笑笑,不知怎地将话题引到骑射、投壶上了,紫狐自诩在草原上从未尝过败绩,借着酒兴,提出要与长安的勋贵们比拼一番。
因他之前言辞上颇有不屑,席上众人都表示愿意比试,好替圣朝出一口气。但今晚来的臣子,皆是三品以上的老头子,有心无力,皇帝只好从年轻的族亲里挑人,除了李谏、李飞麟,还选了个世家弟子。
场地有限,今晚只能比试投壶。阿布勒紫狐大言不惭,倒不是吹虚,几轮比试下来,李飞麟和玥宁都败下阵来,到最后决胜负,只剩了紫狐和李谏。
最后一局,地上放了五个壶,距离比之前几局的都远了三丈,难度更大了。一时观赛的众人都有些紧张,之前想着咱们人多势众,光这气势便能将紫狐吓倒,没想到紫狐毫无怯意,还越战越勇。众人心里都捏了把汗,万一靖王输了……这泱泱大国,居然输给一个外邦人,让圣朝的脸面往哪阁?
皇帝心里也有些嘀咕,趁着宫人收拾地上的残箭,悄悄让顾安去问话,“王爷,皇上说了,您要是没把握,皇上就借口累了,今晚到此为止。”
李谏额角一抽,皇帝开金口,大家自然不好说什么,但这么做和当众打自己的脸有什么区别?就是输,他也得输得堂堂正正的,他正想说不必,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