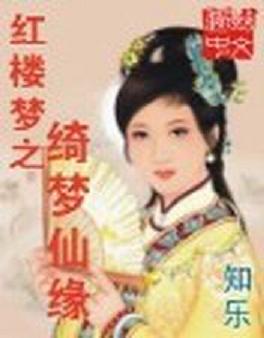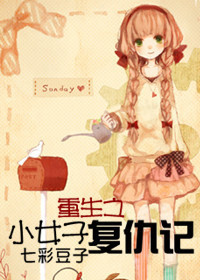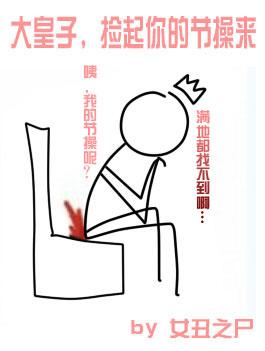红楼之小皇子奋斗记-第34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说,每次科考之前,那些考官们出的文集才会卖的那么火,那些考生们都是指望着从那些文集里面,得出自己到时候该怎么答呢。
当然; 文风虽然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 但策论考得更多的还是实事,毕竟,这些考生若是中了,那以后都是要做官的; 当官自然是要会处理事情。
前几年的策论,秦子轩并没有像是那些学子一样,专门去看过,不过等他又放松三天回来监考时,却被那策论的题目给狠狠的震惊了一下。
虽然说做官就是要管理天下名声,而每次的科举除了少部分的幸运儿能够留在京城以后,大部分都会被派到各地当知县,做父母官县太爷。
可即便如此,这策论考得也未免有点太接地气了吧,其他的那些题目暂且就不说了,可那一本正经讨论该如何种地的题目是怎么回事。
种地那是能够讨论出来的吗,而且看这一个个的举子,虽然肯定有出自农家的,但读书不易,有所成就的肯定是不会下地干活的。
这些人,哪里能够答出个所以然来,而且,就算是答出来了又能怎样呢,难道他们还能比多年种地的老农还要厉害吗,真当人人都是袁隆平啊。
就算是袁隆平,那人家也是种了无数年地以后,才发明出来的杂交水稻好不好,那成功的背后,可是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尝试呢。
虽然心里面在疯狂的吐槽,更是觉得,那些考生们会败在这道题目上,但秦子轩面上却是并没有表现出来,年纪越大,他的表演功力也就越好。
老早就已经练就了一脸云淡风轻的技能,心里越是惊涛骇浪的时候,面上就越是平淡,这已经不是在表演了,近乎于直接把自己贴上了一张面具。
往年的策论如何不知,但今年的策论,无疑是更偏向实际的,那讨论如何种地才能更好的题目不说,还有关于水利方面的题目。
秦子轩还在其中又看到了关于如何赈灾的题目,还特意引用了云州的例子,除此之外,就只剩下那道老生常谈的题目了,也是考验这些举子们情商的题目。
没错,就是那道万金油的,问你如何看待皇帝之政,这道题基本上从大乾立国以来,是年年都有,科科必出,而且虽然形式都是这个形式。
但具体内容却每科都不一样,毕竟朝中的大事那么多,皇上下达的政策那么多,三年才一科考,那么多的素材中随便抽出一个,永远都不带重复的。
别看这样的题目,长得挺像是前世那种送分题一样,但实际上,两者相差的可不只是十万八千里那么简单,这道题可以说是科举最难的一道题了。
问皇帝之政如何,还具体到了实事上面,那真是轻不得重不得,既不能猛夸显得太过虚伪谄媚,却又不能轻了淡了,这个度想要把握好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至少秦子轩觉得,换成他,大概是做不来的,不过好在,他这辈子也不需要那么处处小心的看人脸色做事,更不需要揣摩上官心思。
他只要本本分分的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做好便是了,当然,没事的时候,也得想办法讨一下自家父皇的欢心,不过那也不需要太勤。
想到此时可能正在御书房批阅奏折的父皇,秦子轩环视了一眼那一个个封闭的考棚,还有他们旁边站着的大头兵看守,想了想,还是回了考官们集聚的屋内。
望了眼依旧是在奋笔疾书的那些考官,还有他们眼下深深的黑眼圈,秦子轩扯了扯嘴角,还是尽量放轻脚步的走到了二哥的面前。
颇有书呆子属性的二哥,根本就没有察觉到秦子轩的到来,又或者,是察觉到了,但因为正忙着写卷子,所以没有时间和心情搭理。
总之,秦子轩这么一个大活人站在了面前,秦子祺却根本就不受影响,自顾自的拿着毛笔,在那里答得欢快,那副乐在其中的模样,让秦子轩看得很是有些无语。
这若是什么其他的考试,秦子祺这幅模样,他倒是能够理解,毕竟他这位二哥一向都是个学霸极人物,可瞅瞅那卷子上的题目。
农业,水利,赈灾,还有为自家父皇歌功颂德,这不管从哪方面看,自家二哥应该都擅长不了才对啊,怎么现在却答得如此认真。
第440章
这么想着; 秦子轩不禁转动了一下身子; 跑到了秦子祺的身旁; 打算看看这卷子上到底都写了些什么; 他可不相信,从未种过地的二哥,能够写出什么所以然来。
不过让秦子轩感到震惊的是,他发现桌子上的那张卷子,只这么一会的功夫; 第一道题就已经答完了,那张纸写得满满的; 是现在最流行的馆陶体。
四四方方,看得很是工整顺眼; 远比他那一手自己都认不出自己写的是什么的狂草,要好上无数倍; 两者全然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然了,看卷子吗,字体虽然赏心悦目,但还是内容最为关键,毕竟; 科举考试时; 所有的卷子,都会由专人进行重新抄写。
这也是为了防止作弊的一种,要不然每个人的字迹那么鲜明,直接拿过来看的话; 实在是太容易事先交流沟通了,若是那样,就连糊名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可就在秦子轩不知道抱着什么心思,仔细去看二哥所写的卷子时,他再一次的又被震惊到了,这倒不是说秦子祺写的有多么好,多么出彩。
而是秦子轩压根就没想到过秦子祺能写出来,所以在看到对方真的写出来时,才会这么吃惊,要知道,这可是农业啊,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上书房可是从来没讲过的。
秦子轩现在再瞅向自己这位二哥的目光,都已经是带着点敬佩了,虽然说对方这卷子上写的,很是有种纸上谈兵的感觉,但对于一点头绪都没有的他来说,能够写出来,这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果然,学霸就是学霸,在学霸的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叫做知识渊博,这才叫知识渊博,懂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那算什么啊。
连这种农业水利很少有人问津的杂学都精通的,那才叫学识渊博呢,这一刻,秦子轩甚至觉得,自己这位二哥若是去参加科举的话,别的不说,进士那是绝对稳了。
当然,这只是秦子轩自己单方面的想法,那些举子的卷子,他都没有看过,自然也不知道,他们都答得怎么样,但他总觉得,应该有一大部分人都是比不过秦子祺的。
其实仔细想想,这也是很正常的,毕竟,身为皇子,拥有的资源那可是全天下最好的,不是状元出身,都没有资格进上书房,不是天下闻名的大儒,都没有资格担当讲学先生。
坐拥着这样的教学资源,吊打一群可能连进士老师都没有的举人,说实话,还显得有些欺负人。
不过这么一想,秦子轩反而是更加羞愧了,因为他发现,坐拥有如此多资源的他,别说是像自家三哥一样,跟欺负小孩子一样的吊打这些举子,不被这群人吊打,那就算是他幸运了。
好在,上书房之内,他的水平应该还不算是最差的,有着自家三哥垫底,秦子轩羞愧了一会,也就恢复了过来,反正浪费资源的不是他一个。
这般安慰着自己,秦子轩又扫了一眼那越写越多的卷子,自信心被暴击了三百回合的他,终于不再自己给自己找虐,而是离开屋子,又跑去外面散心了。
说是散心,其实也不过就是坐在外面,吃吃点心吹吹风而已,没办法,屋子里那么忙碌的状态,他这个闲人,实在是不好意思在那些考官面前吃零食。
至于说找一个单独的屋子,那倒是行,贡院还是很大的,他们每位考官都有着单独的住处,不过那地方,离得有点远,就为了跑回去吃点东西,秦子轩还是不愿意动弹的。
一场一场又一场,一天一天又一天,时间便在秦子轩打酱油中过去了,等到这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不要说这些备受煎熬的举子们了,就连秦子轩都快忍不住感动的哭了。
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木有,这科举还真不是人该干的事啊,抱着这样的想法,秦子轩走出贡院的时候,只觉得外面的空气都清新了两分。
当然,这是因为他们这些考官,有着专门的通道,没有跟那些考生们挤一个门,要不然,三天窝在一个地方不洗澡,还就那么一个小空间的考生们,身上散发出的味道绝对会让人怀疑人生。
事实上,就连那些自己走出去的考生们,也都有些受不了自己身上的味道,有随从的由随从扶着,便赶快的上马车回府,没有的也是急匆匆的雇辆马车回客栈。
在这贡院门前,是丝毫都不需要担心,雇佣不到马车或者轿子的,那些做生意的人,一向都最是机灵,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准时的跑这来找生意。
其实这也不能算是找生意了,京城这个地方,马车和轿子大多都是不愁生意的,他们会大老远的跑过来,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沾文气。
古代嘛,大多数都有些迷信,虽然自己不一定就能拉到状元爷或者是进士老爷,但那概率还是有的,而且三年就这么一次,也没有人会嫌耽误功夫。
第441章
相比于这些还需要排队出门的考生; 秦子轩就要舒服的多了; 他可以轻轻松松的从专用通道出去; 回府好好的洗漱休息放松一下。
不过这是独属于酱油党的待遇; 那些正经的考官们,此时还是在那小屋子里面憋着,而且相比于前几天,只需要悠哉悠哉的答答题。
这会的考官们,算是正式进入到了紧张备战状态; 那场面,与那些参加科考的考生;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一个个的面色都极为凝重。
没办法; 不凝重严肃也不行啊,这会试可是科举的最后一关; 选中的人是要带过去给皇帝过目的,但凡出一单差错,可能就会是无数个人掉脑袋的下场。
这不是考官们自己瞎想,而是在太宗那一朝的时候,就真真切切的出过这种事; 那会大乾刚立国不过五十年; 天下需要算是安定了。
科举考试上来的官员也不少了,不再像是再往前那样,得需要举人去做县令了,可相应的; 其他问题却也很突出,就比如这南北考生的比例。
因为从前战乱的影响,北方的很多典籍文书都失落了,那些文人大儒们也有很多都遭殃了,整个文化阶层可以说是照以前直接跌落了不止一个层次。
而相比于北方,受战乱影响比较小的南方,就要好得多了,甚至在战乱祸害北方士子圈的时候,南方还没少接受那些逃难过来的文人和各种各样的典籍书册。
这么此起彼伏的,也就导致了北方士子的水平与南方士子的水平,差距太过巨大,当然,这些差距,在会试以前,是不显眼的。
因为各省各府都是各考各的,各地有各地自己的名额,南方与北方也不是在一起争那个名额,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
不过到会试的时候就不行了,那是全天下的学子们一起科举考试,可不存在什么不冲突的说法,而科举考得是真才实学,差距过大的情况,就是上榜者没有一个北方士子。
其实要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南北方的文化差距摆在那里,可关键是,那届的考官们,全都是南方人,没有一个北方人。
这下子,那可就是捅了马蜂窝喽,那些北方来的举子们,哪个会承认自己比人差呢。
而且,就算是他们承认了自己可能水平不过关,会有人承认整个北方士子的水平都不过关,都比不上南方人吗。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看到一个北方人都没有上榜之后,这些举子们就开始闹起了事来,人家也不说别的,只三个字,那就是不公平。
简而言之,就是这届科举有猫腻,肯定是那些南方的考官们,偏向自己的家乡人,这个说法,在现代看来,或许显得有些可笑。
但在那个时候,同乡同窗同榜都可以算作是天然的盟友,所以这个说法一经传出,那是非常有市场的,基本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很有道理。
毕竟一届科举,一百多个名额,怎么可能全都是南方人,北方人就算是学问再如何差,那也都是一个个考上来的,不是滥竽充数的,怎么可能一个人都考不中呢。
这件事情闹到后来,已经不只是北方的士子们大喊不公了,就连北方在朝为官的都站出来弹劾了,而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太宗自然也是下旨彻查了。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显而易见,那一届的所有考生都被罢满了功名,发配到了边疆,而考官们,则是全部罢官免职,直接便砍了脑袋。
而借着这件事情,在那些血淋淋脑袋的震慑下,太宗成功的推出了南北分榜的政策,这个决议不是一时兴起得来的,而是早就已经想了很久的。
不过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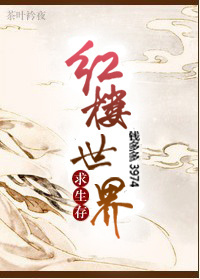
![[红楼]世家公子贾琏封面](http://www.cijige2.com/cover/1/138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