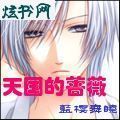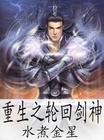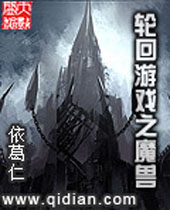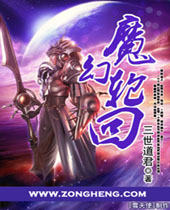轮回之帝国的历史-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七月,李庭芝、姜才在泰州战死,淮东之地尽失。
十月,元军董文炳破瑞安,秀王赵与择和他的弟弟与虑、儿子孟备以及观察使李世达、监军赵由噶、察访使林温、瑞安知府方洪被俘,他们均不屈而死。
十一月,陆路元军挥师从浙入闽,水师也从海上向南进逼,元军破建宁府、邵武军。陈宜中、张世杰匆忙护卫端宗小皇帝及卫王、杨太妃等登舟下海,朝廷彻底成为海上行朝。此时跟随朝廷的,实际还有军人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兵万人,与元军不是不可以一战。
载着行朝的船队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师相遇,但当时弥天大雾帮助船队躲过了一劫。
行朝南下到了泉州,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蒲寿庚是阿拉伯商人,史称其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这时,他正在宋、元之间见风使舵。他表面上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实际上是观望。张世杰还算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同意。等蒲寿庚回城内后,张世杰因海船缺乏,强征了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蒲寿庚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并株杀在泉州城里的宗室人员、士大夫与淮兵,次月就与泉州知州田子真投降了北元。陈宜中、张世杰只好护着端宗先赴chao州,后到惠州。
在惠州,陈宜中再次派人奉表赴元军请降。这位丞相在临安就搞过这伎俩,结果事到临头了,他又跑路了。到了现在还要再弄这个,到底是缓兵之计还是真想投降,还实在是让人琢磨不透,只不过他想没想过,对方会信任他吗?反正忽必烈是没被他忽悠,请降的使者被留在大都。
十二月,元军下广州。陈文龙在福建兴化也被部下出卖,被俘后绝食而死。
第二年的一月,循州刘兴,梅州钱荣之开城投降。至此,行朝在广南东路已无陆上立足之地,只能在海上游荡。
这时,忽必烈因蒙哥可汗的第四个儿子昔里吉为争夺汗位而造反,招南伐之师北还,以应付北方危机,帝国的军事压力才暂时得以减轻。借此机会,帝国残余的力量又开始活跃起来。
三月,宋文天祥复梅州。四月,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复会昌县。六月,文天祥率军入雩都。七月,文天祥派赵时赏等人分道收复吉、赣诸县,围赣州。衡山人赵?、抚州人何时皆起兵响应,一时声势浩大。
张世杰也亲率江淮军围攻泉州的蒲寿庚。此时汀、漳诸路剧盗陈吊眼以及陈文龙的夫人许夫人所率的畲军也前来助阵,因此兵势稍振,蒲寿庚见此只能闭城自守。
八月,北元李恒奉命率兵援赣,他亲自率军奔袭文天祥于兴国。文天祥军都是聚合之众,根本未习战阵,李恒猝至,当即溃散,使其兵败空坑。幸亏部将巩信舍身断后,监军宗室赵时赏故意引走追兵,文天祥才得以与杜浒、邹?等人脱身,但部属大多散失。文天祥的妻子、家属也尽落入李恒之手,两个儿子死于押解大都的路上。
九月,元将页特密实再破邵武军,进入福州,端宗的船队只好游荡到广南东路之浅湾(今香港荃湾)。同时伯颜也平定了昔里吉的叛乱,北方的危机暂时得以解除,于是忽必烈下令达chun与李恒、吕师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岭,下广南;蒙古岱、唆都、蒲寿庚及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合力追歼流亡的帝国小朝廷。
此时,张世杰对泉州的围攻也无进展。蒲寿庚私下里贿赂畲军,使之没有全力攻城,同时派人间道求救于唆都,于是唆都来援,张世杰只得解围,回军浅湾。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的处境显然有点信心不足了,他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在招回了陆秀夫后,就借口yu作准备先赴占城了。
至此,到景炎二年(1277)底,在北元灭宋大军的打击下,各路宋军和义军,或败或降,只剩下张世杰所率的相对完整的一支力量,保护着年仅10岁的宋端宗赵?和流亡的小朝廷向南败退。
十一月,在浅湾的行朝船队,又遇元将刘深所率领的水师来袭,幸亏当ri大雾弥漫,刘深因情况不明,不敢穷追,才使得流亡朝廷的船队死战得以逃离。
十二月,当这只船队到达井澳(又名仙女澳,今珠海市横琴岛深井湾)时,老天也助元为虐,突然飓风大作。那飓风直掠过整个船队,所经之处,舟船倾覆,无一幸免。好容易等风暴过去,只见端宗的坐舟也被掀翻在海里,可怜幼龄小皇帝也溺入水中。虽经众水手急忙救起,皇帝却早已在狂风巨浪中被折腾的衣杉褴褛,面目青肿,半死不活,好几ri都说不出话来。
风暴过后,陆秀夫和张世杰赶紧整理船队,拯救落水士卒,但是人员已伤亡一半,实力大幅削弱。
然而宋室的厄运似乎还没有完,就在小朝廷休整船队,试图恢复元气的时候,刘深又率北元水师再度追杀过来。
看看手下残破的队伍,张世杰只好率船队再次遁入大海。可是刘深却不依不饶,一直穷追猛打,直至七里洋(今海南东南)。双方再恶战一场,不幸国舅俞如?又被掠走。那刘深眼看气候恶劣,深海难测,也不敢再追,只好返航。
这是一个让人压抑的天气,天空被乌云所遮盖,海面上的风浪很高,即使是在庞大的楼船上,人也难以站稳。船队中的许多船都用铁环或皮索连接在一起以抗风浪,同时保持船体的平稳。在船队中部一只楼船的大厅里,一群人为着船队的去向在激烈的争论,他们已经分成三派争论了很长时间了。
一派认为应该去占城,因为左丞相陈宜中已经前往那里联系,更何况占城原来就是大宋的藩属,去那里避一避,再借点兵马粮草,回头再举,大事也是可为的。帝国在沿海的各地均已被占领,回去难有立锥之地。
另一派却反驳说,占城路途遥远,现在海况极差,途中十分危险。同时帝国的皇帝到藩属国那里算什么?避难?别人愿不愿意还两可。故此认为应该回广南东路,因为那里的百姓还是心向大宋的,而且chao州马发还在坚守,大宋的另一个丞相文天祥也已退到那附近。如果在那里能找一个落脚点,物质、粮食、兵员都可以得到补充,复国也不是不可能。
持这两种观点的人最多,也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议去琼州,因为那里距船队不远,再说元军还没有占领那里,但这个建议很快被其他两派的人所否决。堂堂大宋天子,怎么能到那个蛮荒之地呢?要知道在整个宋朝,那是个专门流放罪人的地方,帝国的皇帝跑到那里,脸面何在?何况它孤悬海外什么也没有,没有百姓,元丰年间户都不到一万。没有什么物产,从它的贡物就可以看出,尽是些槟榔、姜等土产,粮食必定也无法供应行朝。这如何能成为行朝落脚的地方?
在大厅的前部,站着两个大臣。年纪大点的,身板宽厚,神态威猛,显然是个武官。年龄稍微轻点的,也已步入中年,手持笏板,一身书卷之气,俨然而立。听着众人的争论,他们二人却一言不发。
………………………………
第二章 一个虚弱的声音
( )这两人就是陆秀夫和张世杰。陆秀夫现在是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在陈宜中赴占城后,行朝实际上就是这一文一武在主持了。
七里洋之战后,连遭打击的宋军士气极其低落,众人对前途均有渺茫之感。陆秀夫和张世杰私下里商议认为:行朝在海上漂泊不是长久之计,下一步的去向如不马上确定,人心就有散了的可能。因此,今天他们召集众臣就此商讨。听着众人的议论,两人表面上不动声se,心里其实也像外面的大海一样在翻腾。
主张去占城的,主要是文臣,陈宜中离开之前曾经和他们交流过对局势的看法。他们并非是怕死,而是对前途悲观,认为应该去占城暂避一时。应该说军事上的失利和陈宜中的观点,这两者对他们都有一定的影响。
而认为应该回广南东路的,是以殿前指挥使苏刘义为首的武官。刘义本是三苏的后人,但却不像他大名鼎鼎的祖先以文弛名。面对异族的入侵,社稷的危难,家传忠君报国的思想使他弃文修武,走上了一条与他祖先不同的道路。年轻时候的慷慨任侠、祖先雄文豪迈之气的熏陶和军人的热血,这三者使其难以言输,他是坚决主张杀回去的。
但是,武官中的招抚翟国秀、团练使刘浚、王道夫、周文英、陈宝等人也主张回广南,却又和苏刘义有些不同。因为他们虽然也被朝廷授予官职,但他们实际上是民团,也就是他们的部属是响应勤王的号召而来的地方军队。这些民兵主要来自于浙、闽、粤,他们的家乡就在那里,对土地和家的情结注定他们没有多少人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军中的情绪迫使这几个人也主张返回沿海,更何况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当地的豪强,舍弃自己的家族也是他们自身所不希望的。
提出去琼州是尚书苏景瞻,这个同为三苏的后人,显然是受他先祖曾被发配过海南经历的启发,才联想到哪个蛮荒之地的。
陆秀夫暗暗摇了摇头。说实话,他不喜欢陈宜中,这并非是因为陈宜中曾经罢了自己的职,而是他认为这个前丞相夸夸其谈可以,做事实在不行。但他并不认为不可以去占城,帝国面临的困局,前往占城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方会接受吗?近千艘的船,二十万人到别人那里,别人会怎么想呢?陈宜中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信回来。另外,海况如此恶劣,陛下已落水一次,身心遭受重创至今没有恢复,如果途中再遇到什么不测……,风险也的确太大。
可是回广南东路呢?作为曾经在李庭芝幕府里担任过幕僚的他,清楚地知道,自鲁港兵败之后,宋军的jing锐已丧失殆尽。现在宋军虽然看起来数量仍很庞大,但战力相去又岂止十倍?这剩下的近二十万军队中,也就张世杰麾下的万余江淮军还有些战斗力,其余的说是乌合之众亦不过分,开战一触即溃是早已就证明的,这样的军队又如何能在那里站住脚呢?
可是陆秀夫也清楚的知道翟国秀、陈宝等人主张回大陆的原因,不说他们现在人数上占有优势,而且有着勤王的旗号,使得行朝有时也不得不迁就他们。就是从复国的大业上看,离开了大陆的行朝没有兵源、没有粮草,又如何能发展呢?时间久了,百姓还认你这个皇帝吗?帝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他的百姓的,如果那样,还谈什么复国。苏刘义的主张虽然激进,但同样何尝不是张世杰的一些想法呢?
陆秀夫真的觉得头痛,他禁不住想到哪个敢作敢为、令他又敬又佩的同年进士状元:“宋瑞,假如是你,你会如何决断呢?你一定不会像我这么优柔寡断吧?”那一瞬间,这位帝师的眼神全是迷茫。然而,当他转头向张世杰看去的时候,他看到对方看过来的眼神里同样是犹豫和迟疑。
张世杰暗自叹了口气,陆秀夫的困惑他是知道的,本来他们私下商议的时候就难以决断,所以才召集众人商量,但现在商量的结果……,也许该去征询一下最后那一个人的看法了。
大厅里争论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众人的目光也都望向了这两位首席大臣。陆秀夫和张世杰互相看了一眼,彼此轻轻地点了下头,陆秀夫开口说道:“诸公的意见我和张枢密都已明了,但滋事体大,还须太后决断。现在我和张枢密前去觐见太后,还请诸位原谅。”说完,在众人的注视下他和张世杰离开大厅。
这是楼船中后部的一个卧舱,舱房很大,但被隔成了里外两间。外间立着几个待命伺候的宫女和太监,里间有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垂手站在一边的是个年龄约三十岁的太监;另有一个年纪相仿、穿着像个道士的人在给躺在床上的孩子把脉;还有一个是显然已无须用其它来衬托其高贵气质的妇人安静的坐着那里。妇人的神se虽然有点不安,但每当望向孩子的时候,她的眼中总是充满着母xing的慈爱。孩子的头上和四肢上依然横七竖八地裹着很多布条,在房间平静的空气中,可以闻到一股草药的味道。
良久,那道人轻轻放下了孩子的手,转身对那妇人作了个揖:“官家应无大碍,但还需多静养。”
妇人不安的神se稍稍放松了些,颔首道:“王……,道长费心了。”转头又再看向孩子,眼中却禁不住有点波光在闪烁。
一个小太监轻手轻脚的走了进来,和那个年龄稍大的太监耳语了几句,哪个太监走到妇人的身后低声说到:“